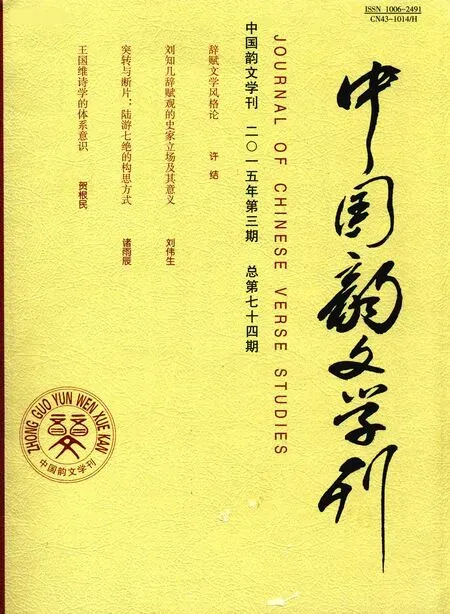王国维诗学的体系意识
2015-11-14贺根民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03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研究”(13XZW001)。
*作者简介:贺根民(1971- ),男,湖南邵东人,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20世纪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受西学的烛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化观念和科学思维促使国人重新检讨和整理旧学,旧学系统化思想逐渐成为晚清民初文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抉择。中国古代文论自有一条相对独立的体系文化脉络,或准体系线索。将古代文论中那些侧重即兴体悟的散金碎玉连缀成富有逻辑、珠光宝气般的串珠项链,还得归功于王国维等民国学者的不懈鼓吹和勤劬实践。王国维是民国学术天际划过的一颗流星,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文化昆仑。他奉学术为生命,融通古今、淹贯中西,以开放的学术胸襟,恢宏的学术视野,在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取得不少具有首创性的学术成就。王国维孜孜于建构文论体系,他以《红楼梦评论》开启了现代文论,又以《人间词话》终结了传统文论。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力图证明王国维诗学无体系可言,而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则紧扣原著,全力展现王国维美学思想,高扬了王国维诗学的体系风貌。缘于二著所持标准的差异,这几近相反的结论恰好从侧面道出王国维诗学的体系意识。
一 思辨基点与体系建构的核心范畴
文、史、哲不分的杂文化生态,铸造纷繁复杂的古代文论表现形态。古代文论中如《文心雕龙》、《原诗》等具有严密体系的文论著作,素非古代文论的典范形态。数量众多、卷帙浩繁的诗话词话、书信序跋、诗选批注、评点以及散见于经书、子书、笔记之中的文论,却是古代文论家乐于操持的武器。将形态纷纭的理论聚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由无序走向有序,恰是民国学人旧学系统化思想的具体表征。王国维有一条颇为自负的文学道路,他的诗词创作、文学理论书写均可视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界标。其《三十自序》夫子自道:“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1](P244-245)王国维填词之所以成功,多缘于其对文学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丰富情感体验。
在梁启超揭橥文学救国的大纛后,文学逐步归依救国和启蒙的宏大指向,文学与政治的联姻速度加快。在一片政治文学观念高唱入云之际,王国维却戛戛独造,坚持纯美的文学观念来打造文学大厦。他极力推举文学为人生的鹄的,其《叔本华及其教育学说》一文载:“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 [1](P89)追逐和高举人生向度,成为其文学及文论书写的逻辑起点。相似的意旨还见诸《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之生活也。” [1](P31)自1904—1913年的近十年间,他耽于文学创作,衣带渐宽终不悔。1906年4月的《人间词甲稿》和1907年11月的《人间词乙稿》,凡105首,就是他静观人生、洞察世情的结晶。罗振玉之弟罗振常认为《人间词》的命名不无深意:“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云。” [2](P15)该词集频繁出现的“人间”二字,透析了王国维以文学创作来观照人生的文化取向。这亦如其《三十自序》所论:“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 [1](P242)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一生命运多舛,家庭屡遭变故。即如自1906年至1908年1月,王国维家庭屡遭不幸,严父、发妻莫氏、继母叶氏相继辞尘,再加上童年失怙、老年丧子等遭际,人生苦痛铸造他深沉的人生考察眼光。如果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还停留在建构悲剧理论层面,那么《人间词》的撰写则带有填词自遣、深悟人生苦痛的意味。
王国维以提倡天下学术为己任,在学术上虽取得诸多惊人成就,一生却为生活所累。他集各种社会矛盾于一身,欲求学术独立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他人。从他一生来观,迨至1925年移居清华园,他方才脱离经济困顿的烦扰。坎坷命运和忧郁情结致使王国维醉心于叔本华和康德之书,职是之故,《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均不同程度上带有西哲影响下、深味社会人生的色彩。《红楼梦评论》形式上的现代性和《人间词话》形式上的传统特质,均标示20世纪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环节。就此而论,社会人生成为王国维诗学的逻辑起点,缘此推阐,就不难发现王国维诗学一以贯之的体系脉络。胡适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有如此记载:“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3](P440)胡适在高度褒奖王国维学术成就的同时,不无体认其学术的体系色彩。
诗学体系往往以某一核心范畴为基础,并由此建构首尾圆合的文论框架。《红楼梦评论》援引叔本华苦痛之说,揭示《红楼梦》示人以解脱之道的悲剧文化精神,忧生—解脱成为该文的基本概念。正因生活与苦痛如形相随,欲求解脱之道,势必先须绝裂生活之欲,文本中的和尚还玉之说就是去除生活之欲。王国维摸索出一条“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铸解脱之鼎”的文化路径,在他看来,自铸解脱之鼎方是真正的解脱:“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1](P9)这就彰显了文学的根本任务,也揭示非功利目的规约下,对文学本质的新的认知。出入《红楼梦》中的世情男女,最后都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以忧生—解脱尺度衡量,可以划归真正解脱者之列的,《红楼梦》世界却只有宝玉、紫鹃、惜春三人。相较而论,王国维更推崇宝玉式的解脱:“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1](P9)注重人生拷问力度,援引叔本华悲观主义来界定中华文学经典的美学价值,这在索隐和评点之法盛行的“红学”界,无疑是一股自然清新之风。如此诗人之眼,预示《红楼梦》研究新时代的莅临。
不必讳言,《红楼梦评论》的剖析路线带有明显的生硬图解痕迹,叔本华哲学印痕斑斑可考。1905年《静庵文集自序》道出事情的原委:“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 [1](P226)深得叔氏肌理的王国维解读《红楼梦》尚带有诸多生涩的意味,他有时甚至抛开作品而自由发挥,该论文的第一章即为注脚。但毕竟有异于叔本华理念为本、直观为末的哲学思辨,王国维推崇叔本华的直观说,虽带有某些舍本逐末的色彩。因为他解读叔本华哲学的兴奋点:“不在其体系外在,而在其人本内核。” [4](P11)这种选择也体现于其《人间词话》之中,该著“理念”的色彩更趋淡化。《人间词话》多处标举人生感悟,形成对前期忧生理论的诗性延伸,也显示他承袭核心理念的一贯追求。
如果说《红楼梦评论》还沦为叔氏哲学解读文学的副本,多归于一种的简单套用,那么《人间词话》则有意化用传统,显示深度融合中西文论的色彩。《人间词话》64则,大致围绕“境界”这一核心范畴展开,境界成为他梳理历代词作的标尺。王国维给予境界以词学之本的地位:“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本也。” [1](P350-351)其他诸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真与不真、隔与不隔等几组范畴均围绕境界而演绎延展,构成一个相互影响、完整有序的体系脉络。境界说的核心功能亦见于建构现代曲学的《宋元戏曲史》。该著认为元剧之佳在于自然和有意境: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5](P98)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5](P99)
著二“亦”字,彰显王国维对这两个核心范畴的注重。职是之故,从境界到意境,一字之别,相互牵连。个中虽不无王国维归依传统文化的思想折光,但其所孕育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审美追求倒是一脉相承的。王国维不仅要求诗文以“境界为最上”,阐述其他艺术也围绕这一中心范畴,在其画论《此君轩记》和《二田画庼记》中申述了意境的批评准则意味,以致聂振斌先生认为意境与典型一样具有同等序列的概括性和普遍性:“王国维自己把意境的含义发展到文学艺术之外,意境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虽然是在文学批评中建立起来的,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和普遍性,不仅属于文学,也属于整个艺术,并被其他的领域所借用。这种情形很像西方文艺学中的‘典型’范畴。” [6](P233)
二 纵横交织的框架
如果说核心范畴是诗学体系的内在结构,那么诗学框架则是其外在结构,内外结构的相生互补,搭建起严密有致的体系大厦。以往文论体系论者多斤斤于诗学的外在形态,做出古代文论是否有体系的判断,以西律中的判断色彩了然无遗。若以西方重逻辑、尚科学的思维裁断,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少数著作如《文心雕龙》、《原诗》才允符西方文论的体系期待。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古代文论则有一条相对自足的演变脉络,它附著于民族文化生态之上,至少具有某种隐体系。文论框架是诗学体系的显在反映,就外在形态而论,王国维交替运用多类形态,1904年《红楼梦评论》、1913年《宋元戏曲史》逻辑性强,具有一以贯之的外在框架;而1906年《文学小言》、1908年《人间词话》则采用传统的诗话随笔体,外在体系并不显豁。
《红楼梦评论》分四期连载于《教育杂志》,1905年又被编入《静庵文集》。全文凡四章,外加一余论。第一章先规设论文的逻辑起点,阐述人生观及艺术观,立一基本格调;第二章阐述《红楼梦》文本的悲剧精神,也就是自第二章起,方才进入文本阐释的轨道;第三、四章分别从善、美的维度发申《红楼梦》的审美价值。《红楼梦评论》每一章均集中论述一个中心问题,章与章之间相互连结。叶嘉莹先生认为篇章之间的关联恰好是该文的长处:“静安先生此文于第一章先立定了哲学与美学的两种理论基础,然后于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基础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精神哲理之所在,再以第三、四章对此书这美学上及伦理学上的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更于最后一章辨明旧红学的诬妄,指出新红学之研究的正确途径,是一篇极有层次及组织的论文,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7](P158)在叔氏哲学的接受视野里,王国维虽存有随意生发的痕迹,但其就文本价值的阐述大致有一个紧密关联的文化脉络:“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 [1](P14)这样,对中华传统文学经典进行伦理学、美学的阐释,一改“红学”史上的索隐、评点之风,刷新了《红楼梦》沿袭既久的研究模式。
《人间词话》的写作始于1906年,历时两年后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较以1906年发表的《人间词甲稿》,可以蠡测到《人间词话》为王国维对文学规律的总结和归纳。《人间词话》正式刊载之本为64则,而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人间词话》手稿来观,20页的手稿录载词话125则。这125则词话的体例跟传统的诗话、词话无甚差别,即多为即兴体悟的点评之作,缺少一以贯之的线索和中心意旨。而备经修饰后的定本,其内在结构和逻辑之前后牵连均大大加强,显然个中饱含王国维的精心思考及其有意为之的体系意识。据《人间词话》的定本来观,颇可考察王国维研习叔本华、康德哲学,援引其严谨结构、缜密逻辑的印痕。64则的《人间词话》大体可分三部分,第1则至第9则是全文的批评理论部分,其中第1则为全文之纲领,提出论词的基本标准,其后几则从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诸方面来分述境界说的具体内涵,它为评论古代词话树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指向;自第10则至52则,以时代为序,沿着李白、温庭筠、韦庄、李颢、李煜、冯延巳而下,径直论述至清代的纳兰性德,构成文学批评的实践。它以个案分析来纵向归纳境界营造的一般法则及规律,理论与实践相互补充、相互生发,构成一条清晰可见的体系脉络;第53则至64则属于第三部分,它涉及历代文学体式的演进、诗中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等命题,补充和延伸境界说的理论内涵。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两则兼及马致远、白朴两位曲学大家,既给予境界说言犹未尽之感,又使人窥探到境界说之于后来的曲学实践。如此说来,“这部《人间词话》,理论上鼓吹美在形式(文体),落脚点是论述境界学说。这样,64则词话就浑然一体了。” [8](P183)耐人寻味的是,即便不承认王国维诗学的体系意识,叶嘉莹先生却客观体认其系统色彩:“然而我们只要一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六十四则词话之编排次序,却是隐然有着一种系统化之安排的。” [7](P186)确如叶氏所论,一破传统词话的散漫之弊,《人间词话》以境界为中心建构了一种完整有序的体系。 ①
王国维感叹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1912年底,他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开始撰写《宋元戏曲史》,1913年分八期连载于《东方杂志》。《宋元戏曲史》这部曲学杰构梳理了古代戏曲的流变、艺术特质,引领国人去正确体认元曲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是戏曲研究史上的一座界标。中国固有的文学通变观和西方著史理念化合,林传甲、黄人撰写文学史的成功实践,这一切均为王国维高屋建瓴地爬梳古代戏曲源流提供观念和实践上的支撑。《宋元戏曲史·序》载:“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5](P1)王国维激于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基础薄弱、鲜人关注的现状,“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 [5](P1)王国维把持进化论,第一次清晰而完整地勾勒古代戏曲的演进脉络。这种观点固有吸纳焦循《易余龠录》的营养的色彩,但对其影响更多的则是外来文化。类似的意旨亦见于《人间词话》第54则:“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而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1](P364)进化论成为民国文人自觉的理论选择,它有效铺设了古代戏曲清晰的流变途辙。
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有一个水到渠成的整体蓝图,他以进化论和文体革新观来勾稽戏曲流变,《戏曲考源》、《曲录》、《录曲馀谈》、《唐宋大曲考》、《优语录》的相继撰述为《宋元戏曲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戏曲考》有一完整的体系,它以考察元剧的崛起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为鹄的,确立全书的骨架。除了开头之《序》和附录的《元戏曲家小传》外,全书凡16章,可分为四部分,亦即勾勒戏曲发展的四个阶段。其中上古至五代的戏剧为戏曲发展的萌芽期,古代的巫、优作为戏曲的远祖,它们确认了戏曲的演进之源;宋、金时代为古剧阶段,戏曲样式的变化和搬演故事的灵活性为戏曲发展蓄势储能;元代为戏曲发展的成熟期,其对元剧时地、存亡、结构、文章的分析,展现元剧巅峰形态的具体特质,而对于元剧的发展,他又厘分为蒙古时代、一统时代、至正时代三阶段,绘制了元剧兴衰的轮廓,相对而言,蒙古时代为最盛,至正时代则为元剧的衰落阶段;明代以后,是戏曲发展的衰落期,主要分述院本及南戏的渊源与文本。如此,五万余言的《宋元戏曲考》从戏曲的起源、发展、高峰、衰落等维度,整体统摄了戏曲的演进脉络。纵向的戏曲流变和横向的文学类型交织,铸造《宋元戏曲史》较为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其有意阐述戏曲与诗词、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门类的关系,已开辟侧重类型学来阐述戏曲特质的新路径。他仔细爬梳戏曲的版本、作者、目录,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建构了颇具王氏色彩的戏曲理论。缘于王国维拓荒性的研究,戏曲逐步成为一门专门之学,促使更多的文人投身戏曲创作和研究,就此而论,誉其为戏曲研究的不祧之祖,洵为确评。
三 从借鉴到融合:方法论的自觉运用
方法论是体系建构之魂,援引西学注重逻辑之长往往是王国维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有自觉的中西思维会通意识,看重新学语对国人传统思维的革新力度,《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已透露他侧重中西交融、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理论实绩。《论新学语之输入》对中西思维有一清晰的比较:“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1](P111)我国传统思维短于思辨推理,重印象与尚直觉,它不易使文学批评发展为严密、富有逻辑的理论体系。将西学之思与中华传统思维融合,新学语的输入为王国维兼容并蓄、化用中西提供了契机。他自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东京物理专科学校之际,他就致力于自学、独辟户牗,独学精神的发扬,铸造其一副广博的知识视野。其《国学丛刊序》就倡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1](P178)以平和心态对待中西古今学术之异,会通兼容,既强化学术研究的非功利取向,又彰显了学术的独立意识。
王国维治学注重科学精神,即便对待旧学,也强化系统的梳理眼光。其1906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提倡以西方现代系统思维来整理古代典籍:“如执近世之哲学,以述古人之说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也。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岂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复如此。” [1](P156)古人的著述体例虽有即兴体悟的散论特质,但备受体系视野的观照,这无疑有助于理出一条有序的线索。《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继承乾嘉汉学治学理论和化用西方科学方法的典范,既条贯宋元戏曲的源流,又建构新颖的戏曲理论体系,实现历史考据和审美批评的有效结合。
194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邀请与王国维精神契合、“风义生平师友间”的陈寅恪先生作序。陈《序》认为王国维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导引一代风气,示来者以轨则,可概括为三端,其一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9](P247)中西学的相互融合和印证,铺设王国维的现代学术基石,他之所以能在现代学术领域均取得不少惊人的成就,与其秉持的科学方法论不无关系,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的概括可谓例证:“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2](P86)王国维出入文、史、哲之间,时有新见,其《红楼梦评论》对叔本华哲学进行有意选择和变形,以形式上较为完整的外在形态确立学术的现代品格。而就《宋元戏曲史》而论,即如陈《序》称许王国维治学路径宽广的背后,隐寓对其史家章法的体认。“元杂剧之渊源”、“元杂剧之时地”、“元杂剧之存亡”均属于史家研究领域;而能划归为文学研究的只有“元剧之结构”和“元剧之文章”。蹈袭史家路径,已折射王国维对科学方法论的追逐,在比较之中自觉皈依史家章法,正显出转益多师的王国维形象。
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以纯美观念开始了他会通中西的治学之路,美学、伦理学维度设定了《红楼梦》阐释的方法论基础,尽管早期融汇西学的实践还带有某些不成熟,也隐寓日后理论申发和完善的契机。他以美术之眼来观照《红楼梦》,一破评点和索隐的迷局。侧重人类全体性质来剖析文本所蕴藏的人生指向,已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王国维援引康德“不关利害”的纯美之说来推崇超脱功利的天才说:“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1](P349)暂时忘却物我,所谓“观者不欲,欲者不观”体现了他非功利的考察视野,相似的意旨亦见于《人间词话》第3则:“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1](P349)二作的内在脉络清晰可见。撰写《人间词话》之际,王国维正主编《教育世界》,该刊在介绍西方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作品方面,费力颇多,出于职业习惯,王国维潜移默化受其影响,运用西学更趋圆熟。
如前所论,《人间词话》第3则“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句下,手稿中尚有“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 [1](P349)一句,对照他1907年发表的《莎士比亚传》和《英国大诗人白衣龙(拜伦)传》,显然他视莎士比亚和拜伦分别为客观诗人和主观诗人的代表。《人间词话》定稿中无此句,恰是他有意消融西学的实践。《人间词话》第17则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1](P352)虽然以《水浒传》、《《红楼梦》、李煜为论述对象,字里行间却饱含化用西学的痕迹。在王国维看来,《脱尔斯泰传》中的托尔斯泰作品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观察益深,阅历益富,构思益妙,运笔益熟”,这与《人间词话》中客观之诗人的“三愈说”异曲而同工。主观诗人的“二愈说”则可从其对拜伦和《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传》找到例证。总的来说,《人间词话》改变了《红楼梦评论》简单套用西方文论的做法,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接纳西学,标举了他会通中西思想的新成就。
四结语
民国学人的文论体系话语是特定文化生态的产物,他们的体系建构实践难免染带社会转型期新旧文化互渗的特征。王国维拳拳服膺叔本华哲学,《红楼梦评论》展示他与叔本华相似的生命感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推许《红楼梦》的经典价值,就在于援引叔本华的美学体验来谋求欲望解脱。遨游叔本华哲学王国,借叔氏理论来浇灌自我的忧生块垒,其解读多停留在以中华经典注释叔本华理论的层面上,生硬强牵,名著的文本价值却被简单化了。《人间词话》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文论家,虽然《人间词话》还提到尼采、席勒诸人,但其已广泛地吸纳包括康德、叔本华在内的西方人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在形式上,《人间词话》承袭传统词话的轨辙,而其对境界说内涵及其外延的精密分析,已揭橥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虽然其批评实践尚不能允符理论倡导的期待。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彰显他扬弃叔本华哲学的理路,也是中西文论交融的会通过程。
孤诣独创、思想深广的王国维,在引进西方思辨方式的基础上,融汇中西,展示体系建构的实绩,其诗学思想不断突破与创新,体系建构意识展示他与时俱进的研究理念。在体系建构实践中,《红楼梦评论》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坐标,借鉴西方体系脉络,衡以中华文化经典,将中华传统文本塞进先验的理论框架之中,借题发挥,还是一种浅表的借鉴。《人间词话》多援引某些核心范畴,融汇中国文论的生命感悟,既借鉴西方理论,又不为其所拘,彰显文论书写的民族化特质。对西学体系因子的借鉴,前者生硬,后者圆熟。如果说《红楼梦评论》援引西方文学理论,还是一项开荒拓疆的工作,那么《宋元戏曲史》则是体系书写征程上一座精致的建筑物,《宋元戏曲史》的史学章法与分期论述方式彰显了现代体系意识。《红楼梦评论》生硬的体系建构色彩在《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中被逐步扬弃,这是一条立足民族文化本位、融汇中西的体系建构的文化跋涉。就外在形式而论,《红楼梦评论》接受西学痕迹最深,《宋元戏曲史》最富有体系色彩,《人间词话》则介于二者之间,这三部著作在小说、词学、戏曲引领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从模拟到再创,缘于它们的现代体系话语书写,致使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