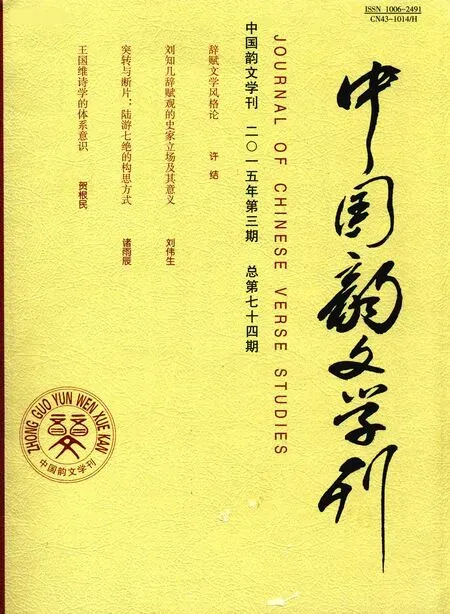郑孝胥诗中的末世心态及其艺术表达
2015-11-14李剑波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027-06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宋诗范式在清代的重建与新变研究”(项目编号11YBB3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剑波(1963- ),男,湖南涟源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古代诗学。
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号太夷,别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十八年,任驻日神户、大阪总领事。二十九年,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宣统三年,任湖南布政使。1923年,入清故宫任总理内务府大臣。1932年,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诗集传世者今有《海藏楼诗集》 [1]。郑孝胥是同光体闽派的代表人物,然以其投靠日寇而为世所不齿,其诗歌鲜为人所关注。
然而,郑孝胥主要生活在晚清光绪到抗日战争初期,这是中国社会多灾多难、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郑孝胥亲身经历了清王朝日益衰败直至覆亡的全过程,而且他又担任清政府的外交官,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有所了解。故其诗歌在内容上反映了神州陆沉之际的国际国内情势和郑孝胥等人的末世心态,也真实地揭示了郑孝胥失节堕落的原因。与此相适应,诗歌在艺术上也体现了这种写心的要求。
郑孝胥诗歌对其末世心态的写照:
一、对清王朝末世的忧患、焦虑与绝望心态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主要收录从光绪十五年(1889)直到1936年,亦即从他30岁到77岁之间的创作。少数辑佚之作更早或更晚一些。这段时间正是清政府走向灭亡的最后岁月和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前夜。郑孝胥身经目睹了清王朝一步步趋于“陆沉”的过程,于是也从一个特定角度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隅,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他和一些人面对动荡时局的末世心态,成为那个时代中一些人的写心之作。
他十分担忧日渐衰落的世道人心。晚清社会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他的不少诗歌都表现出了对礼义泯灭的焦虑和不满,如《吊日本大将乃木希典诗》:“中原今何世,谁复识名节。纲常既沦丧,廉耻遂澌灭。” [1](P230)《续海藏楼杂诗》其三十八:“举世轻忠义,苟全为高流。”《续海藏楼杂诗》其四十二:“功名与节义,时论方背驰。名教已扫地,何人能维持。” [1](P221)《冬日杂诗》:“礼义坐销亡”,“俗佞空张狂”。 [1](P24)这些诗句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纲常沦丧、廉耻泯灭的不安与忧心。这些诗歌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时的清代社会已然寡廉鲜耻、礼义消亡、世风日下、名教纲常为之扫地了。
他还担心外患,因为西方一直试图霸占中国。他尤为清楚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其诗《纪对南皮尚书语》:“彼族治战具,其端讵难闚。”“中朝实久弛,文武苟以嬉。” [1](P44)《海藏楼杂诗》其三十四:“强邻久阻兵,跨海置遮逻。吾民被迫逐,待毙但僵坐。其锋诚难争,善守抑犹可。” [1](P196)郑孝胥对日本的罪恶用心是看得清楚的,也曾为国家的安危担忧。他希望国家采取措施来避免危机,也寄希望于变法图强。但令人沮丧的是中国的变法实在太艰难。《天津入都车中》:“举朝议变法,不动犹拔山。” [1](P52)郑孝胥看到了危机,却看不到希望。这就使他徒增忧患。
众多的内忧外患萦绕于他的心中,凝铸了郑孝胥诗歌的主题词之一:忧患。“忧患”在其诗歌中反复出现。《高松保郎诗》:“人生历情劫,忧患深相缠。” [1](P13)《日枝神社晚朓》:“少年心事行看尽,忧患人间待此身。” [1](P26)《八月六日携炳垂二子登晴川阁》:“端令忧患满人间。” [1](P99)《呈栗兄》:“忧患如山容一罅,聊凭佳酿醉阿兄。” [1](P102)《陈弢庵过谈》:“十年忧患谢欢场。” [1](P131)《枕上》:“忧患磨人转畏名。” [1](P136)《刘聚卿属题文征明石湖画卷卷中有张文襄乙未十月题诗翁文恭庚子四月和文衡山诗》:“展览历忧患。” [1](P302)《入都车中和病山韵》:“忧患万端天正醉。” [1](P314)《青厓雨山竹雨香城夜饮》:“漆身吞炭都经过,忧患余生亦等闲。” [1](P411)《正月廿一日进呈》:“忧患相琢磨。” [1](P371)这里只是部分用到“忧患”一词的例证,而更多的情况是,虽然写忧患而并未使用这一词汇。然而这样已经足以让人清楚地看到郑孝胥诗歌充盈的忧患了。本来,对国家、社会、民族充满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点。尽管如此,像郑孝胥诗歌这样忧患满纸,也还是并不多见。毕竟,郑孝胥生活在那样一个极为独特的时代,社会政治腐朽,朝廷颟顸无能,道德信仰崩溃,经济每况愈下,民变此起彼伏,列强虎视眈眈,无休止地割地赔款,一个曾经自鸣得意的中华帝国眼看着就要分崩离析了。这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不能不正视和担忧的事情。惟其如此,作为对国内外情况都有较多了解的知识分子、封建官僚,郑孝胥才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忧患。
除了忧患,郑孝胥还表现出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朝廷无人的尴尬局面。《劳人》:“边事将谁语。” [1](P139)《海藏楼杂诗》其十五:“惜哉无大臣,独立济时艰。” [1](P192)《哀东七三首》:“中原适无人。” [1](P45)《移居绵侠营》:“物望谁云国有人。” [1](P46)《十一月十二日出京道中杂诗》:“中原虚无人,唾手真可袭。” [1](P56)《十九日又作》:“中朝不省筹边策。” [1](P142)《冬日杂诗》:“诚恐时无人”,“豪杰皆安在”。 [1](P24)对于清王朝种种危机的忧患,转化成为了对济世救国人才的企盼。这个时候的人们只能幻想有杰出人物出现,能够重整朝纲,富国强兵,守边御侮,救济时艰,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然而普天之下就看不到这种人才的踪影,这就不能不使郑孝胥之辈万分焦虑与惶恐。
清政府面临的问题成堆,而又无人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于是,郑孝胥产生了事不可为、必然亡国的绝望。《和陶乞食》:“时事岂可为。” [1](P138)《十月十七日奏辞督办边防》:“事急适无人”,“颓波既难挽”。 [1](P141)《天津入都车中》:“国势决难挽,将相岂足为。” [1](P52)《七月二十日召对纪恩》:“积弱非一朝,无兵决难支。” [1](P88)《重九雨中作》:“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 [1](P260)《十一月十八日出山海关》:“危邦空叹吾为虏,浩劫终愁谷作陵。” [1](P208)在诗中郑孝胥一遍遍地发出了事不可为、国家必亡的哀鸣。这种哀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噩梦,是那个末世中人们心态的写照。
为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和危机而忧心忡忡,为朝廷无人而焦虑不安,最后对神州陆沉的大势而绝望。这就是郑孝胥的心路历程,也是其诗歌的基本思想倾向,也是郑孝胥最终何以堕落为日本人走狗的根本原因。
二、顾影自怜的忧伤与哀叹
郑孝胥在其诗歌中常常表现出自我哀叹与感伤的情绪。照理说,郑孝胥的一生虽然说不上十分地春风得意,但也谈不上怎么坎坷,毕竟是为官作宦,衣食无忧,甚至还大富大贵。然而郑孝胥自己不这么看。他本来就是不甘寂寞甚至很有野心的人,总想有朝一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这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可以隐隐地看到一些端倪。或许这正是有人称其诗歌有“伉爽”之气的缘故吧。或许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腆颜去委身日寇的原因吧。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迟迟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因此感到自己很委屈,又觉得举世皆醉唯我独醒,虽有超人的睿智、才华却不为世用,浑浑噩噩一生又实在不甘,满腹牢骚又无处倾诉,眼看着年华逝去徒呼奈何,因此,他在诗中处处流露出自我伤感与哀叹之情。很典型的例子是《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一诗:
驻颜却老竟无方,被发缨冠亦太狂。
归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对茫茫。
孤云万族身安托,落日扁舟世可忘。
从此湖山换兵柄,肯教部曲识蕲王。 [1](P146)
这首诗的题目就揭示了郑孝胥这一类诗歌的主旨。在这首诗中,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态:生不逢时,有志难伸,不愿就此碌碌无为而泯灭,还厚颜地将自己比拟为宋代爱国名将蕲王韩世忠,似乎自己像韩蕲王丧失了兵权那样,空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却无法施展。以此之故,愁绪茫茫。郑孝胥的诗歌大抵都是表达此类的忧伤与哀叹之情。
郑孝胥为自己的不甚得志耿耿于怀,时常要长歌当哭,借诗言志,但他不是每首诗都明确地表达叹老嗟卑的意旨,从而招人厌憎。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只是在写景状物和叙事的同时稍加点染。且看《人日雨中》:
人日梅花空满枝,闲愁细雨总如丝。
临江官阁昼如暝,隔岸楚山阴更宜。
逋客偶来能自放,翔鸥已下又何之?
凭阑可奈伤春目,不似江湖独往时。 [1](P93)
《残春二首》:
近水生惆怅,看天抱苦辛。
一闲成落魄,多恨失收身。
又作江南客,还逢白下春。
春风太轻别,无地著愁人。 [1](P166)
这两首诗都是诗人触景生情,产生无穷的愁绪与伤感。至于伤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诗歌没有明言,只是让人觉得诗人哀愁、忧郁之深。然而,这种哀感无端,比具体的某种忧伤情感的表达,更使人能够体会到诗人的忧伤、哀怨无处不在,弥漫于整个诗中。
郑孝胥诗歌相当多地表达自己那种顾影自怜的忧伤,发出哀婉、凄苦的慨叹,甚至连五十岁生日之际,或者大年三十之夜,他也写出诸如《哀五十诗》、《除夕》这样悲伤苦楚的诗歌来,比比皆是的哀叹使其诗歌形成了一种忧伤、悲概的情感基调,仿佛末日就要到来了。
三、哭挽
郑孝胥诗歌中有许多哭挽之作。这是因为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多位亲人的离世。同治六年丁卯(1867)其母卒。光绪二年丙子(1876)其父郑守廉卒。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其三子东七殇。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兄孝思及其子友荃相继猝死于瘟疫。未几,长兄孝颖自沉于河。未几,妹妹伊蘐也因为痛兄而殒。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次女惠病卒。1918年四子胜病卒。1928年吴夫人卒。1933年长子垂病卒。亲人接连不断地逝去是郑孝胥痛彻骨髓的事情。他往往把这种锥心之痛用诗歌表达出来,长歌当哭。这类诗确是性灵之诗,血泪之作,有些诗写得极为沉痛、真切,富有感染力。如《哀东七三首》 [1](P45),东七为郑孝胥第三子,卒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仅两岁。作为父亲,诗人不胜悲痛,其诗句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与感受:“纸钱送汝去,遗烬那忍扫。今宵我不寐,窗下灯皎皎。后房汝啼处,絮泣剩婢媪。”又如《伤女惠》 [1](P175)诗,悼女惠之亡。次女惠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夭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年仅十三岁。女儿去世后,诗人沉痛之极,作诗回忆女儿惠的聪明可爱,并哭诉“我欲执汝手,汝手何从牵;我欲抚汝面,空想悲啼颜;我欲拭汝泪,却觅衣上痕;我欲抱汝身,唯有三尺棺”,真是如泣如诉,长歌当哭。
郑孝胥的这些哭挽亲人的诗歌,情到深处,每觉纸短,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写成组诗,如《哀小乙》六首、《述哀》七首哭兄与侄子之死、《哀垂》六首、《伤逝》等13题15首悼念其夫人吴氏。这些哭挽之作,大抵都是真情结撰,为他本来充满末世忧伤的诗集又增加了浓浓的一层哀痛色彩。
郑孝胥诗歌在艺术方面很好地适应其写心的要求,也甚有特色:
一、描写对象的主观化
从总体上来说,诗歌是一种抒情性较强的文学体裁,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特别是那些抒情诗,就更是如此。但是,诗歌中比例较大的写景、状物之作相对来说主观性就不一定很突出,有的诗比较重视描写对象的形貌的刻画,为描写对象作写照,就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然而,郑孝胥诗歌总体上非常注重主体感受、主观情感体验的表达,其诗歌虽是写景状物之作,他也常常是以我观物,按照我的主观感受来抒写,具有明显的写意———写心的特点,至于客观表现对象的形状、颜色、大小之类的外在特征,则不甚关心,不在乎是否形似。这里以他的几首咏月诗为例试作说明。
《咏月当头》:
霏霜蚀月月魂寒,可奈当头隔雾看。
宫阙天高归已晚,江湖夜永梦将残。
未斜何碍悬银汉,自转休疑失玉盘。
白发丹心人渐老,绕枝乌雀待谁安。 [1](P298)
《月》:
月是钓愁钩,钩来无数愁。
月愁有密约,相见五更头。 [1](P123)
《十月十五夜落月》:
凄清月色无今古,寂寞人间有死生。
雾阁云窗忽今夕,只将涕泪送西倾。 [1](P367)
《月下》:
千金不换今宵月,历劫难销往日心。
不道人生不如梦,人生是梦苦难寻。 [1](P432)
这几首诗都是将“月”这个客观对象物主观化,以我观月,以月写心。郑孝胥的《咏月当头》诗由所见之月写自己关于月的联想、想象,“月魂寒”是一种主观化的描写,“宫阙晚归”是化用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词意,与“休疑”句均是诗人借月做自我言说。《月》诗以月亮的外形似钩发生联想,表达诗人五更之时令他不能入眠安睡的万千幽隐愁绪。《十月十五夜落月》诗借月色的凄清写自己的寂寞凄凉之感,客观景物浸染在诗人的主观情感之中。如果说以上几首诗还是从月亮的外形、颜色出发来写的话,那么,《月下》诗就不太怎么扣紧月亮来写了,月亮在诗中只是提供了一个诗人所处的环境而已。诗人不顾所咏之月,自说自话,直抒胸臆,一吐内心情愫。诗歌的主观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些咏物诗都通过对高度主观化的月的歌咏,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末世感受。类似的诗作还有很多。总之,高度的主观化是郑孝胥写景状物之类诗歌的一个鲜明特点。它们揭示出郑孝胥诗歌创作心态的一个特点:内敛———诗人重在自我的内在情感体验与感受的表达,而将外在表现对象的再现置于次要地位。
二、以幽人意象出现的抒情主人公
在郑孝胥的诗歌中有一个“幽人”的意象经常出现,这个幽人就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即作者本人。这个意象出现时,有的明确使用了“幽人”这个词汇,也有的并没有使用这个词汇,但实际上也与写幽人的内容并无二致。即如《夜起》:
林杪春江月上时,楼中清影久参差。
四更欲尽五更转,犹有幽人恋夜迟。 [1](P108)
《十月二十六夜》:
晓色微茫雾未收,夜珠郁郁对银钩。
残霄谁待东方白,只有幽人独倚楼。 [1](P274)
《二十夜待月二首》:
峰明月未上,流碧满庭除。
空山独吟人,百虫来和余。
夜色不可画,画之以残月。
幽人偶一见,复随清景没。 [1](P134)
此外,写幽人的还有很多,如《磨墨》:“宜与幽人伴夜分”; [1](P348)《樱桃花下作》:“一春又去云为泥,难遣幽人楼中意。” [1](P371);《八月十一日夜雷雨》:“幽人独卧意殊适,江声入梦含苍茫。” [1](P110)郑孝胥诗歌中的幽人都是写实。这些诗歌记录了诗人在某些特定时刻的具体活动。但是,并不只是仅仅写实而已。郑孝胥以幽人自居,确是反映了他的某种末世心态,那就是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幽人在郑孝胥诗中出现的情境不尽相同,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境是深夜或者夜阑时分,月色当头,万籁俱寂,四野清旷,幽人夜起,独自面对夜色苍茫。这个幽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相伴,只有无边无际的巨大夜幕。他是孤独的。但他的孤独还不只如此。他是一个思考者。面对黑洞洞的夜幕,当众人沉醉于黒甜与温柔乡中的时候,他在倚楼张望、思索、等待、独吟,然而除了百虫的唱和之外,并没有谁来与之应答,并没有谁知道他,所以他陷入到了孤独的深渊。这个孤独的幽人实则就是郑孝胥深层心理的外现。郑孝胥是清末官僚中少数比较了解国内外形势与赞成变法的人物之一,然而他自认众皆沉醉唯我独醒,知道清政府腐败无能,事不可为,只能像伍子胥那样,眼看着神州陆沉,所以他是深夜的独行者。这些幽人意象就是郑孝胥心理、人格的象征与投射,也是其诗歌主题的形象体现。
三、喜议论而能写心,有深致
郑孝胥诗歌创作喜议论,不少诗作通篇议论说理。一般地说,议论如果太多的话,往往有损于诗歌的形象性和韵味,但郑孝胥诗歌的议论不太招人厌恶,究其实,乃是因为他的议论说理往往能写心,而且有见解,有深致,能给人以启迪。
他的有些议论表现出了对国家安危与社会弊端的深刻洞察。《冬日杂诗》:“运会今何世,更霸起西方。谁能安士农,唯闻逐工商。贾胡合千百,其国旋富强。此风既东来,凌厉世莫当。日本类儿戏,变化如疯狂。天机已可见,人心奈披猖。诚恐时无人,礼义坐销亡。豪杰皆安在,俗佞空张狂。” [1](P24)
这首诗纯粹议论,同时又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他那复杂的末世心态,即对时世的忧患、焦虑与绝望。他的忧患主要在于社会政治。他担忧的是,使外国迅速富强的工商业在中国却得不到重视,并且清代社会把压抑工商作为安定士农的手段。社会上世风日下,礼义消亡,国家缺乏人才。全诗纯以议论行之,虽然充满末世的恐惧与绝望,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病和危机却做了极深刻的评析。
有的议论表现了对人生哲理的深刻体悟。《孔子生日》第三首:“熟计老将至,时时欲息肩。不如有营者,汲汲常忘年。尼山不知老,劬学遗忧煎。犹云乐忘忧,其忧固难捐。孜孜毙乃已,治易姑勉旃。孔颜何所乐,寿夭从其天。老学若炳烛,吾意殊不然。多能实鄙事,作茧真自缠。颓然且放浪,如鱼跃于渊。毋为学所役,益智滋可怜。无忧岂非乐,至乐还随缘。纵老乐不改,以此得终焉。” [1](P422)
诗人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大问题。有的人想到年事已高就要歇息养老,实则不如忘年而工作。孔子老而劬学,忘记老之将至,可谓高人一等。不过,这样做,并不能将其忧真正抛开。诗人认为,真正的乐趣在于不计寿夭,任其自然。这样,连忘年、捐忧的措施和想法都没有了,就能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放纵自己,得到真正的乐趣。诗人所言,深得人生真谛。老之将至,郑孝胥对此不免难以释怀,有所思考,尽量宽慰自己,表现出豁达却又颓唐的姿态。这也是其末世心态的一种表现。诗歌通过说理议论的方式讲述了诗人对末世人生的理解。
郑孝胥诗歌的议论往往表现出对末世人生与社会的种种问题的深刻理解,意涵深蕴,以理取胜。这也充分体现了同光体诗人的学人之诗特点。郑孝胥诗歌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很好融汇的结果,但作为学人之诗,他较少堆砌典故,其诗歌语言大都平易晓畅。他也较少以学问为诗材,虽有少量诗歌把学术问题作为表现内容,却并不具有代表性。他的学人之诗特点主要表现为诗人具有良好的学养,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从而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过人的识见与思想,较高的理性思维水平,有深致。
四、以文字为诗:散文笔法、散文句式和虚词入诗
郑孝胥诗歌明显具有“以文字为诗”的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用散文笔法来进行写作。他的《赠林赞虞侍郎》、《严氏三耄耋图》、《十月初十日贵州丸舟中夜起》、《黎受生遗郑子尹书四种及巢经巢诗钞》、《赠丁叔珩》、《从母罗母诗》等诗歌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如《赠林赞虞侍郎》:
我朝二百年,未尝用闽士。
闽人入军机,有之自公始。
公虽负清望,峭直素难比。
特擢由圣明,此外更何侍。
孤立固甚危,诡随吾亦耻。
愿先收人心,以此立宗旨。
用人与行政,切忌犯不韪。
但令识轻重,缓急差可倚。
亦莫太矫激,徐徐布条理。
朋党兆已萌,勿使祸再起。
时艰至此极,任重宁足喜。
连宵语月下,含义深无底。
唯将忧国涕,珍重付江水。 [1](P163)
朋友林赞虞成为闽人第一个军机大臣,郑孝胥却认为“时艰至此极,任重宁足喜”,两人月夜道别时竟然流着“忧国涕”,全无弹冠相庆的喜悦,也没有新官上任的豪迈,只有重重忧虑,仿佛是一桩不祥之事,全然是一种末世心态。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完全是散文。它以意为主,逻辑性很强,没有诗歌应有的意象与意境。前八句以清廷开国以来第一个成为军机大臣的闽人说明林赞虞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与赏识;继而由林赞虞的峭直性格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愿望,希望他注意争取人心,用人行政都不要犯众怒,处事不要过于激烈,要防止朋党之祸等等;诗歌末尾处抒发伤感之情。全篇主要是对林赞虞的叮咛告诫,包含多层意思,内容上远比普通诗歌复杂。而且诗歌运以散文的单行之气,全篇一气贯通,没有一般诗歌的思维跳跃。它是用散文笔法来写的诗歌,或者说它用诗歌形式来承担了古文中“序”这种文体的任务。
二是其诗歌多用散文句式。通常情况下,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有着明显的区别:诗歌语言凝练,语意断续、跳跃,句子成分可以缺省,词序可以颠倒,与日常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有着较大差别。而散文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普通的书面语。郑孝胥诗歌常常采用一些超越了诗歌语言常规的散文化语言。诸如:
《六月十八日未明望海》:“天荒荒而非云,月团团而无色,海兀兀而不波,楼迢迢而将白。” [1](P42)
《三月初十日夜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1](P317)
《十月初十日贵州丸舟中夜起》:“海上有孤月,流光遍人寰。” [1](P327)
《严氏三耄耋图》:“其父百二十,名曰杨叔连。”“子云仁者寿,岂非人事焉。养气兼积善,可使生命延。” [1](P326)
上述诸例都是典型的散文句式,如“天荒荒”四句就是并列关系的复句,“一惭”句是转折关系的复句;而“养气”两句,就是以主谓结构做主语。这都是十分典型的散文句式。又其句子成分较为完整,词序排列规范,语意顺畅,语气单行、贯通,一切都显示出散文语句的风貌。
三是多采用虚词进入诗句。诗歌语言由于其字数有限,且要求高度凝练,一般尽量不用虚词,特别是连词、助词、感叹词等,而散文则无此禁忌。郑孝胥诗歌使用虚词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送檉弟入都》:“吾今之所行。” [1](P18)《冬日杂诗》:“乃于瞥然际,而作攫取想。” [1](P23)《述哀》之五:“其故独何欤”。“畏疾而馮河,哀哉岂此愚。” [1](P119)《三月初一晓》:“亡者果已矣,何用期遐龄。” [1](P358)《陆文烈公(钟琦)文子遗墨卷书后》:“事败成忠孝,而亦能感人。” [1](P385)《述怀》:“国侨以治郑,葛亮以治蜀。” [1](P417)《寄弢庵》:“太公归乎来,避纣岂长策。” [1](P424)《与立村谈沈文肃事》:“《鲁论》不熟乃至此,哀矜勿喜岂忘之。”“滥刑则不仁,近名则不义。奈何以儒生,而欲为酷吏。” [1](P475)《石遗卒于福州》:“石遗已矣何所遗,平生好我私以悲。”“勇哉子曾子,得正斯可毙。” [1](P478)由上述诸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郑孝胥诗歌大量使用虚词如连词、语气助词、结构助词、衬音助词、感叹词、副词等虚词,使得诗歌的前后两句之间意脉更加连贯,语气、音调更加顿挫多变,摇曳多姿,打破了诗歌语言的常规,呈现出散文化特点。
五、风格清苦幽寂
郑孝胥诗歌呈现出清苦幽寂的总体风格。这首先是由其内容特点决定的。如前所言,郑孝胥诗歌表现了晚清人的一种末世心态,在兼济与治平的层面上,对政局的内外交困感到担忧,对道德风气的日益沦丧感到伤怀,对朝中的人才缺乏、回天乏术感到焦虑,对神州的日渐陆沉感到绝望。在独善与修齐的层面上,亦多壮志难伸、老大迟暮的自伤与哀叹,以及挽悼亲人的长歌当哭之作。由此,形成了郑孝胥诗歌内容上清苦的特点。在艺术上,郑孝胥诗歌意象孤独、幽寂,而且主观色彩非常浓厚,常常是以我观物,将其末世心态与顾影自怜的哀伤投射到写景状物之中,写心的成分常常超过客观描写,这样,也更加凸显其诗歌的情感色彩。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造就了郑孝胥诗歌的清苦幽寂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