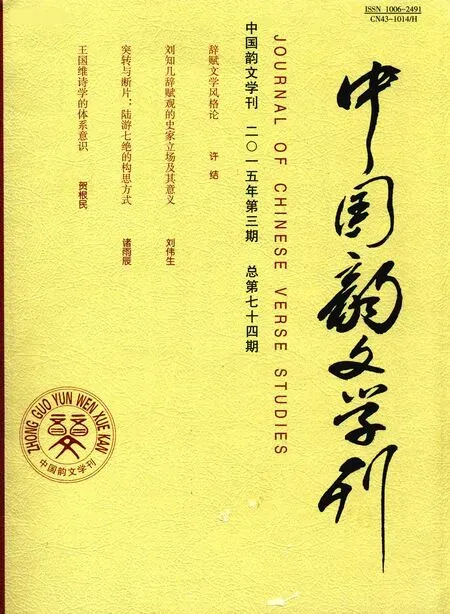欧阳修诗学理论疏辨
2015-11-14周建军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001-07
*作者简介:周建军(1966- ),男,苗族,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欧阳修虽为人为学都是韩愈的忠实追随者,但在对诗歌的态度上,却明确反对韩愈“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的作风, [1](1957)虽和梅尧臣分工“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 [1](P745)自始至终从没消退过对诗歌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的高度热情,他不仅以九百多首诗的创作实绩,成为北宋中期诗风革新的重要代表之一, ①而且首创《诗话》一体,在众多诗文中开展广泛、丰富而活泼的诗学批评,为宋代诗歌的走向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欧阳修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其《诗话》中,另还散见于《归田录》、《笔说》、《试笔》以及书、简、奏、启、序、记等诸多文章以及大量的交游诗里。总体来看,欧阳修的诗学观念和理论主张是在梅尧臣的诗学观的启发下形成的。不过,在梅尧臣的影响下,欧阳修的诗歌观念只是形成了初步的雏形,随着自身诗歌实践的不断积累和诗会活动的不断丰富,欧阳修的诗学观又带有了明显的个性化倾向,甚至有了对梅尧臣的诗论观和而不同之趋势。总体上看,欧阳修具有对诗歌从内容上振流拔俗、革故鼎新、从形式上进行开拓创新的强烈愿望。
一、对苦吟、诗理、诗典的独特发微
首先,和幼年启蒙时对晚唐诗歌的接受相关,以及自己孩提苦难的成长经历的影响,欧阳修思想深处,始终积淀着对苦境、寒荒的缅怀。因而在评诗上表现出对孟郊、贾岛、李贺甚至一些诗名不显的苦吟诗人的偏好,以及对苦吟风尚刻意讲究诗眼、妙句、炼字等诗歌手段的极力推崇,强调精妙诗句的取得往往是勤奋、敏晤和才情的综合结晶,若勉强造境,为诗难工。如他评诗曰:
余尝爱唐人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末,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煦,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读之便觉欣然感发。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 [1](P1982)
唐之晚年,诗人无李杜豪放之格,然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犹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在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也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1](P1952)
在第一节评论中,撷取晚唐温庭筠《商山早行》、中唐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中精警的诗眼句子进行品鉴,从两个选例看,欧阳修主要膺服于温、严二人都通过精粹的物象选择、打破常规的句型构造,来塑造打动人心的诗歌境界,用“画工小笔”来形容他们的雕琢之功。第二节评论,引晚唐周朴《春宫怨》、佚题诗句为例, ①主要推崇其“精意”和“雕琢”,也就是诗歌内容的清纯脱俗,句式构造的匠心独运。细品他两节诗评中所选之例,其寄托物象都是自然天籁之原始状貌,绝无俗世纤尘之染,句式都采用名词与动词、形容词的精准搭配,在自然流淌间一字出神,也就是锻句炼字之功。欧阳修诗歌审美趣味之高雅和精到,可见一斑。只不过由于“诗话”的随意性,没有展开阐释,以致引来洪亮吉“欧公善诗而不善评诗”、潘德舆“浅学不能喻”等吹求之诮。 ②
有人论及欧阳修对诗歌语言锤炼的追求时评曰:
欧阳文忠公酷爱鲍溶诗,《山中寒意》一篇最佳,云‘山深多悲风,败叶与林齐。门遥非世路,何人念穷栖。哀风破山起,夕雪误鸣鸡。巢鸟侵早出,饥猿无时啼。晨兴动烟火,开门伐泳溪。老树寒更瘦,阴云晴更低。我负自力求,颜色常低迷。时想灵台下,游子正凄凄。’文忠晚得,恨见之迟,今人少爱溶诗者。 [2](P153)
所赏诗例的确堪称诗中上品,为表现隐士鲍熔之苦寒情境,诗歌用词遣句极为精到传神。尤其“老树寒更瘦,阴云晴更低”,将温度、光线的变幻给人造成的形体、距离错觉精准而艺术地表现了出来,与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异曲同工而更显雕琢之功。此例从整首诗歌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欧阳修审美视角的独到。
考察《全集》,他所最为称道和偏爱的唐代诗人,往往是些政治上无关显达,诗名上并无隆声,沉湎于山林江湖之间,追求纯粹诗性生活的僧人和隐士,如常建、郑谷、周朴、贾岛、鲍溶、温庭筠、严维、九僧等。而他们诗歌的共同特征,就是对语言句式的进行苛刻的雕琢打磨,用精粹的语言句式,撼动人们的心神。
其次,在强调雕琢的同时,欧阳修还强调诗歌意境构造要合乎情理,不能造境而违理。故其《诗话》云: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燕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1](P1954)
其《笔说》云: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圣人之所以不言也:磁石引针,螂蛆甘带,松化虎魄。 [1](
P1970)
其《试笔》称:
谢希深尝诵《哭僧诗》云:“烧痕诗入集,海角寺留真”,谓此人作诗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谓好句亦好意矣。贾岛有《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唐人谓烧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再次,反对西昆体和时下诗人浅俗的诗歌表现。对西昆体用典成风、追求冷僻晦涩之学者型的作诗方法,提出中肯的批评。 [1](P831)对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西昆体唱和诗的生僻用典,明白地加以反对,但又不一味地反对用典,认为在精思博学的基础上,适当用熟典,未尝不可;但对改造前人诗句入诗,则持断然的鄙视态度:
如其《诗话》云: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 [1](P1955)
其《笔说》云:
“空梁落燕泥”未为绝警,而杨广不与薛道衡解仇于泉下,岂荒炀所趣止于此邪?“大风”、“飞云”信是英雄之语也,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终非己有,又何必区区于窃攘哉! [1](P1968)
二、对诗歌韵律崇险尚奇,劲折跌宕的气势之偏爱
仁宗时期,天下承平日久,以才子文士为主干的统治阶层,大多沉湎于歌场宴会之中,酒酣耳热之际,歌诗酬唱,成为当时颇为风行的交际方式。而仁宗本人,亦热心其中,且因为娱乐之初衷,有意将诗歌朝着难韵、险韵的方向导引,推动诗歌朝着纵才使气的方向发展,据清胡寿芝《东目馆诗见·倡和》卷二载:“仁宗险韵诗,臣下艰于和。多具表求免者;否则,亦诮徘徊太多矣。”在当时诗坛如战场的现实条件下,欧阳修自觉不自觉地需要俯仰其间,凝心静气地探索诗歌尤其是长篇歌行体的艺术规律。
欧阳修气高才雄,识见阔大,加上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他的诗歌创作在体式和音韵上,都显示出不同于同时代人的开拓意义。
欧阳修除诗歌之外,一生还酷爱琴、酒,热衷“鸣琴酌酒留嘉客”, [1](P831)长期的乐僻和频繁的歌宴酒会,使欧阳修具有较高的音乐修养,如其《论乐说》尝诘:“清浊二声为乐之本,而今自以为知乐者犹未能达此,安得言其细微之旨?” [1](P1985)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学审美和诗歌创作,使他对诗歌的音乐之美感受尤深,认为一个时代诗歌的成败和一位诗人诗歌的优劣很大程度上系根于诗歌的音乐韵律和节奏。故其在文中阐述:
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 [1](P1048)
和散文提倡博取众长,反对趋奇趋怪的态度不同,欧阳修极力推崇诗歌境界的雄浑气势、节奏韵律的劲折跌宕、意象情感的奇险和张力,注重诗歌艺术化的表现力。
如他在诗中称赏苏舜钦之诗、书:
……是以子美辞,吐出人辄惊。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众弦排律吕,金石次第鸣。间以险绝句,非时震雷霆。两耳不及掩,百痾为之醒。语言既可骇,笔墨尤其精。少虽尝力学,老乃若天成。濡毫弄点画,信手不自停。端庄杂丑怪,群星见欃枪。……使我终老学,得一已足矜……。 [1](P752)
……子美气尤雄,万竅号一噫。有时肆癫狂,醉墨洒霶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 [1](P28)
在悼亡诗中称道石延年的诗歌:
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轩昂惧惊俗,自隐酒之徒。一饮不计斗,倾河竭昆墟。作诗几百篇,锦组联琼琚。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麤。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诗成多自写,笔法颜与虞。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余,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 [1](P19)
在《诗话》中,他明白表达对韩愈诗歌之倾慕主要落在工于险韵上: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欤?坐客皆为之笑也。 [1](P1957)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对李白最为膺服,在一些场合表现出一定的崇李抑杜的倾向,如其论李杜诗: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故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1]( P1968)
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李杜诗才的比较不是从全方位来考虑的,侧重于从诗歌奔腾张放的气势,跌宕劲折的节奏上来评价。正是因为他对李白诗歌的气势和节奏的情有独钟,故其在自己的诗歌中尽量推崇并模仿太白体诗歌。如其诗称: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① [1](P86)
虽然这种戏言式的唱和诗带有明显的随意性,甚至为表达写作时刹那间的某种情感而有背于一贯的初衷的现象,如他此诗为了表现对李白诗歌天造地设的磅礴气势的景仰,却有意将同样作为自己追摹对象的孟郊和贾岛作为排抑对象便是如此。
诗话体例的随意性,也更真切细致地透露出诗人不加伪饰的审美趋向和诗学追求,由于欧阳修独特的诗歌探索历程和心理情感机制,使他诗歌关切的着眼点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有所不同,表现出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的倾向。明代毛晋《六一诗话跋》中称:
六一居士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凡《诗话》褒讥,亦多与前人相左,非好为已甚也。其自道云:“知圣俞诗者莫如修。尝问圣俞举平生所得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称赏。盖知心赏音之难如是。”其评古人诗,得毋似之乎? ② [3](P631)
此说虽然有突出欧梅的诗歌审美趣味相对立的倾向,且其所引欧公之语纯属伪造, ③但其强调欧阳修诗论提倡独到心会、别处心裁,却是中肯的,从总体上看,欧阳修论诗重意轻形、注重气格,对苏梅之诗极为推崇,却又有自己独到的悟见。以至叶燮以“狂”和“狷”来归结他和苏梅之间的同声而异调:
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汉魏至晚唐,诗虽递变,皆递留不尽之意,即晚唐犹存余地,读罢掩卷,犹令人属思久之。自梅苏尽变昆体,独创生新必词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类以赴之,竭尽乃止。才人伎俩,腾踔六合之内,纵其所如,无不可者;然含蓄停泓之意,亦少衰矣。欧阳修极服膺二子之诗,然欧诗颇异于是。以二子视欧阳修,其有狂与狷之分乎? [4](P605)
从欧阳修对自己诗歌创作的评价来看,他最为得意之作为和王安石的《明妃曲》和仿太白而作的《庐山高》。史料载:
前辈诗文,各有平生自得意处,不过数篇,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毘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文忠子棐以乌丝欄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也。 [5](P424)
我们不妨对其自诩超李杜的《庐山高》一诗稍作考察,以略窥其诗学追求的旨趣。
庐山高哉,几千仭兮,根盘几百里,岿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里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青苍以晻霭,下压后土之鸿厖,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窺空谾。……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玒,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其气兀硉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
此诗和李白《蜀道难》、韩愈《嗟哉董生行》 ④的创作心态与情感机制大体一致,其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段可感受到李诗影响的痕迹,但又渗透着韩诗豪怪险崛的影子,既讲究奔腾的气势,又注重吞吐回环,既追摹李白的汪洋恣肆、一泄千里,又融入韩愈趋奇好险,排戛跌宕的风格特征,糅太白之高朗豪迈、韩愈之奇险劲折于一体,又将描写、抒情和议论等艺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也许此诗正是苏轼“诗赋似李白”、 [6](卷三四)陆次云“其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 [7](卷上)诸论的重要缘由所在。但运用骚体句式杂于其间,又是其试图超越李、韩,将此种古乐府体远追《楚辞》的匠心独运,标新立异的表现,翁方纲称道:“庐山诗,欧阳子一篇最著”。 [8](卷三)但细致考察欧阳修的全部诗歌,我们会明显感觉到它并非欧诗中的上品,它古奥有余,而诗味不足,刻意效仿李白、韩愈歌行体诗之气势、节奏,而缺乏李、韩诗歌之内在情韵和深邃,有明显的斧凿痕迹,也许正是对韩愈思想和文学家数的顶礼膜拜之原因,造成他诗评观的局限性,引得后来学者对其诗学观的怀疑和困惑。如王士祯评:“《庐山高》一篇,公所自负,然殊非其至者。” [9](卷四)“自诩《庐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属中下。甚矣,知人知己之难也!” [10](卷二)翁方纲提出:“七言歌行,以极长之句,杂以骚体,中插三言、四言,皆所不难。独中间插入七言整句一联,则颇难合拍。虽以欧公《庐山高》,尚未免以气胜压人也。求于此等处拍出正调之七言,而从容中节毫无强拗盖洵所罕见。所以渔阳极不劝人为此”; [8](卷五)“欧公有太白戏圣俞一篇,盖拟太白体也,然欧公与太白不同调,此似非当家之作,《庐山高》亦然”。 [8](卷三)
三、强调创作环境和创作心态对诗歌成就的决定作用
自《史记》“发愤著书说”开论以后,对于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日渐成为历代学人热议的话题,尤其中唐韩愈在自己真切感受的基础上,首次将此问题纳入诗歌领域加以探讨,其《荆潭唱和诗序》明确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11](卷二十)便是针对诗歌而发的。欧阳修曾和梅尧臣讨论过“诗穷”问题,尤其结合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对古代尤其是晚唐穷苦诗人的考察,和对当时作为诤友的梅尧臣仕途偃蹇、生活困顿的境况的感受,欧阳修逐步得出了“非诗能穷人”、“穷者而后工”的一系列诗学理论观点:
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篆穷苦之言以自喜。或问二子其穷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诗见之。郊曰“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岛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盖孟氏薪米自足而岛家柴米俱无,此诚可叹。然二子名称高于当世,其余林翁处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见于数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怡,人情和畅,又有言不能尽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1](P1981)
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圣俞以为知言。铭曰:不戚其穷,不困其鸣不踬于艰,不履于倾,养其和平,以发厥声,震越浑鍠,众听以惊,以扬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诸冥。[1](P496)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P612)
欧阳修极力倡导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引起同时代及后代学者、诗人的广泛争议。认同者奉为至理,大加弘扬,如苏轼《答钱济民三首》:“人来领手教及二诗,乃信北归,灾退并获此佳宠,幸甚幸甚!又知诗人穷而后工……”。 [6](卷八五)“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 [6](卷五)是直接秉承其旨,后又有程大昌、陈师道、李纲、卫宗武、方夔,明代唐元竑、黄仲昭,清代陆莹等,争相鼓吹,晚清曾国藩“盛世巨公,其诗不及衰世之孤臣逐客,庙堂卿相,不及穷巷憔悴专一之士”, [12](序)更是此说之远代嗣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因循此论或加以张大。但是,由于此论不能完全精确地对应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体轨迹,因而也引起诸多质疑或否定之词,如陆深、翁方纲、姚鼐、李元度等。 ①
欧阳修绝不是率意而发此论,之所以为然,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现实条件。首先,欧阳修“孤于绵、长于泰”的孩提遭遇,给他提供了反刍穷苦的基本土壤,芦杆画地而为学,也是从苦吟诗人入手的。其次,欧阳修此论,主要是以作为诗歌最鼎盛王朝的唐代为参照的,纵观唐诗,如果从诗歌创作对技巧手段的讲究、诗歌境界与诗人心性精准契合来看,晚唐诗人的确有胜于初盛中唐诗人,正是以穷苦诗人为主体的晚唐诗人,将一代唐音推向了艺术极致。再次,欧阳修此论主要是针对堪为诤友的梅尧臣的遭际而在《梅圣俞墓志铭》、《梅圣俞诗集序》两文中细致阐发的。梅尧臣乐易仁厚,才气横溢,却长期沉于下僚,在欧阳修、赵概等的援引举荐下,官终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修在《诗集序》中较详细地阐述了此论的触发点:
予友梅圣俞,少以阴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尤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1](P612)
可已看出,欧阳修在发此论之际,是抱有一定的情绪的,其间既包含着对梅尧臣的深知,也饱和着对梅尧臣遭遇的同情,更隐含着对有司阻抑的愤怒。所以在发论之时,也许存在过于夸大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的对诗歌的决定作用,因而引得后世诸多讪讥,如清代王棻就曰“欧阳子乃谓‘穷而后工’,其论褊矣。” [13](卷十,序跋四)
四、追求诗歌风格的闲远古淡,讲究诗歌旨趣的兴味无穷
宋人讲究诗歌的闲远古淡、言意之旨的审美取向开源于苏舜钦,由于他多与佛徒交游论诗,故在其诸多切磋诗艺的诗歌中表现出对这种艺术境界的孜孜追求。如《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正声今遁矣,古道此焉存。商缓知臣僭,风薫见帝尊。雄豪尚余勇,淡泊忽忘言。繁极殊无间,来长若有源。已能通变化,直可探胚浑。此理师应得,西风独掩门。” [14](卷八)《赠释秘演》:“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 [14](卷二)《诗僧则晖求诗》:“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 [14](卷八)但对这种诗歌境界的开掘和实践,是由梅尧臣来实现的。《直斋书录解题》称:“圣俞为诗,古淡深远。” [15](卷一七)《宋史》称:梅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 [16](卷四四三)《四库总目》称:“佐修以变诗体者,尧臣也。……然尧臣诗旨趣古淡,知之者希……惟欧阳修深赏之。” [17](P2054)但真正在创作和理论上都一以贯之的是欧阳修,欧阳修通过与苏舜钦、梅尧臣之间长期的倾心交游,诗文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审美趣味,推崇诗歌应在质朴古拙的境界里,蕴含深厚的耐人回味的诗趣,进而提升为对诗歌“真味”和“奇趣”的追求,间接表现出对宋初白体诗人以来浅率作风的轻视。
其《诗话》载:
圣俞尝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缾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
仔细剖析此段论述所包含的诗学理论成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认为诗歌创作要“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也就是强调诗歌创作不能简单地因袭前人,要善于开掘新的题材,用精粹的语言构筑出崭新的审美境界,表现出对诗歌语言和意境的创造性、开拓性的特别关注。其次认为诗歌要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诗人对景物要有敏锐的感受力,诗意表现要婉曲靖深,余味悠长,给人留下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要达到这些,物象的选择极为重要,从欧阳修所推赏的所有例句例诗来看,他最为垂青的是古淡朴野、肃如天籁、清如寒塘,又往往为一般诗人所忽视的原生态物象,如“竹笼”、“山果”、“瓦缾”、“石泉”、“老树”、“山鹿”、“鸡”、“野禽”、“槐根”、“马骨”等物象,都古拙淡雅、不着铅华,这些物象通过精准的动词、形容词的勾连,就能创造出灵光一闪,恍然大悟、余味悠长的艺术效果。在欧阳修的诗文中,常常表达他对这种诗歌境界的执着追求却总难如愿之遗憾:
……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羮岂须调以荠。怜我区区欲强学,跛鳖曾不离污泥。问子初何得臻此,岂能直到无阶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惮入海求灵犀。周旋二纪陪唱和,几翼每并鸾皇栖。有时争胜不量力,何异弱鲁攻强齐……。 [1](P82)
……作诗三十年,视我尤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1](P29)
另据史料载:
王禹偁《橄榄诗》云:“南方多果实,橄榄称珍奇。北人将就酒,食之先颦眉。历口复弃遗。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欧阳文忠公曰:“甘苦不相入,初争久方知”极快健也,胜前句多矣。 [18]
欧阳修在《江邻几墓志铭》一文中称道:“其为文章淳雅,尤长于诗。淡泊闲远,往往造人之不至。” [1](P500)在《题青州山斋》一文中,更较为细致地描述了他时至晚年,由于心力所限而难臻此境的悲凉:
吾尝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晚来青州,始得山斋宴息,因谓不意平生想见而不能道以言者乃为己有,于是益欲希其仿佛,竟尔莫获一言。夫前人为开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称其怀,岂人才有限而不可强?将吾老矣,文思之衰邪?兹为终身之恨尔。 [1](P1065)
欧阳修的诗学观有着明显的时代意义:首先,在西昆体诗风弥漫,整个诗坛趋之若鹜的背景下,欧阳修能整合苏舜钦、梅尧臣等诗学同道新辟之见并发扬光大,为宋诗朝古朴典雅、重视余味和理趣,在平易中追求锤炼的方向发展,开辟了新路,矫正了西昆体诗人单纯在典故和学问中兜圈子,在前作和遗编中拾取芳润的时下作风,为北宋诗风丕变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次,开创了诗话批评的先河,为后来日渐风靡的诗话体式,提供了最原始的示范;再次,欧阳修诗学理论,给后来的欧门弟子如苏轼、曾巩、黄庭坚等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权威的方法论指导,为北宋诗歌高潮时代的到来,起了具体的推动作用,如有人评宋人的诗学成就时称:“宋人承唐人之后,而能不袭唐贤衣冠面目,别辟门户,独树壁垒,其才力学术,自非后世所及。如苏、黄二公,可谓一朝大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半山、欧公、放翁,亦皆一代作手,自有面目,不傍前贤篱下,虽远逊东坡、山谷两家一格,亦卓然在名大家之列。” [19](卷二)虽力推苏、黄之功,但亦旁及欧公,且二子均系欧门嫡传,其诗学精髓皆直承于欧,欧之影响,不言自见。然后人亦有极贬欧阳修之诗论者,如潘德舆曰:“《六一诗话》所载圣俞《河豚》、《春雪》二诗,皆非至者。公许《河豚》诗为绝唱,惟首二语‘春州生荻芽,春岸飞杨花’差可无忝,余则有韵之文耳;许子美《新桥对月》诗‘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为雄伟称题,尤不可解。且而公佳诗甚多,略而不录,而所赏在此万万非浅学所能喻也。” [20](卷七)未考究欧阳修诗学观之全貌,断章取义,未免有吠影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