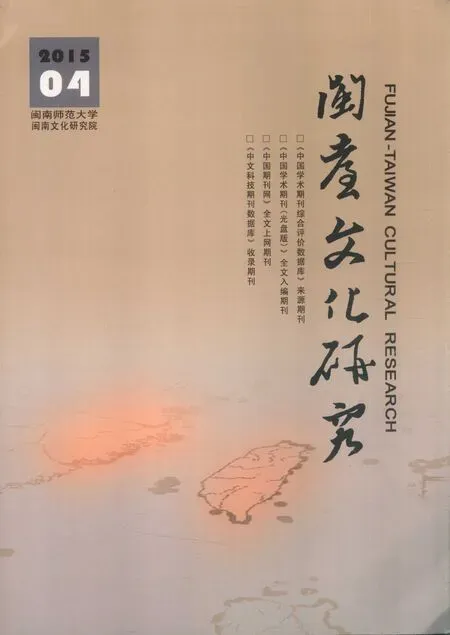国家符号与地方社会:獭窟岛双忠信仰的历史文化考察
2015-11-14陈尊慈
陈尊慈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0)
国家符号与地方社会:獭窟岛双忠信仰的历史文化考察
陈尊慈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0)
獭窟岛的双忠信仰肇端于宋元之交。其时,追随宋端宗南逃的洪氏先祖等人为了“护驾”,开始在井亭宫供奉双忠香火,井亭宫由此成为獭窟当地带有特定政治和“正统”色彩的“忠臣之庙”。明清以后,随着獭窟社会的不断转型,双忠信仰的“正统”色彩虽然得到了当地士绅们的推崇,但獭窟人也对井亭宫及其双忠信仰的历史记忆进行了有选择的加工和改写,“忠臣之庙”及其“正统神明”逐步走上了“地方化”道路。
獭窟岛;双忠信仰;历史文化考察
双忠,又称文武尊王,在泉州的安溪一带则称为尪公,通常是指唐朝的张巡和许远两位忠臣。史载,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张巡和许远因守卫睢阳城而身殉安史之乱,之后被立庙奉祀,且历代都享有香火。
泉州是双忠信仰极为普遍的地区,全市各地都有许多奉祀张巡和许远的宫庙,其中,仅市区就有24座。由此可见,双忠信仰在泉州传统的祠庙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相对于同样是民间信仰的妈祖、关帝和保生大帝等其它神祇,在既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对泉州地区的双忠信仰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迄今为止,无论是对当地双忠信仰的整体考察或是个案研究都没有太多的学术成果。为此,本文拟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泉州獭窟岛双忠信仰的由来和演变,以及这一信仰曾经作为当地的国家象征符号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试作一番探讨。
一、獭窟岛双忠信仰的由来
獭窟是泉州湾湾口的一个海岛,又名浮山、獭江,土地面积2.3平方公里,居民5000人左右,原本隶属惠安县,现在则是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的一个行政村。獭窟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港口,港内有前澳、后墓垵、后海坪三个港区,自宋、元开始一直到民国期间,这里都是泉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70年代,獭窟开始围垦建造海堤,从此变成了一个半岛。
獭窟的双忠庙位于东峰自然村,是一座由门厅和大殿组成的具有闽南传统风格的合院式建筑。该庙大门的匾额为“忠臣庙”三字,左右侧门则分别挂有 “双忠”、“睢阳胜境”和“古庙”、“井亭古地”的匾额。尽管有“忠臣庙”的庙额,但是,当地人一般都俗称该庙为井亭宫。而且,1998年重修该庙时所立的两方碑记也将其称为“井亭宫”或“井亭旧宫”。这两方碑记分别为《井亭旧宫述胜》和《井亭宫重建志》,根据碑记记述,獭窟双忠庙的庙址原为唐代僧道的修炼之所,宋天禧三年(1019),僧人道洵又重新设计改建,并“掘七井成北斗状”,井亭之名由此而来。
井亭宫原本并不是双忠庙,先前也没有双忠的香火。那么,这里究竟何时开始奉祀张巡和许远?关于这一点,上述碑记和地方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而调查中,当地人却都说,井亭宫是宋代开始才由洪氏在这里供奉张巡和许远。
历史上,张巡和许远自从唐肃宗时被褒封并纳入祀典之后,北宋时也于汴京立庙。而且有宋一代关于双忠显灵阴助宋帝的传说也层出不穷。如宋淳熙九年《建东平忠靖王庙》中记述了张巡曾阴助宋太祖事迹;又如南宋高宗南逃避难明州时,“幸奉国楼,金兵及之,见张许南姚雷五公帜,又布蛛网楼门,金谓无人乃退”等。因此,双忠信仰在宋代不仅继续得到了朝廷的提倡,而且还不断向南方扩展,泉州地区的万安飞炉庙和安溪凤山忠义庙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调查发现,獭窟现有居民中并没有洪氏,但在民国以前,洪氏却是獭窟的主要姓氏之一。不仅如此,清康熙年间,洪氏家族中有一位叫洪崑的读书人有感于獭窟“乌可无志”,便抱持着赤诚的乡土情怀撰写了《獭江新考》一书。洪崑在书中对自己的家世留下了这样的记述:“洪氏,世居梁山之下,崑之族也。自宋末航海时,来家于此。”无独有偶,在洪崑之后,另一位叫做曾枚的獭窟人又于光绪年间撰写了《獭江所知录》一书,书中也有关于洪氏“祖宋官进义郎,于端宗航海时,家獭江,居梁山下”的记载。在这里,洪崑和曾枚都说洪氏是在“宋末航海时”或是“端宗航海时”迁徙到獭窟的。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洪崑关于洪氏“自宋末航海时,来家于此”的记述,还是曾枚关于洪氏“于端宗航海时,家獭江”的记载,字里行间,说明的不仅仅是洪氏迁徙到獭窟的时间,他们同时又说明了洪氏迁徙到獭窟的原因。质言之,洪崑和曾枚分别以“自宋末航海时,来家于此”、“于端宗航海时,家獭江”行文,而不以“自宋末时航海,来家于此”、“于端宗时航海,家獭江”叙事,他们都涉及到宋元更替之际,宋端宗赵昰南逃时发生的“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这一件事件,而这一事件又与獭窟双忠信仰的肇端有着直接的联系。
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十一月,元兵由浙江攻入福建。为避元军,陈宜中、张世杰“率舟师十万”护送宋端宗赵昰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并“欲作都泉州”。然而,在蒲寿庚的把持之下,却发生了“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除了元代泉州僧人释大圭的《筑城曲》,明清两代的方志也多有记载。如,明何乔远《闽书》记,“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宋幼主过泉州,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以上记述,虽然对于宋端宗南逃泉州的过程说法不尽相同,比如,有说蒲寿庚“闭门不纳”、“闭门拒命”,也有说“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但宋端宗一行被当时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蒲寿庚拒之门外、甚至被其追杀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正因为如此,曾枚的《獭江所知录》又进一步记述到:“景炎元年,端宗航于泉州港,值蒲寿庚作乱,与元将唆都犯帝舟,因改泊外渚,即獭江,忽濛烟蔽海,咫尺莫辨,庚惧不敢迫”。在曾枚的记述中,宋端宗不仅因为“蒲寿庚作乱”而到过獭窟,且因为“忽濛烟蔽海,咫尺莫辨,庚惧不敢迫”,从而在此地得到了停留喘息的机会。
除了曾枚的记述,在獭窟居民中也流传着不少与宋端宗有关的传说。相传,当宋端宗一行逃至獭窟澳仔口时,当地就有人发动过“护驾”,于是獭窟的澳仔口又被称为“护驾澳”。而且,当地还传说,端宗登岛之后,见獭窟“景色秀丽,环山曲水,有如困龙在田,左有金墩(烟墩山)障其流,右有玉盘(大磐石)阻其潮。远近叠峰峻岭,争相拱峙。屹然若士笏而朝,深为叹息:‘此地真如我江山’”。此外,獭窟西峰境别称“西安”,也传说与宋端宗有关。对此,有报道人回忆,在已散失的《西峰曲江张氏族谱》中就记述了宋端宗在獭窟时,见西峰风光秀丽,遂将西峰称为“西安”。该报道人还回忆,清代獭窟人曾作楫文集中,也有当年西峰人发动保驾,宋端宗由此获得了安全,于是将西峰改呼为“西安”的记载。不仅如此,曾枚的《獭江所知录》还记述了宋端宗在即将离开这里继续南逃时,曾经“口占《踏莎行》一阕与居人别”。虽然该词今日已无从寻觅,但在獭窟却又流传着另一首名为《帝子吟》的七言诗:“一叶孤舟逐水轻,西峰山下驻行旌。半帆月色家千里,两岸渔歌酒百斟。树紫暮烟成画景,江涵夕照浴波金。当年赤壁高吟处,今日为君再咏吟。”诗中,“西峰山下驻行旌”一句,描述当年宋端宗一行在西峰驻扎的情形;而“当年赤壁高吟处,今日为君再咏吟”之句,则以《赤壁赋》中苏轼对周瑜人生起落的感怀,来类比獭窟人对宋帝命运的同情。
根据以上文献和口碑资料,我们认为:一、南宋末年流亡的宋端宗及其小朝廷确实曾经在獭窟停留过。二、作为“祖宋官进义郎,于端宗航海时,家獭江”的洪氏,也极有可能就是当年宋端宗南逃时的随臣;而他们之所以 “家獭江”,没有继续随宋端宗南逃,“舟不足”极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三、在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宋端宗及其小朝廷以曾经阴助前朝抗金而屡有神功的双忠作为精神激励,从而在獭窟号召效忠、“发动护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獭窟当地人关于双忠香火是宋代由洪氏族人开始奉祀的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獭窟岛双忠信仰的政治和“正统”色彩
如前所述,獭窟的井亭宫原本并不是双忠庙,之前也没有双忠的香火。而随着宋端宗及其小朝廷在獭窟的 “驻跸”,追随和效忠于宋室的洪氏先祖等人才开始在井亭宫奉祀双忠香火,从而开启了獭窟岛双忠信仰的先河。因此,獭窟双忠信仰从建立开始就具有了国家象征符号意义的、特定的政治和“正统”色彩。而联系獭窟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我们又不难发现,在宋代之后,当地双忠信仰的这一意识形态色彩也有过多次得到强化的机会。
据《獭江所知录》记载,獭窟在唐代之前是一个“人未有问津者”的边陲海岛,虽然“有宋南渡,江浙人避难入闽者沿海托迹,由是獭之居人稍盛”,但政府的行政力量并没有完全普及到这一地带。明清两代是獭窟社会逐步转型进而被纳入国家体制的关键时期,尤其在明初,獭窟当地有了正式的基层行政建制,成为惠安县二十六都獭窟铺。明洪武年间,倭寇开始侵扰泉州,“江夏侯周德兴为防海寇入侵,在獭窟建造卫城,并设立巡检司,领弓兵百名”。巡检司的设立使得獭窟开始成为泉州重要的海防门户之一。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据《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记载,“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獭窟成为政府指定的与台湾对渡的港口。光绪年间,清政府出于加强对外贸易管理的需要,又在獭窟设立海关关卡,獭窟关遂成泉州常关所设的十个分关卡之一。与獭窟社会的逐步转型相对应,明清两代,政府对双忠信仰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代,“丙子命有司立张巡、许远庙于归德州,岁时致祭,洪武正韵书成诏颁行之”,朝廷将双忠信仰列入国家祭典。而清代更将张巡、许远的塑像请到太庙,名列41位历朝名臣之中。因此,在獭窟,带有官方正统色彩的双忠信仰在当时也得到了当地士绅们的更多推崇。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洪崑《獭江新考》下面这段记述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张巡庙:在梁山之阳。
洪崑曰:忠臣之在于天下也,虽万世如一日也。盖天理在民心,惺惺不泯,忠则慕之,否则斥之,顾慕之不已,为之立庙,立庙不已,为之塑像,乃至血食相延,世世不绝,势与天地相为长久。呜呼!大丈夫立身一正,千载如生。原其初,亦不过自尽乃心,平常之事耳,非有高远难行之举,奈何庸众人不能自尽,豪杰之士尽之。旷观宇宙不一生,遂使中庸易而难能,而忠臣之庙亦竟以罕而见珍,顾不惜焉。吾獭庙宇数数见皆非中义之举,吾所不取。独张先生一庙俨然可亲,同志之士,时常伏谒。夫先生之庙遍天下,岂特海隅苍生,闻风思慕?然号为人者,莫不各有是心,虽一乡善人,犹思则效而况忠义之士也哉?此吾所谓天理之在民心也。今特记张先生一庙,别有异于众。又己卯年尝有诗题其庙,今亦补入。《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后人之谓欤?
题张睢阳庙诗云:
剡蒿志不小,朝像义何深。齿折江淮冷,城危天地阴。英风吹死简,忠血染人心。所以文丞相,为公千载吟。
洪崑所说的“张巡庙”即是井亭宫。比较特别的是,井亭宫是洪崑《獭江新考》中唯一着墨“特记”的庙宇。其原因,洪崑认为,井亭宫相较于獭窟其他宫庙独具“忠臣之庙”的特殊性。而双忠所代表的“忠义之士”,又使其自成一类,“别有异于”獭窟其他“非中义之举”的地方神灵。因此,在洪崑看来,獭窟“独张先生一庙俨然可亲”。在这里,洪崑不仅系统地强调了双忠这一信仰的正统性,而且记述自己“己卯年尝有诗题其庙”,并与“同志之士,时常伏谒”。除了洪崑的这一自述,我们在《井亭宫重建志》“后记”中,还发现清康熙己卯年重修井亭宫时,洪氏家族捐地作为祭祀活动场所的记录。显然,无论是洪氏家族还是洪崑个人,或是洪崑的“同志之士”,他们的言行无不体现了当时獭窟士绅们向国家提倡的“忠义”等正统道德观念的自觉靠拢,他们无疑是延续当地双忠香火、维持双忠信仰“正统性”的中坚力量。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洪崑及其族人对待双忠信仰“俨然可亲”的态度,还与他们特殊的“家国”记忆密切相关。在洪崑的记述中,表面上看,双忠的忠义是“万世如一日”的,是超越了对某一个特定朝廷效忠的,是一种永远 “在民心”的“天理”。甚至,根据洪崑的解释,双忠所以被人们在獭窟立庙,是因为民心仰慕忠义,因而为其立庙、塑像,“乃至血食相延,世世不绝”。但如果结合他为该庙题写的诗句进行分析,我们又不难发现诗中所隐藏的特殊的自我情感。“所以文丞相,为公千载吟”,这是诗中的结尾之句,指的是文天祥被元朝关押燕山时,写过颂扬张巡、许远的《沁园春》词和《许远》诗。《沁园春》最早收录于元凤林书院本《精选名儒草堂诗余》,该书为“亡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洪崑的诗至今仍被镌刻安放在井亭宫的墙壁上,这与潮州东山灵威庙的情况颇为类似。潮州东山灵威庙也是建立于宋元更替之际,在当时是一座颇具反元色彩的双忠庙。至元二十六年(1366),潮州总管王翰当年也曾经将文天祥的《沁园春》易名为“谒张许庙词”,并在灵威庙前镌石立碑。同时,当年灵威庙修建时的主事者赵嗣助本身也是参与过文天祥抗元活动的宋朝遗臣。由此可以推论,虽然洪崑为井亭宫题诗已晚至清代,但与灵威庙同样建立于宋元之交、同样位于宋端宗逃难路线、且同样特意镌刻与文天祥相关的诗作于庙宇之中的井亭宫,是否也同样寄托了洪氏族人“对于宋王朝的某种特殊情怀”?
此外,洪崑在《獭江新考》中还写到,洪氏在獭窟“垂伍佰年,世祀不失,诗书相续,然不甚光显,历代惟教官而已。”而查阅《獭江所知录》“治最”一卷中所叙的17位人物,有14位均出自洪氏,但这14位洪氏族人中,于元代入仕的仅有两位,且均为武学谕。其余的12位洪氏后人在明清时期也只是担任训导、学正、教谕等学官。一般而言,学官不直接参与机要,生活并不富有,与统治百姓的其他官员不尽相同,因而,历史上,以隐于学官的方式表达对“故国”的忠诚就成了许多“遗民”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推测,洪氏在獭窟定居数百年间对富贵功名的轻视,或许正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这一遗民意识和故宋情结。
宋亡之后,民众借助特定信仰迂回地表达对宋室尽忠的事例在泉州并不少见。如泉州市区和晋江青阳、深沪等地发现的日月太保信仰,奉祀的就是以赵昰和赵昺为原型的两尊“孩童佛”,当地人对外称两尊神像为保护孩童的神祇,而日月太保的神讳和真实身份则以口头形式流传。又如,元朝妈祖取代通远王成为最主要的海神之后,青阳石鼓庙福佑帝君(即通远王)的地位受到冲击,但当地百姓并未奉祀妈祖,而是以供奉石鼓庙主神顺正王的形式来怀念宋室。因此,结合前述对獭窟双忠信仰香火缘起的考证,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獭窟岛的双忠信仰和当时泉州的许多秘密信仰一样,是南宋遗民将其对故国尽忠的情怀隐于民间信仰之中,从而迂回留存下来的一段历史记忆,是当时泉州地方社会以象征、隐喻的方式对政治忌讳的一种暗中挑战。
三、獭窟岛双忠信仰的“地方化”道路
然而,双忠这一具有官方正统色彩的忠义之神,在獭窟普通百姓中是否也有着同样坚实的信仰基础呢?关于这一点,考察双忠信仰在当地人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我们或许就能解开这一疑问。
獭窟的地方神庙系统基本成型于民国时期,呈现出全岛性宫庙—境主庙—角头庙等三个层次。其中,公认的全岛性宫庙有浮山寺、西宫(妈祖宫)和夫子馆。浮山寺是獭窟唯一的佛教寺院,而西宫和夫子馆则因其灵力而从岛上众多庙宇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夫子馆,它于清末建成,年代并不久远,且其中供奉的夫子原先仅为私人会馆中的“私佛”,但因夫子屡次帮助渔民躲避海难,夫子馆便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所有岛民竞相朝拜的宫庙。在獭窟,拥有大批信众的除了上述“正神”之外,还有收纳海上无名尸骨的“大众爷”、由阴转为神的两艘船模“大巡伯”和“新大巡”等,他们的信众同样超越了“境”的界限,影响力也远超某些境主。而这些信仰之所以如此兴盛,唯一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灵验”非常。
在獭窟,井亭宫是井亭境的境庙。獭窟的境不见于方志和地方文书记载,但很可能由民间自发形成。獭窟共有六个境,它们分别是一个个以境主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獭窟人习惯于称双忠为文武尊王,而文武尊王最主要的神职是井亭境的境主。境主即是境的保护神,他们掌管境内的公事,是境的象征,而境庙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乡民的“自治机构”。在獭窟,境又往往与宗族相整合,呈现以某一大姓为主、周边小姓依附的社区形态,是一种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组织。对于作为境主的井亭宫文武尊王来说,他们决定公事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井亭宫“堆沙”这一习俗上。
井亭宫“堆沙”据说是一种最迟在清代就已经出现的、颇为独特的断案方式。根据调查,在獭窟所有宫庙中,只有井亭宫有“堆沙”的习俗,而且大多数獭窟人一谈起井亭宫,也总会立马联想到“堆沙”。据报道人介绍,古时候,当地村民若是丢了东西,常常怀疑邻里,最终东西没找到,还伤了和气。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每当发生失窃案,士绅们就到井亭宫扶乩,求助文武尊王帮忙。扶乩时,扶乩者写出“化干戈为玉帛”、“要善中求,不恶中取”之句,之后,士绅们在宫前放一个大木桶,桶里面先装些许沙子,桶上盖一块布,并叫那些被怀疑的村民每人拿一个小斗也到海边装沙,互相不可偷窥,不然会遭到神的责罚。小斗装满沙后,在斗上蒙一块布,带着斗到井亭宫,将沙倒入宫前的大木桶。通常,偷东西的人惧于神威,都会将所盗之物连同沙子一起倒入桶中。因此,每每揭开蒙布,人们都会发现失物已在桶中。“堆沙”断案似乎是井亭宫最主要的职能,也是当地人认为能寻回失物的最佳方式,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当时,由于政府严查鸦片,有岛外人就将鸦片送到管理相对松散的獭窟让人代为保管,后来鸦片遗失了,当地人同样也是用“堆沙”的方式找回。
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陈春声在对潮州地区双忠信仰的研究中指出:“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域的民众所接受,除了有待于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培养外,还常常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结合井亭宫“堆沙”事例,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獭窟的双忠信仰。
在獭窟,士绅们一方面像洪崑那样,强调着井亭宫双忠信仰相对于其他宫庙的正统特性,从而着力推行并寄望“忠臣之在于天下也,虽万世如一日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得借助最被民间社会所接受的通灵仪式和传达神意的方法,使双忠信仰不至于因为“曲高和寡”而丧失群众基础。通过井亭宫的“堆沙”断案,士绅们不仅延伸了“忠臣”的内涵,将文武尊王从国家的忠臣进一步塑造成为乡土社会明察秋毫的父母官,并且借助神谕,渲染了文武尊王的灵力,试图让民众相信,没有哪一位地方神灵,能比具有忠义品质的文武尊王更好地关注和解决民众生活中的一些棘手问题。井亭宫的“堆沙”断案,是獭窟双忠信仰进一步“地方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双忠得以“地方化”,则明显得益于乡绅们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巧妙地借用和重塑了双忠的“忠义”。这样,双忠信仰不仅成为“国家意识”在獭窟的象征符号,同时又扎根于岛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士绅们管理地方社会的工具。此外,为了进一步建立双忠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井亭宫在为文武尊王配神的设置上也走上了“地方化”道路。和妈祖宫、王爷宫等獭窟的其他境主庙一样,井亭宫中也配祀了保护妇婴的“太后妈”和看管宫庙的“黑狗爷”。同时,还供奉着一艘疑为其他地方举办“送王船”仪式后漂流至附近海域的船模——“船王公”。
尽管如此,在獭窟,士绅们对双忠香火的苦心经营一直面临着挑战,井亭宫的“地方化”之路也并不十分顺畅。獭窟地理偏僻,与大陆若即若离,政令或张或驰,自古就是私商活跃之地。加上明清以来多次兵灾、迁界和禁海,居民离乱播迁,社会不断重构。即便到民国初期,獭窟也“由于走私地势得宜,利润倍蓰,獭人趋之若鹜,对子弟栽培,多所忽略,读书之风,因以大隳。自科举废,半个世纪,仅有曾谋钟、张瑞钦、曾达本、张含珠四人急起维新,就读于泉州府官立学堂。”在这样的地方氛围中,要培养和维系民众的正统意识显然不易,双忠信仰的社会基础也由此并不稳固和广泛。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逐利风气的弥漫,獭窟传统乡绅的身份和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和以往一样,通过正统儒学连接官方和乡野,文武尊王信仰中所蕴含的那些儒家正统道德观念也就失去了代言人。因此,没有了苦心经营和推崇的士绅,獭窟的双忠信仰失去了进一步地方化的机会;没有了不断创造出的灵应故事和占卜仪式来维系双忠信仰与渔民生活的联系,双忠这一本来就具有“外来”性质的信仰也难免与当地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至于在今天的当地村民看来,除了“堆沙”这一特殊习俗之外,井亭宫的文武尊王与獭窟其他的境主并无二致,甚至,村民们对屡次化身人形、托梦救助渔民的“船王公”反而印象更为深刻。因此,在曾经是“山高皇帝远”的獭窟,双忠这一不经意间又因“皇帝”的到来而播种的香火虽然延绵至今,但却一直止步于境主神的地位。
综上所述,宋元之交,当宋端宗及其小朝廷在獭窟“驻跸”,追随和效忠于宋室的洪氏先祖等人在原为僧道修炼之所的井亭宫供奉双忠香火之后,井亭宫便成为獭窟当地带有国家象征符号意义的、特定的政治和“正统”色彩的“忠臣之庙”。明清以来,虽然獭窟社会已经逐步转型,政府对双忠信仰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且带有官方正统色彩的双忠信仰在当地也得到了包括洪氏后人在内的士绅们的更多推崇,然而,随着獭窟地方社会的不断重构,大多数时候,双忠和岛上其他的神灵一样,身处于一场激烈的灵力竞争之中。而它们的灵验与否,又直接决定了信众的多寡和香火的存续。因此,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獭窟人基于不同的诉求,对井亭宫及其双忠信仰的历史记忆进行了有选择的加工和改写,双忠信仰的原初形态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蜕变。尤其是民国之后,伴随着社会变革和地方逐利风气的弥漫,双忠信仰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土崩瓦解,一般意义上的祈福禳灾便取而代之,“忠臣之庙”及其“正统神明”逐步走上了“地方化”的道路,成为了獭窟岛双忠信仰今日的面貌。
注释:
[1]《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忠义下·张巡传》。
[2][5]李玉昆:《泉州双忠庙》,《泉州晚报》,2004年6月22日。
[3]“宋太祖亲征太原,川水泛溢,上忧之。冰忽合,师遂济,空中见神来朝,加征应护圣使者。”卢镇《琴川志》卷十,《叙坛庙》,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4]乾隆《象山县志》卷七《坛庙》,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版。
[6][22][27][32](清)洪崑:《獭江新考》,1988年抄本。
[7]獭窟岛山名。
[8][16](清)曾枚:《獭江所知录》,1988年抄本。
[9][11](元)释大圭:《梦观集》之《筑城曲》:“吾闻金汤生◇枢,为国不在城有无。君不见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 ”
[10]泉州丰泽区法石街道云麓村《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碑。
[12][33]庄奕谋、庄世坚主编:《獭窟岛地志》,未刊本。
[13]“帝遂趋潮州,口占踏莎行(沙)一阕与居人别。”(清)曾枚:《獭江所知录》,1988年抄本。
[14]据报道人獭窟村民张炳南抄本。
[15](清)乾隆《泉州府志》,泉州: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3年。
[17](清)雍正《惠安县志》。
[18][19]叶恩典:《獭窟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0](明)雷礼:《皇明大政记》卷三《洪武正韵书》,续四库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1]《大清会典事例》卷433,《礼部》一四四,《中祀》历代帝王庙。
[23][25][26][31]参见陈春声《“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地域社会的建构——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4]《元草堂诗余》跋,转引自23。
[28]参见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9]《奇特双童神像引出一段历史传奇 南宋两幼帝曾与泉州结缘》,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9-04/13/content_3047302.htm来源:泉州网-泉州晚报。
[30]参见庄汉成:《青阳青龙宫的日月太保》,晋江市情信息网:http://www.jjsqxx.com/Item/Show.asp?m=1&d=99385 2011年9月22日。
〔责任编辑 钟建华〕
The Sym bol of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y of Shuangzhong Belief on Taku Island
Chen Zunci
Shuangzhong belief of Taku began at the turn of the Song to Yuan Dynasty.Then the ancestor of Hong, who follows the runaway Emperor Duanzhong of Song began to consecrate Shuangzhong,the godswho have beenmost celebrated for their loyalty,in Jing Ting palace,which became a temple of loyalism with political and orthodox significance.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ith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aku society,Shuangzhong turned to be amore respectable belief in the Taku elites,but the local individuals alsomade selective changes to it and Jing Ting palace— and the temple of loyalism and orthodox godsmake their way to localization.
Taku island,Shuangzhong belief,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y
陈尊慈(1991~),女,福建泉州鲤城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