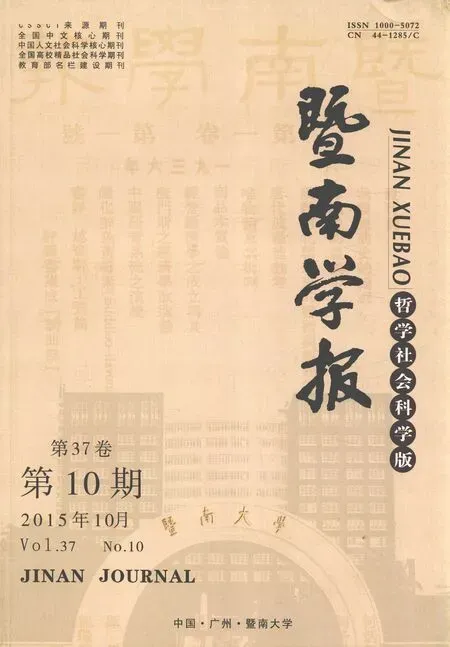复古与新趣——论南宋以降两百年左右文人书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015-11-14朱圭铭
朱圭铭
(暨南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一、引 言
审视中国书法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有几个重要转变阶段所发生的现象应特别值得重视。一为战国中期前后“隶变”现象的出现,致使汉字就此由古文字系统逐渐向今文字系统过渡,同时衍生出中国书法笔法系统中另一最为重要的、几可与中锋用笔并驾齐驱的笔法形式——侧锋用笔;另一个阶段即为汉魏时期,在这一阶段汉字字体本身的演变就此结束,随后历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文人化之风格史阶段,而该时期钟繇及“二王”等名家的书法遂亦成为后世书家规模取法的圭臬;再就是北宋初期,历五代之乱,文物摧落,艺事匡阙,缥缃散佚,加之晋唐书法发展过程中的“口传手授”式笔法传承谱系因此断裂,致使笔札无体,古法湮灭,因而刻帖之风应运而生,帖学大行,后世书法发展基本遵此道而为。至若清人标举“碑学”大旗,上溯秦汉甚而三代,尊碑抑帖,不过是趁帖学末流之弊,另辟蹊径,今日观之,似亦无可厚非。而南宋以降文人书法的发展,“帖学”风行之大背景下,体现在某些具体书家的身上,又呈现出一些不尽相同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二、“当则古”——从赵构到赵孟頫
北宋书法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至神宗、哲宗朝时,苏轼、黄庭坚、米芾诸人的相继出场,由唐溯晋,转得晋意,方将“尚意”这一新风演绎得有声有色,使得宋代书法的发展出现了几欲与唐人争一席之地的良好趋势。惜好景不长,随着金人铁蹄的南下,“靖康之变”后北宋政权即被覆灭。神州的板荡,使文明遭到了重创,皇室百余年的积聚尽数为金国掠夺。书法刚刚繁荣了不到五十年,至此则受到了比党祸远为酷烈的毁坏。南宋前期书法的代表人物,都是在南北交替之际活跃在书坛上的,他们饱经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南渡之后,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和收藏,而且失去了研习书法的条件和氛围,但是最可悲的莫过于书法进取精神的失落。关于此,南宋高宗赵构《翰墨志》中曾言:
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只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
诚然,若从政治角度而言,赵构内心深处以东晋政权自况,似亦能略得几分安慰,毕竟赵宋江山尚存半壁,祖宗基业并未全失,而其欲以晋室东渡后之王、谢风流来观照南宋初期书法发展之状况,实无法同日而语。整个南宋时期,其一百五十余年间再没有产生第一流的书法家,应该最能说明这一阶段书法发展总体上趋于式微的客观状况。
关于南宋书法发展总体特征,方爱龙曾在研究中指出,从传世的南宋书法史料,包括书家、书作、书论以及其他大量的材料出发,通过钩稽、排比和客观分析,可以发现南宋书法史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双线”发展形态。即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延续了北宋书法主流的“尚意”风潮,另一方面以赵构为代表形成了“以钟、王为法”的“复古”思潮。前者是表流,而后者是暗流,两者交汇— —这就是南宋书法的历史之河。
方爱农的概括堪谓体现了南宋书法发展之主要脉络。进而察之,即便宋高宗赵构本人,其学书之始亦初从黄庭坚,再学米芾。楼鑰在《恭题高宗赐胡直孺御札》中云: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刘)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
岳珂亦云:
中兴初,思陵(高宗陵寝)以万几之暇垂意笔法,始好黄庭坚书,……后复好公(米芾)书,以其子敷文阁直学士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遂大变,追晋躏唐,前无合作。
大抵赵构在学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须追本源的重要性,遂从智永上追钟王,其越到晚年越沉迷于魏晋法度当中,从而走上一条复古之路。赵构后来总结自己的学书经历时说: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
赵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对时人及后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惜他的这种书学理念因时代发展的多种原因所囿,未能再进一步拓展。赵构自己的书法,亦由于自身天份稍弱,在精神气度上与北宋苏、黄、米及其父徽宗赵佶皆相去较远,其“详观点画,以至成诵”的学书观点,不免给人一种过于强调功力的感觉。
北宋苏、黄、米所开“尚意”之风,以意运法,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在南宋书家群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其在南宋却又走向了另一种不合理的方向,即单纯模拟苏、黄、米的因袭之风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而并非是他们在书学“尚意”精神上的传承。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藉宋人文献记述:
南渡而后,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此见于玉海及诚斋诗话。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兼为书坛“中兴四家”之一陆游亦曾云:
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
其实,苏、黄、米书法在南宋的风行,无论是由于上行下效的惯例所致,还是诸多文人书家在骨子里面对他们书法的真正认可,有一潜在的原因当不可无视,即古代的书法遗产经过北宋末年的动荡,再一次蒙受了浩劫。本已稀有之物,又被皇家巧取豪夺。到了南宋,不用说魏晋,即使是唐代的名帖,在民间业已难再保存。周密后来所称高宗在位时“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仿佛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真实的历史情形恐并非如此。若曾敏行《独醒杂志》中有记:
番阳董氏藏怀素《千文》一卷,盖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1129),董公逌从驾在维扬,适敌人至,逌尽弃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极珍藏。一日朱丞相(胜非)奏事毕,上顾谓曰:“闻怀素《千文》真迹在董弅处,卿可令进来!”丞相谕旨,弅遂以进。
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和现状,南宋一般操觚之士于书法一途的追求,完全丧失了赖以沿波讨源的借鉴依托,他们只能因地制宜,随着时风的好恶改变其价值取向。南宋书家中之一二杰者,若赵令畤、孙覿等人之于东坡,米友仁、王升、吴琚等人之于米芾,虽承衣钵,然多有规模形貌之嫌,神理情趣实远不可逮。吴说、陆游、张孝祥等人稍度新声,下笔追古人笔意,意欲高远,可却总给人一种器局略小的感觉,此恐与山河破碎、外侮欺凌、民族危亡对文人内心深处的折磨和压抑不无关系,而这种文化心理,体现在绘画层面之马远的“马一角”、夏圭的“夏半边”无疑最能与之呼应。
南宋末年至元代初期,以杭州文化圈中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人的相继出现为标志,书法的发展似乎随着政权的更迭也出现了另一个转向,一百多年前赵构的书学“复古”思想,竟然在他们的身上爆发,衍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赵孟頫作为赵宋宗室后裔,其书学思想受赵构的影响颇深,并将赵构的“复古”思想进一步拓展发挥,托古改制,将这种思想应用到诗文、书、画、印等多个文艺领域。
站在崇古的立场上,赵氏于书法明确提出:“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赵氏的书法实践以晋人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古籀文,习古之广,实为有宋三百年间所无,而他的成就对时人及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若吾衍、吴叡、周伯琦等许多书家以篆隶名世;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至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终元之世,许多书家或曾得其亲授,或为其再传弟子,为其余绪,鲜有不受其沾溉者,形成风格鲜明的赵派书家群。受他影响的书家不仅有同代友人鲜于枢、邓文原等,还有学生辈的书家如虞集、郭畀、柳贯、钱良佑、朱德润、柯九思、揭傒斯、康里巎巎、张雨、俞和等,而且其亲属一脉也都以赵氏书法为宗,如其胞弟赵子俊,其妻管道昇,其子赵雍、赵奕等在元代均有书名。
由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赵孟頫的书法及书学观念甚至一直影响到明代,明代中叶吴门书家若祝允明、文徵明等人对其皆比较推重,特别是文徵明,其一生于书画之诸多方面皆以赵孟頫为师事对象,诚如其子文嘉在《先君行略》中称:“公平生雅慕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论者以公之博学,诗、词、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一直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赵书之风靡方有所减弱,但他的书法仍然受到许多士人的喜爱。
三、清遒古媚 自有一种风气——从张雨到宋克
晚明董其昌有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法乎?宋人自以其意为书,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为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董氏在此一方面总结了晋、唐、宋、元几个时代书风的总体特征,一方面又点出了宋人取意及赵氏复古所存在的不足,旨在强调要想追求晋人的“韵味”,则必须做到“意”“法”统一方可。赵孟頫所倡导的复古书风,本为矫南宋末流之弊,其诸体兼为的书学实践客观上亦有旨在恢复古法的历史贡献。然究其个人的艺术风格而言,赵氏主要取法二王平正一路书风,魏晋书风以二王为代表的那种情驰神畅、风情万种、不拘一格之艺术特点,在他笔下并未也不可能得到充分演绎,故董其昌批评其“虽己意亦不用”。赵氏入元后官位显赫,加之其本为宋皇室后裔,所以其书法又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一种贵族色调,而其许多追随者更是将这一路书风演化为平正圆熟、含蓄婉丽的习气。因此,如欲突破赵氏藩篱,似又应另寻他径。元代中后期,在赵氏的传人以及江南隐逸书家群中,一批有识之士在尊崇“复古”理念的大旗之下,书学魏晋,兼及唐宋,纷纷对古风重新加以演绎,尚意率情,自我意识强烈,走出一条别开生面之路,同时也对吴中地区的书法发展带来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张雨、杨维桢、倪瓒、吴镇、宋克等书家即为这群人中的代表。
张雨(1283—1350)于书学初从赵孟頫,得其指授,转而习李邕《云麾将军碑》、张从申《茅山碑》等,并又从欧阳询之书中汲取养分,草书则取法怀素大草豪迈一路,此外,其还得到陶隐居墓及遗文,六朝梁陈清逸之风的沾溉。此正如元明诸家所论,元末高启云:
贞居(张雨别号)早学书于赵文敏公,后得《茅山碑》,其体遂变,故字画清遒,有唐人风格。
文徵明曰:
贞居书法先学松雪,后入陶隐居,稍加峻厉,便自名家。
明李日华言:
伯雨书性极高,人言其请益赵魏公,公授以云麾碑,书顿进,日益雄迈。魏公平日学泰和,得其舒放雍容,而伯雨得其神骏,所以不同。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亦云:
贞居师李北海,间学素师,虽非正脉,自有一种风气。
根据诸家所论可以看出,张雨虽然于早年曾师事赵孟頫,并在赵氏指导建议下研习唐人李邕《云麾将军碑》等名刻,但在风格表现上能不被前贤所囿,化古为己有。张雨曾入茅山学道,思想上又受到同时期杨维桢、倪瓒等人的影响,其书中自然溢出隐逸文人孤傲不群的气息,故《书史会要》又称其“字画清逸”,倪瓒更评其“诗文书画,皆本朝道品第一。”从张雨传世的代表作品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题画二诗卷》来看,其作品中去掉了赵孟頫的雍容、平和,增之以神骏、清遒的艺术特征,结构也没那么圆熟,饶有趣味。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张雨书法的取径对象似乎已非仅仅局限于晋唐诸名家,而是有重新向宋人米芾等学习的迹象。“北郭十友”之一的张羽在论及张雨书风时曾言:“贞居真人生平慕米南宫之为人,故其议论襟度往往类之。其诗句字画清新流丽,有晋唐人风流,不蹈南宫狂怪怒张之习。”虽然张雨“不蹈南宫狂怪怒张之习”,然因其爱慕米芾之为人,故其书法在潜意识中多少会受到米芾的一些影响,亦应是情理中的事情。从张雨的另外一件经典作品《登南峰绝顶诗轴》来看,用笔率真自然,静动起伏,若不经意而又变化自如,激越跳荡处即颇有米字遗韵。张雨在杭州作为艺坛盟主时,交游甚广,与之交谊颇深的吴中地区的书家亦甚多,影响且深,故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元明之际吴中书法的奠基者。
倪瓒(1306—1374)是元末江南隐逸文人的代表人物,其与张雨、黄公望、王蒙、杨维桢等皆多有交往。倪瓒书法瘦劲超逸,意境高古,可以看出其主观上对元代赵孟頫典雅平正一路书风的刻意回避,故后人曾赞许其“无一点俗尘”。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倪瓒书作均为楷书,关于其书学取法,顾复《平生壮观》中称其:
早岁学欧,《水竹居》《惠山图题》《题过秦论》是也;中岁大变,如有一注冰雪之韵,沁人心肺间。
明徐渭评倪瓒书云:
瓒书从隶入,辄在《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疏。
清笪重光则云:
云林书法得笔于分隶,而所书《内景黄庭经》宛然杨、许遗意,可想见六朝风度,非宋元诸公所能仿佛。
无论是赵构还是赵孟頫,他们虽然倡言“复古”,但他们个人取法的主要对象实以二王为主,保留至今的赵孟頫论书文字,也以论二王为最多,《兰亭十三跋》堪谓代表。黄惇先生亦曾指出,影响赵孟頫最深的,当首推二王、智永、李北海、宋高宗诸家。向比二王更早一点的钟繇学习,不仅是笔法层面,在审美上亦以其更加古质拙朴的气息特征为旨归,应是元代中后期崇尚“复古”大背景下的一种风尚,倪瓒的小楷书法堪谓重要代表。至于笪重光所谓杨、许即指东晋时期的杨羲、许迈,可知倪瓒虽然师法晋人,却并非赵孟頫提倡的二王,反而与张雨吸收陶隐居的情况比较相似,属于偏师独出,从而摆脱赵的影响。又,晚明董其昌还曾评倪瓒书法云:“人谓倪书有《黄庭》遗意,此论未公,倪自作一种调度,如啖橄榄,时有清津绕颊耳。”董氏强调了倪瓒书法创造性,而倪氏书中的“自作一种调度”,其实又与何良俊评张雨的“自有一种风气”大体相同,皆为个体情性的抒发与表现。
元末时期杨维桢(1296—1370)的书法亦以其放逸奇古的风格特征引人注目。杨维桢比张雨小十三岁,比倪瓒大十岁,与他们亦皆交往密切。在元末江南文化中心由杭州向苏松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杨维桢其实为继赵孟頫、张雨之后江南文化圈的又一代领袖人物,此正如明王世贞所说:“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姿,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
杨维桢的传世书迹主要为行草与楷书。其行草多掺入章草笔法和结体,应曾受到其前辈书家康里巎巎的影响,同时又能远师汉晋张芝、索靖,所书《张氏通波阡表》(日本东京私人收藏)为这类书作的代表。与赵孟頫学习章草的书法作品相比,其去秀润、婉约而增拙拗、冷峭,在书风上显露出特有的狷直个性。杨维桢的楷书如其五十八岁所作《周上卿墓志铭》,书风有刻意效仿唐代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的痕迹,刚峭之态,一反元代所崇尚的魏晋风韵,走险绝之路,同样反映了他在书法上的革新与创造精神。杨维桢的书法虽没有成为元末文人普遍模仿学习的对象,然而其意义在于突破了赵孟頫的书学藩篱,其充满个性、尚意抒怀的风格特征,扩阔了书法艺术美感的表现。同时,杨维桢作为元末吴中文艺坛的主盟人物,其观念必然会对身边的人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上也是必须要肯定的。百年以后,同样强调个性、提倡尚意抒情的明中叶吴门书家恐与其思想上仍有共鸣,故对其书法的评价甚高,若徐有贞尝言:“铁崖(杨维桢别号)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吴宽则云:“大将班师,破斧缺斨,倒载而归,廉夫(杨维桢字)书或似之。”
宋克(1327—1387)是元末明初吴中书坛承前启后式的重要人物,在明初诸书家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最高。关于宋克之书学师承,解缙《春雨杂述》中述其受业于饶介,而饶介则又得于赵孟頫之弟子康里巎巎,为赵之再传弟子。宋克最为擅长的书体为小楷、章草及狂草与章草相结合的糅合体草书。宋克的小楷作品如《七姬权厝志》,结体微扁,用笔瘦劲,遒丽疏朗而又显醇朴古质,从风貌上看当源自魏晋钟王,其中更多当得益于钟繇。吴宽《跋宋仲温(仲温为其字)墨迹》称其:
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墨精妙,而风度翩翩可爱。
都穆《寓意编》云:
乡先生宋仲温氏书法师钟元常,后竟以是妙绝天下。其书今人间往往有之,余所阅殆不止此,独元常书世远罕传,并刻石者亦不多见,曩成化间尝观元常荐季直表真迹,始知仲温之诚有得于元常,而今岂易得哉?
又,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七十六云:
《七姬志铭》,为浔阳张羽撰,东吴宋克书。文既近古,而书复典雅,有元常遗意,足称二绝,第其书大奇而不情。
可见明人评价宋克小楷书风的来源多为钟繇,并指出其不仅能得钟之古朴典雅,且能于书中蕴之以“奇”,因此他的小楷已经较远地离开了赵氏一路的风格。宋克的小楷书风影响了吴中地区很多同时期及后世书家,后世对其评价亦极高。诚如王世贞所云:“吾吴诗盛于昌谷(徐祯卿)、而启之则季迪(高启)。书盛于希哲(祝允明)、徵仲(文徵明),而启之则仲温(宋克)。”清翁方纲甚至推许“有明一代小楷宋仲温第一,”并有诗赞曰:“东吴生楷有明冠,儿视枝山孙孟津。”从祝允明的一些小楷作品来看,确实受宋克影响颇深。如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小楷前后出师表》,与宋克的《七姬权厝志》相类,点画清刚丰腴,体势宽绰。翁方纲曾跋此卷云:“祝京兆书以小楷为上乘,有明一代,小楷书能具晋法者,自南宫生(宋克)开其先,惟枝生得其正脉也。”
宋克擅长的章草及糅合体草书,在明初亦影响甚大。其章草名特重,时人李翊云:“近世学书者,知有宋克体,不知有章草,然非重头曲脚之法也,善隶者知之。”由此可见其时宋克章草之盛名;而他的糅合体草书特色尤显,他将章草、今草及旭素狂草的用笔、结体糅合得浑融无迹,在赵孟頫、康里子山等人探索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宋克的章草作品以临写《急就章》为主,今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均有庋藏;糅合体草书如《唐宋诗卷》(上海博物馆藏)及《杜甫壮游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从其作品所呈现的整体风格特征来看,笔力劲健,笔势流畅圆浑,点画精到而气势磅礴,既有使转之迅疾,又见波磔之高古。
宋克的草书尤其是糅合体草书,客观分析乃是其学章草、二王草书、旭素草书及受到康里巎巎一脉草书书风的影响之后,于深层体悟笔法所得的结果。解缙评其草书曰:“鹏抟九万,须杖扶摇。”点出了宋克草书的劲健之姿,磅礴之气。祝允明评价宋克书则“如初筵见三代卣彝,盖有天授,非人工也”,盖指宋克书中蕴藏着一种为人难及的高古之意。当然,后世有些评论家站在保守的立场,对宋克亦颇有微词,如王世贞在肯定其成绩时,也批评他“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詹景凤更讥为“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公允论之,如以宋克的草书与明代中后期祝允明、徐渭等人的作品相比较,其草书中更多地强调法度,表现出“理性”的色彩,使转丰富而多变,在字势上呈纵势,并以字末收笔之波磔表现苍古之意。而祝、徐草书中之个人“情性”的表现似乎更加强烈,更加豪纵不羁、风骨烂漫、天真纵逸。但是,相较于同时代的许多书家而言,宋克创造尽管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与赵氏书风笼罩下的东施效颦者当有天壤之别。一般认为元末明初杨维桢与宋克的书法都能远离赵氏,故而也是最具个性和胆识的两位书家,以至于有人将宋克书风视为元末隐逸书风向明代浪漫书风过渡的典型。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从南宋政权的建立到宋克的出生恰巧为两百年时间,而在这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书法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对北宋之苏、黄、米三家书风的因袭效仿与赵构的“复古思想”相并行,到赵孟頫承继赵构思想,高举“复古”大旗,回归晋人,并在元代蔚然成风,形成庞大的赵派书家群,影响深远,再到元代中叶以来张雨、倪瓒、杨维桢、宋克等许多江南地区的书家在书学复古之大背景下,又能突破赵氏的书学藩篱,尚意率情,重新诠释传统而彰显自我个性的阶段性特征。就具体的书法取法和创作观念而言,从张雨到宋克等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书家,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几点现象也应特别值得关注:
(1)对钟繇的取法学习,钟繇在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历代书家书家对其皆极为推崇,然而实际情况是自唐宋以来,钟繇书风蕴涵的“古质”特点似并未得到深入挖掘,众多书家所着力学习的对象应是以二王为主。就本文提及的赵构或者赵孟頫而言,他们学习晋人及王羲之,其取法和表现的也主要是王羲之不激不厉之平正、典雅、秀逸一路书风,这一点亦正如前述,从他们对《兰亭序》的推崇即可管窥。而倪瓒、宋克等人小楷作品,无论是笔法、结体还是气息特征,都更加接近钟书古质雅逸。同时,学习钟书在元代中后期已然成为一种风尚,而明代中叶吴门地区祝允明、王宠等人在小楷上师法钟繇可视为这种风气再度延续和承传。
(2)即对初唐大小欧阳的取法,欧阳询作为初唐楷书大家,其书风本身体现了南北交融的风格特点,结体峭拔,笔势方折居多,尤其是其子小欧阳之书,似较其父更加凌厉险绝,而若杨维桢竟然向其取法学习,与赵孟頫笔下之晋韵明显不合,反映了其不随时俗的个性以及在书法上的革新与创造精神。
(3)出现重新向北宋苏、米等人学习的迹象,赵氏之复古本为矫宋人末流之弊,回归晋人,兼及唐法,但是到了元代中后期以后,张雨、杨维桢等人却表现出对苏、米为人之个性及书风的再度膜拜,其笔端的激荡跳跃似亦颇有宋人意趣,并对身边诸多友人产生影响。
(4)当为众多书家学习唐代旭素大草书风,追求一种气势奔放、酣畅淋漓而更加抒情率意的书风表现,宋克无疑应为其中成就颇高的代表人物,江南苏松地区受其影响者亦甚重。而这种学习旭素连绵大草的风气,可视为开明代中后期祝允明、徐渭等更加纵逸烂漫大草书风之先河。
元末明初,随着江南的文化中心由杭州向苏松地区的转移,该地域的许多书家虽然在思想上都尊崇赵孟頫,亦重视师古,甚至很多人在师承关系上与赵氏还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然而落实到各自个性化的创作,却表现出与赵氏并不完全合辙的特点,加之这些文人在思想和生活方式存在不同程度的隐逸色彩,故而“古法”在他们的笔下又得到重新演绎,赋以新趣,与赵氏的典雅平和书风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对后世有启迪意义,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奏响了颇具特色的一个篇章。但是,随着明代前期政治环境的改变,江南吴中地区许多文人的命运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文艺上的创作个性亦因此受到了极大钳制。书法方面的发展,与台阁诗文、院体绘画一样,于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了朝野盛行的台阁体,雍容典雅、婉丽遒美的书风成为时代的主流,造成了文人书法注重情趣表现的个性特质急剧衰弱,而这样一种文化景观,则要等到明代中叶吴中地区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出现方得以再度改变。同时,在祝、文等人的书学观念和艺术创作中,也有很多方面充分体现了元代以来该地域既有的书学传统与文人精神的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