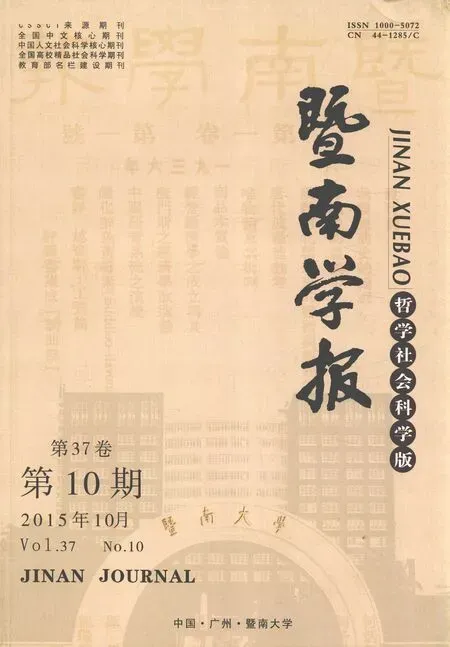晚清公羊学与变法维新
2015-11-14陈煜
陈 煜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清代公羊学作为清学的后起之秀,一度可以与作为清学代表的朴学(汉学)相抗颉,且因康有为借公羊之学行变法之志故而风靡一时。尤其是康有为为了给其变法主张寻求理论基础而著的公羊学作品,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更是引发了当时政治界和学术思想界极大的震动。于是后来研究晚清变法改制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联系到公羊学。但是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端:一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专门探讨公羊学在清代的发展,间或提及其与晚清变法之关系;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晚清法制思想的几次变革,而将公羊学作为舞台的一幕布景。至于清代公羊学究竟为晚清变法提供了何种资源,其内在的线索是怎样的,虽然也有学者做出过卓越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将围绕着清代公羊学在各个时期与变法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明学术是如何受到时势的影响又是如何对时势做出回应,并继而对变法发生重大的影响的,当然本文所说的“变法维新”,不限于康梁维新变法,而是包括改革在内的一切求变思潮。
一、公羊学的要义及其在清代的复兴
“公羊学”源自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一度也是聚讼纷纭,但通常认为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相传公羊高为孔子高徒子夏的弟子,为了解释孔子所著的《春秋》,并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图,从而作《公羊》,《公羊》起初只是口耳相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与胡毋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武帝之后,《公羊传》作为传《春秋》经典之作而得列入官学,并成为今文经学最重要的经典。本文所谈公羊学,实际上相当于在谈今文经学。
西汉尊今文经学,《公羊传》因此也成为解释《春秋》之义的不二权威。加上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推衍发挥,着力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于是围绕着《春秋公羊传》,逐渐形成一门学问。东汉虽尊古文,但围绕着公羊传依旧传下了有力学说,最为著名者为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此书除了回应公羊子之“辞”之“义”,更是归纳了孔子作春秋时确立的若干“例”。这个“例”可看作是孔子在写作《春秋》过程中,通过所选择的用词和写作的语气所透露出来的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准则。清代公羊学家如孔广森、刘逢禄辈高度评价何休的设例之说,当然在此基础上又有新解。总之,到了何休那里,公羊学才真正成为一种有条理有系统的经学学说。但在当时的两汉今古文之争中,何休发展出的公羊学实不占优势。
而随着东汉的覆灭,原先的今古文之争也告一段落。诚如梁启超所云:“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后来的正统经学回避这一问题,而是由政府统一确定各门经典,到唐时《五经正义》出,杂糅今古文说,而宋更是废汉唐故训,这种情况延续至清初。公羊学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式微的境地,中间虽有宋代的孙复、胡安国,明代赵汸、郝敬攻击古文经学,试图振衰起弊,重塑公羊学的地位,但因为种种原因,终未有成。但是不管公羊学在这么多年中的遭际如何,学者间评判公羊传中所谈《春秋》之“旨”和“例”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亦可见清代公羊学之所以中兴,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已经有相当积淀的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当然,公羊学本身的开放性以及丰富的内涵,也保证了这门学问可以常研常新。
公羊学内涵丰富,各家均有独到见解,但治公羊者基本上都是在同意这些观念的前提下而各成其说的。
第一,孔子为受天命之素王,代行天子之事,作《春秋》为后世立法。
第二,六经为孔子手定,用以推行其政教,而其中最为关键者,在于《春秋》一书。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第三,《春秋》本质上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改制之作,孔子通过贯彻于书中的“微言大义”(“旨”)以及写作的“笔削褒贬”(“例”),来表达其对社会的看法、对人事的评价和对理想制度的追求。
后来各公羊家的差异,集中在对“旨”和“例”的探究上。《公羊传》本身已经揭示出了《春秋》的某些要旨,诸如“大一统”、“别夷狄”、“异内外”、“讥世卿”、“三世异辞”、“九世复仇”、“拨乱反正”等等,后来董仲舒又加以发挥,形成“张三世”,“通三统”,“新周、故宋、王鲁”等命题。至何休,则更为系统,形成所谓的“公羊家法”,即“春秋大一统”之义和“三科九旨”之说。后来的公羊家都是对此大一统之义和三科九旨之说“接着说”(冯友兰语)。
至于清代中后期公羊学为何会复兴,成为一融合政治与学术于一体的大流派,乃至在清末大放异彩之故,历来研究者往往会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矛盾、中外关系等角度进行诠释,陆宝千先生在《清代思想史》中的一段话,堪为其典型:
其有不愿返诸宋学者,复由东汉而上溯西汉,遂及公羊之学,是学也,亦为汉学,而无训诂之琐碎,亦言义理,而无理学之空疏。适中清儒厌钻故纸而不忍遽弃故纸,菲薄宋儒而又思求义理之心情。偶有一二嗜奇者嗜之,公羊之学遂茁春萌。芽蘖既透,清运亦衰,匪乱夷患,纷至沓来。由是而平章朝政,由是而试议改革,皆据圣经贤传以立论,而又莫便于公羊。于是公羊之学披靡一时也。
清代中后期公羊学的复兴,首先是学术本身的发展使然。乾嘉之时,正是“汉学”如日中天之际。“汉学”本是为纠正宋明理学之弊端发展而来,汉学家认为,汉代去六经纂成不远,汉诸经师所作传注较之于后来宋明诸子所作章句,当更能得圣人本意,所以希望通过辑佚汉人传注,并加以文字音义训诂,先“识字”后“通经”,最终真正理解经典。于是吴、皖两派相继兴起,诸子对于经典的整理和考异,成果斐然。但物极必反,吴派最后陷入“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泥古一途,而皖派陷入“凡经必考,凡古必疑”的琐碎境地,而皖派的影响尤为深刻。既然东汉诸训诂都不能定黑白是非于一尊,那么再往上追溯到西汉,就是非常自然的学术逻辑了。而西汉最为强劲的学术思潮中,公羊学赫然在列。于是公羊学的新起,乃是汉学发展的必然。因此,汉学(皖派)强调识字为通经,通经在致用,表面上是考证,而里子则隐含了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实际拉开了类似“重估一切价值”思潮的序幕,而公羊学正好可资重估价值之用。
学术契机固然重要,但公羊学的真正兴盛,还在于其对国家形势和社会生活的回应,所以虽然乾隆中后期庄存与已经开始公羊学的研究,但是真正形成气候,还要等到四十多年之后,其外孙辈的刘逢禄那里。如同上引陆宝千先生所述那样,乾隆中后期,因天下承平日久,百弊渐生。文法益密,治法益疏。贿赂公行,歌舞升平。在表面的繁荣背后,已经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乾隆时期,虽然尚在“盛世”,但是已经出现了某种由盛转衰的迹象,其后至嘉庆、道光年间,则国势衰颓,政治上出现巨大的危机。所谓“匪乱夷患,纷至沓来”。在这种情形下,有识之士更难以稳坐书斋,而思以所学“经世”。“经世致用”的命题再次在时代危机中被重新揭橥,此时西学思潮尚未汹涌东来,故思想家治国之道只能从原来的知识结构中去寻找。《春秋》本衰世求太平之理想之书,又是孔门不刊之经典,而《公羊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本身即具有传《春秋》的正统性,又蕴涵改革求治之道,最关键者,《春秋》公羊本身具有“无达诂”的理论开放性,便利于解释者假托经典发挥己义,于是公羊学在这种境遇之下就开始了复兴之路。事实上,我们回头再看,晚清公羊学,正是沿着“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轨迹一步步发展过来。
二、公羊经世:温和的变革观
晚清的公羊学,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经学而被探讨,但后来因“经世”之需逐渐衍化为一种政治思潮,遂与传统经学渐行渐远。这个情形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下文仅以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公羊学说为线索,来讨论公羊学与晚清变法的关系,当然我们所述的这段时期的公羊学说,相对来说是较为温和的。
(一)庄存与的开创性贡献
一般的学术论著,往往将晚清的今文经学(公羊学)的源头追溯到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最早可以追溯到龚自珍的说法:“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此后,清代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或者和他有师承关系,或者受到他的影响,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庄乃常州学派的开创者,此后自第二代庄述祖、庄有可,到第三代刘逢禄、宋翔凤,再到第四代龚自珍、魏源,其间的师承关系至为明显。至于其影响所及,如此后湖南的今文经学家王闿运、皮锡瑞,四川的廖平,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可以说是受益于庄的开创性著述。
庄存与,常州武进人,曾在上书房行走多年,为乾隆皇帝的近臣,并教授诸皇子经书,一生著述颇丰,其公羊学代表作品为《春秋正辞》。庄存与本人并无意识去复兴公羊学乃至开创常州学派。但是由于其置身于其时如日中天的“汉学”氛围之中,不可能不受到汉学的影响。作为一名帝国官僚和学术精英,庄必须要为现存意识形态维护。但是汉学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理学正统地位,自皖派出,疑古之风盛行,其以训诂的力量,甚至断定某些帝国长期奉行的教条为前人之伪,继而以此为突破口,怀疑既存的一切,汉学因之越来越激进。于是庄在教授和著述中,有意无意地要维护圣人之道,公羊学春秋大一统之道,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反击武器,诚如学者所言:“庄存与的学术主张旨在抵消他所认为的汉学的激进政治影响,这种影响似乎从18世纪40年代即威胁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巩固。”
庄本意如此,但是一旦他走向公羊学研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他借《公羊传》这样一部非正统经典发挥己意时,就不仅有异于汉学,甚至走到理学的对立面。‘真汉学’切断了与汉宋两家的联系。重建今文经学的理想鼓舞着庄存与的弟子们向汉以降的一切基于古文经学的政治话语宣战。”
庄存与揭示的公羊要旨很丰富,我们仅举与晚清变法有密切关系者来叙述。首先,庄存与重新强调了世人尊崇春秋,并非因为春秋是一部记“事”之书,而是一部记“道”之书,记“事”之“辞”,只不过是“宏道”的手段,正所谓“寄言出意”。比如对《春秋》“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这一段辞,庄解释道:“此灭虞也,曷为书执而已?忌也。虞,畿内之国,灭而不忌,是无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晋国人,晋侯也。目人以执王官,罪既盈于诛矣。举可诛而人杀之,以不失罪;不书灭以隐之,而不伤义,而不伤义。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所以,读《春秋》,明事更要明道。
那么《春秋》所揭示最大的道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孔子作《春秋》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庄存与认为:“所谓《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也。”这就表明,《春秋》之目的乃是“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对《春秋》人事的评价,来为后世立法。
那《春秋》为什么在遣词造句上如此谨慎而简练,有时整个句子仅仅只记某时、日、月呢?庄氏认为,“君子作《春秋》,起教于微渺”。《春秋》本意在记治乱,治乱中渗透着变革之道,庄含蓄地表达了孔子改制的用意。所以庄总结“《春秋》约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为繁省,识天下之故而已矣”。
当然,庄氏如此解读《春秋》,除了学术立场外,也有政治上的忧患缘故。乾隆后期,和珅势力崛起,并围绕着他的周边,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贪腐集团,而皇帝对此不以为意,信任有加,这种情形又加速了乾隆后期政治的腐败。作为和珅对立面的庄存与对此既痛心又无奈,于是将一腔愁思化作文字,寄于公羊学中。
但是,“庄存与没有预见到,他的大胆开端将会导致一种对经典政治学说激进式的重新发挥,同时还将影响他曾维护过的儒教国家的合法性”。
(二)刘逢禄集清代公羊学学术之大成
刘逢禄出身簪缨之家,其祖父刘纶、外祖父庄存与皆做过乾隆时代的大学士,刘逢禄早年从其外祖父庄存与、其舅庄述祖学习今文经学,可谓家学渊源,深厚毕至。正是在他手里,原本作为常州家学的今文经学传至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学问。也正是在他手里,所谓“公羊家法”得以重建,公羊学作为一门学问正式确立。刘长于用《公羊传》解释经典,其著作体例精严,思想深邃。梁启超为此盛誉:“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为最有价值之著作。”而且,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其外祖父庄存与的公羊思想,才真正得以传播。
刘逢禄对清代公羊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将董仲舒、何休的观点进一步发挥,并总结出了春秋的三十个“例”,每一例均有充分的证据,且不拘泥于《春秋》一书,还和《论语》相互发明,迭出新意。诚如论者所示,刘对清代学术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响亮地提出只有公羊学说才得孔子真传,并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派系统,堂堂正正地拿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强调这是被埋没的儒家正统,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
刘本人虽然无意也无力作改革家,但是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却因为《公羊传》本身内蕴的变革思想以及作者对公羊精义深刻的发掘,从而深深地启发了后来的思想者。刘在这个角度上,既可谓清代公羊学集大成者,又可谓改革思潮的引路之人。
首先就《春秋》一书的性质,刘站在传统公羊学的基础上,认定是圣人欲有所作为之书,既可用于学术研究,亦可用于持身治世:“《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天道浃,人事备,以之贯群经,无往不得其原;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则先王之道可复也。”所以要体察圣人之道,必须首先要读通《春秋》一书,正所谓“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
然后,就《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的顺序、详略,以及孔子为何如此安排,刘解释说:“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内诸夏、不言鄙疆是也。”这是对“公羊三世说”的进一步发挥,鲁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正是在这种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更要用《春秋》来施行王化,这就是公羊学“王鲁”一义的延伸。《春秋》当新王,在于构建一个理想的秩序。在鲁国的衰败中,孔子想到的是保存祖先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文质彬彬的礼乐文明,所以与其说王鲁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阐发。故而“《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极太平”一说后来被康有为演化为“大同”世界,康并且用很大篇幅的《大同书》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
刘同时就“春秋大一统”也发挥新义,认为:“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大一统’也。”认为王者一统并非纯用武力可致,更在于“德化”,“德博”才能“王化”,“君道”成,“大一统”方可致。我们要体察刘的用心,他并没有谈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更注重“一统”的道德正当性。作为一个公羊学家,他自然深通“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的道理,所以不可能有类似“暴君放伐”的激烈言论,他所说的一切,都还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字里行间,却隐含着变法的主张。比如他在论述《春秋》的变革之义时,提到“《春秋》通三代之典礼,而示人以权”。这里面的是“示人以权”,就是要求人们因时损益,通权达变,而不是拘泥于周代制度,应该在通三代的基础上,发掘最好的治理之道。
最终,在借助于对春秋之“例”的阐发上,刘构建了一套阐发变革进化的历史哲学,为后来改革者“穷通变久”的改革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学术支持。《春秋》在这些改革者看来,实在是一部“为万世开太平”的指导之作,刘氏一语实可谓代表:“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
(三)龚自珍、魏源的“公羊经世”的改革主张
龚、魏两人同时受业于刘逢禄,年龄相仿(龚出生于1792年,魏出生于1794年)且为密友,两人思想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以可以同论。龚自珍并没有专门的公羊学著作问世,只有一些单篇的论文,贯彻着公羊之义。魏源著有《诗古微》、《书古微》两部公羊学专著,但是这两部专著,并没有将公羊学理更进一步深化,只是将公羊之义套在《诗经》和《尚书》这两部经典当中。作者试图证明的是,《诗》和《书》同样贯彻着大一统、通三统等公羊义理,并且试图总结《诗》、《书》中的公羊之“例”,作为《诗》、《书》本身的研究,的确富有新意,但是对于公羊学而言,并没有知识上的“增量”。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认定龚魏的公羊学研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志向就不在纯学术上。对他们而言“通经”只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致用”。其学术说到底是为他们的改革设想服务的,很多时候甚至不惜曲解经典。所以表其作品表面上是考证发微之作,而骨子里则是为改革制造依据。
龚自珍认为要振衰起弊,必得破除人们的保守习气和陈旧观念。而此习气和观念乃人们长期迷信经典所致。因此,龚首先从为“经”“正名”开始,龚认为“经”的定名,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如“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这些观点在习惯了传统经传的人看来,无疑是很大胆的,而龚的意思就是要人们破除盲从盲信,不要拘泥于经典。
然后,他又强调,圣人制作六经,目的是为了应用,龚自珍用《春秋》之例,来证明此点:“谨求之《春秋》,必称元年。年者,禾也。无禾则不年,一年之事视乎禾。”而“禾”恰恰是百姓日用所必需,所以,“经”,是切合人伦日用的。正所谓:“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民事终,天事始,鬼神假,福祉应,圣迹备。”而不是简单地应人们“进德修业”之需。
那么圣人制作经典,如何能够满足人伦日用之需呢?最终的结果只有一条,就是“应时制宜”。龚自珍同样用春秋公羊学,来解释礼的制定也是时代的要求,就祭礼而言,“夫《礼》据乱而作,故有据乱之祭,有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不同的时世,用不同的祭法。而刑罚同样如此,在一篇文章中,龚同样用春秋三世说来解释“刑罚世轻世重的”的内在原理:
愿闻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轻典,据乱故,春秋于所见世,法为太平矣。世子有进药于君,君死者,书曰:弑其君。盖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责忠孝也密。假如在所传闻世,人伦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闻世,人伦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由此可见,公羊学给龚自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龚自珍用他来表达对世道的关切以及提出改革的主张,这既源自对社会危机的直感式的忧虑,更有积淀于学术之基上的理论推衍。两者的结合,使得龚自珍后来的思想超越了早期的感慨式议论,而更加系统深刻。
针对当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万马齐喑的状态,龚敏锐地预感到“衰世”的来临: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临,未即于床。”这个时代,“士气不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甚至连才盗,才偷都不可得。更可悲的是,在此日之将夕之际,更多的人还沐浴在“盛世”的余晖中,龚应用“春秋三世”,直陈现在的世道是“衰世”,而衰世开始的表现还类似于“治世”,但是如果履霜,还没有做好防备“坚冰至”的话,那么“乱亡”的命运也就不远了。他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履霜之嶠,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痺劳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这是在建基于公羊学理之上而发出的“盛世危言”,那么如何防止呢?龚自珍的答案是改革。依旧是公羊学思路,首先表明“圣人”制作法制以垂统,孔子作春秋给世人立法。“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绝续,俾枢纽也。”正是因为孔子的制作,所以文明相传不绝如线。“圣人者,不王不霸,而又异天;天异以制作,以制作自为统。”
又如前所述,圣人制作,是因时而动的,既然看到了弊端,就得相应改革,于是在公羊学所内蕴的历史进化的思想上,龚自珍发出了堪为当时最强音的改革呼声:“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龚氏“自改革”法律思想。
魏源的学术路径和人生轨迹和龚自珍相似,他在公羊学学问方面并不突出,但在“经世”这一途上,却比龚自珍走得更远。
首先,魏也用“改制质文”的公羊变革观,来表达自己“变道”的主张,所谓:“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于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和龚自珍相同,他在许多著述中,也多次总结时代的弊病,诸如“堂陛玩谒”、“政令丛琐”、“物力耗匮”、“人才嵬蜶”、“谣俗浇酗”、“边场驰警”等在魏的笔下,世道较之龚自珍益为“衰世”,于是魏的“经世”之志,比龚更强烈。龚多少还用春秋公羊学作为经世的依据,并屡屡引公羊学章句。而到了魏源这里,直接宣称如果经书不能治国经世,那么就是“无用之王道”言下之意,如果能经邦济世,那么即便不用经书,也是符合“先王之道”的。
三、公羊维新:康有为激进变法观
刘逢禄之后,经过龚、魏等人的传播,公羊学作为一门学问,在知识界几成为一门显学,后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受到公羊学的影响。而康有为则将公羊维新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也由此使得公羊学离开其学术本义越来越远。
康是一个有着很大学术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观其在年轻时(28岁)完成的《康子内外篇》就可以看出,他素有构建系统理论的学术倾向,他试图为“天地人”三才,世界万物寻求其基本原理。对于变法,他同样要寻求变法基本义理。此后他受公羊学启发,终于发现了变法的原理,这个原理就通过两本专著表达了出来,这就是学界周知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这两本著作的作用,简言之就是一破一立,前者在于破除人们对此前经典的迷信,根本颠覆传统经学主流观念;而后者将孔子塑造成无所不能的改制先师,直接为变法服务。《新学伪经考》开篇就有惊人之语: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殁,沦于霾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且后世之大祸……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
这几乎一开始就将刘歆、郑玄定为经学之罪人,而给数千年读书人所奉的经典下定语为“伪经”,骤然读之,怎能不骇然。然后康有为从十四个方面来证明当时所传经典为“伪经”,他的主要方法是考辨相关的史传记载为伪,并且经学的传授源流有误。但是其考辨,往往是将推测之语定为铁证,譬如他要证明“六经”完全,即便经过秦火,也没有缺失。其证据是司马迁去圣不远,本人又是今文学家,且自身师承很明白,康氏据此认为“若少(稍)有缺失,宁能不言邪?此为孔子传经存案,可为铁证”以司马迁不记载,就断定一定无,这实在有点强词夺理,至多只能存疑。又如考辨《汉书》刘歆、王莽传,其证据有一条:“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为了证明《歆传》之不可靠,就认定班固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不知康依据为何?像这类论证全书所在多有。很显然,其结论一开始就已经摆出,康氏所做的考证,全是为了服务于这个结论的,所以常常倒因为果,不惜诉诸臆断。
《新学伪经考》一出,就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很快书版就被销毁,后来虽有重版,但很快又遭到保守硕儒抵制而再次被毁。
但即便书版被毁,康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传统经典的不可靠和不可信已经作为一种思潮流行于世,康于是又作《孔子改制考》,堂而皇之地兜售其公羊变法的理论。
全书是在传统公羊学理论框架下写作的,并且接受六经为孔子所作,《春秋》孔子为后世立法开太平之书,孔子素王改制之义。但是康显然走得比传统公羊学家要远得多。在《孔子改制考》中,康首先论证先秦诸子都有改制创教、托古改制的行为,后来孔子创立了儒教,儒教在和各教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孔子独立地制定了六经,孔子法尧舜文王进行托古改制,逐渐成为凌驾于一般世俗权威之上的改制“教主”。康的整个做法,颇有点类似于一种新的“造神运动”,这一点从该书的序言中就表达得很明确:
“天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此制乎,不过于一元中立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世中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
康有为如此“打扮”孔子,实际上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因为要变法,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由谁来推动变法,方具有合理性?如果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不可避免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如何使得这部分人能够做自我牺牲?只有塑造一个超越于世俗王权的改革者,然后以其名义,改革方有合法性。孔子由此被康有为笼罩上了一层强烈的宗教气息,比如他说:
儒者创为儒服,时人多有议之者。亦以为行道自行道,无需变服之诡异。岂知易衣服而不从其礼乐丧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于礼乐丧服之外,人不得议之。此圣人不得已之苦心。故立改正朔,易服色之制。佛亦必令去发,衣袈裟而后皈依也。
这简直是把历代改朝换代时的改正朔、易服色,比附于宗教行为,实在离其历史本义太远,很难让传统读书人信服。所以许多在政见上同情康有为者,也不以孔子改制为然,最终因学术上的分歧,而与康分道扬镳,如朱一新、汪康年等。但是康始终坚持己见,断定孔子为改制教主。原因诚如汪荣祖教授所论:
但康氏正欲转换人心士风以求变,并不计较学术的客观性与正确性,故对朱(朱一新)之答辩,一味坚持孔子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大都口传,难以证实,康氏不过是要托孔子以改制,间接发挥政见,学以致用,原不在学术的精确。
但是以上这两本书都是以学术考证的面貌出现的,康本意是想借公羊学的外衣行鼓吹变法之实,但是却引发了忠诚于公羊学的各家,乃至于传统经学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学术考证而言,这两本书都不可靠,纰漏实在太多。若单纯从变法的角度去看,这两本书并没有提供变法的策略和技术;而若单纯从学术的眼光去看,这两本书则已经超出了传统公羊学的范畴,甚至很多走向了公羊学的反面。比如公羊学独崇孔子,认为只有孔子所传,方为经,也只有孔子,方为改制的素王。而康有为却说诸子都有改制之实,这样一来其效果则是:“说孔子是托古改制,本来是想抬高孔子,结果是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都托古,冲淡了孔子的神圣性,降低了孔子至尊之上的地位,于是诸子学随之兴起,这也是康有为始料所未及的。”这两本书的义例不纯,给后来康的变法活动带来很大甚至完全是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这两本著作,暂且叙述至此。回到我们要解决的本质问题上来,康有为是如何具体用公羊学来支持他的变法改制主张的呢?我们下面就以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以及变法之时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向皇上所上的奏章中,来看看清代公羊学与维新变法的关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针对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条款,用《公羊传》中所揭橥的大义,非常沉痛地写道:“何以为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也就是说,公羊传中认为梁国自弃其民等于亡国,这一种春秋笔法,寓讥刺在内,康以此公羊经文,强调割弃台湾,预示亡国之患就在眼前,故非变法不可。
在同书中,康提出了很多变法的建议,其中关于教育方面,有一条为:“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为什么要增设道学呢,根本上在于“将来圣教施于蛮貘,用夏变夷,在此一举”。这个道理也是直承《公羊传》别夷夏,异内外之义而来,康不想看到中国与外国竞争中,最后重演“中国亦新夷狄也”的悲剧。而在该书的最后,在提到上书的心情时,康又写道:“譬犹父有重病,庶孽知医,虽不得汤药亲尝,亦欲将验方钞进。《公羊》之义,臣子一例。用敢竭尽其愚,”这很明显也是直接援用《公羊》之义,后来这样的语言在康其他的上奏中多次出现,表示其上书的目的是想为国家富强,为变法进一言,即便所献之方不够灵验,甚至有误,但是内心的忠诚日月可鉴,春秋许止进药,孔子是之,君子原心,希冀用此打动统治者。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初八日,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又奏上《上清帝第四书》,仍旧强调“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的道理,鼓吹变法,其中的重要证据就是“公羊”之义:“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王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提到的“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一句,几乎成为后来变法包括具体的制度变革指导思想,尽管康自己也并未意识到。但事实上,就是“托古改制”,加上一点西洋舶来的政治理念。而所谓“穷经义”,最重要者,仍是通“公羊”之义,而非汉学家孜孜以求的琐碎考据。
为了更明确地表明变法改制的立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初一日,康有为奏上“清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并呈《孔子改制考》”一折,其中论道:
中国圣人实为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若大教沦亡,则垂至纲常废坠,君臣道息,皇上谁与此国哉……臣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崇孔子,无以维人心而励忠义,此又变法之本也。
康有为所称的“变法之本”,在于廓清伪经、尊崇孔子之后,慢慢地培养出一批新人,以这些新人为王前驱,实现变法维新之志业。此前康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所本的就是这个精神。与其说康在培养学术传人,毋宁说是在培养政治人才。康在这个奏折中还勉励皇帝接续孔子改制精髓,支持变法事业,所用依据同样来源于公羊学:
臣考孔子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出焉。故孟子称孔子《春秋》为天子之事。董仲舒为汉代纯儒,称孔子为改制新王,周汉之世,传说无异,故后世祀孔子皆用天子礼乐…伏惟皇上典学传心,上接孔子之传,以明孔子之道。
且康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八日“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中,又提到科举所用经义,特别提到《春秋公羊》,未及《左传》和《谷粱》,也从某种侧面上说明了康有为的公羊家底色:“经以《诗》为一科,《书》、《易》二科,《仪礼》、《礼记》为一科,《春秋公羊》为一科,凡五经分为五科。”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三日,在变法主张终于获得光绪皇帝认可,并得到编书的任务之后,针对《孔子改制考》引发的争论,康又向光绪帝奏上“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一折,为自己辩诬:他首先认为,自己著书的苦心未获得人们的体谅,“即如《孔子改制考》一书,臣别有苦心,诸臣多有未能达此意者”。随后,康又向皇帝申说公羊义理以及他如此塑造孔子形象的理由:
臣考古先圣人,莫大于孔子,而系《易》著穷通变久之义,《论语》有夏时殷珞之文,盖损益三代,变通宜民,道主日新,不闻泥古。孔子之所以为圣,实在是。故汉以前,儒者皆称孔子为改制,纯儒董仲舒尤累言之。改者,变也;制者,法也。盖谓孔子为变法之圣人也。自后世大义不明,视孔子为据守古法之人,视六经委先王陈迹之作。于是守旧之习气,深入人心,至今为梗。既乖先王陈迹之作,尤窒国家维新之机。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藉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
正因为守旧势力太过强大,在“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氛围中,为了唤醒保守派,赢得更多人支持变法,康不得不下猛药,这剂猛药就是《孔子改制考》。康并且还解释孔子之所以如此不惮烦琐而岌岌于改制,乃:
孔子《春秋》明新王改制,必徙居处,改正硕,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何为纷纷,不惮烦哉?以为不如是,不能易天下人之心思,移天下人之耳目也……故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
这样,康最终要表达的主题就出来了,就是要变,不但要变,还要全变,急变。之所以这么激进,当然有康个性问题,康性情本来就很急躁,当然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危机紧迫。还是在这年六月,康向皇帝奏上《日本书目志》等鼓吹变法的书籍,再四强调的,仍是一个“变”字,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康写道:
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由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
而康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存亡绝续之际;国家面临的危险,有被列强瓜分之虞,在呈给皇帝的《波兰分灭记》的序中,康引经据典,提到“《传》谓: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这是引用《左传》中的一段话,强调在列国纷争时,要敢于面对现实,参与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会灭亡。如何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呢,只有变法一途。
从以上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在向皇帝提出变法主张时,所用的劝说工具,脱不开春秋公羊之义。此外,在很多奏章中,即便没有只字片言提到春秋公羊,但整个风格仍旧不脱公羊学底子,比如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康在一封上书中,提到“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宜也”。这个不过是“文质改制”、“三世说”的推衍,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康有为又提到:“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同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随后康又引《易经》中的“穷通变久”之说,以及董仲舒的“为政不调,更张谓理”之说,来佐证其变法的正当性。
所以,康有为变法的主张,将公羊学发挥到了极致,当然除了公羊学外,康有为的改制学理,还有舶来的西学,但是细细研读,发现西学只是他改制理论的外衣,流于“器”的层面,而公羊学才是其学理的底子,是“道”之所在。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公羊学至此,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康有为将公羊学,改造成了一门激进的变法之学,将传统公羊学中的孔子形象颠覆,成为变法圣教主,同时与诸子并列竞争,这不仅让视孔子为“至圣先师”、“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道德圣人的传统士人惊愕,即便是在其他公羊人士看来,也难以接受。如前所述,甚至在变法过程中,同属于“维新”阵营的人士,也为此争辩不已。康的缘饰经术的行为招致了大量的恶感,连曾经支持他的帝师翁同龢也批判康“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很明显,这个情形是康在推衍其公羊学经术所未能预料到的。
康有为的变法很快失败,其公羊学著述自然也成为惑乱黔首之书而遭官方查禁,尽管民间仍有流通,但此后任何人都再难借公羊学掀起波澜。而到庚子事变之后,清廷名正言顺地下诏“新政”,朝廷由此前的排外一变而转为媚外,此后西学入开闸之水,一拥而入中华。到这个时候,不要说《公羊传》,就是其他一切传统经典,在更为直接的自西徂东的改革思想面前,统统失去了战斗力。改革派人士可以堂堂正正地对西籍引经据典,而不需要再像数年前缘饰儒经了,毕竟所谓“宪政”、“民主”、“人权”等词皆是外来语汇,直引西学似乎更为便利。不过这又开起了一股轻薄浮躁的学风。回到公羊学来,康有为立足公羊学进行变法,只是偏离了公羊学正途,最终与公羊学一同退出变法的舞台。历史之吊诡,令人唏嘘。
四、小结:公羊学——由学术到政治
清代公羊学的复兴,一开始的契机在于对汉学的反动(或者说是与汉学的竞争)所致,其学由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启其端,刘逢禄最终完成。但是因为随着民族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重,公羊学中内蕴的变革思潮和解释多元性被日益纳入到“致用”的环节上,从而开始逐渐偏离学术的轨道。正如有学者所谈的那样:
经学一旦强调“致用”,对经典所注重的就不会是陈旧的本义,而必然是溢出经典字句以外能“致用”于当下社会的新义,经典及经学的价值取向就不会拘泥于固守“德性”范围,而必然会指向认知新知识、打造新观念的方向。
故而,晚清公羊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学术研究到政治应用的过程。继刘逢禄之后,诸立足于公羊学而持变革主张者,逐渐由对经典的重新诠释,进化到追寻经典背后的多重意蕴,到最后经典只是被他们作为一个幌子,而其真正的目的是“经世”乃至“变革”。这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龚自珍、魏源时代,虽然他们也主张变革,但是危机似乎还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所以他们所揭橥的公羊学,停留在对旧制度的修补之上,构成一种温和的变法理论。而到了康有为的时代,国势江河日下,变革之势客观上显得极为紧迫之时,康已经不满足于阐发传统的公羊之义了,而要求一种更为激进的变法理论。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传统经史子集仍是士人普遍的知识框架,若一味用西法西籍来号召变法,效果可想而知。且“事实上,晚清变法家若无传统学问之素养,便难以发挥其言论之效力。新思想若无本国语言之词汇表达;若无本国历史文化之例子作譬,新意思亦不能表达”。且限于康自身的知识框架故,他也不可能开出西式的药方。于是剩下的途径,就是改造传统的公羊学,将之改成为适应变法之需的形态,可是这样一来,其离开原本的学术面貌却越来越远。所以公羊学的复兴,端赖一“变”字,而公羊学最后式微,同样在一“变”字。
即便如此,我们也无须为公羊学唱挽歌,公羊学在历史上的盛衰,本就应时而变,且没有哪一种学问能够永远显达。何况,晚清的公羊学即便最后退隐,但它可能是开出现代化道路的最大的一门本土学问,它使得人们的视野摆脱了传统儒家“天下”观,而进入“世界”的范畴,它所揭橥的“变法”之义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国家的现代、富强而努力奋斗,有此因缘,又何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