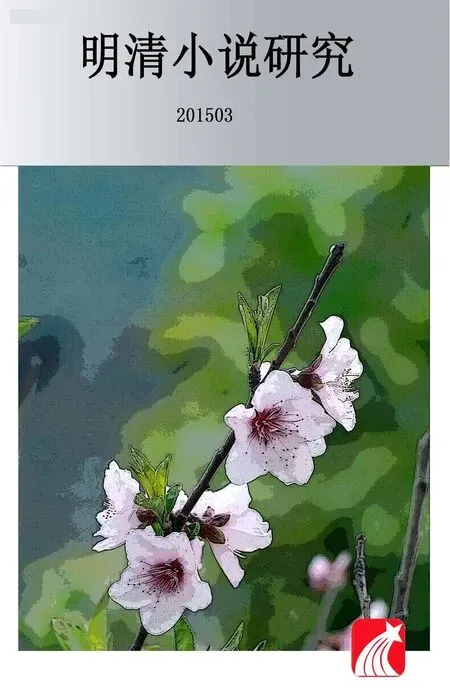中国古代小说对东亚小说影响的序列及模式
2015-11-14刘廷乾
·刘廷乾·
“东亚”主要指汉字文化圏中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古代朝鲜半岛、日本群岛、越南半岛,具体可以朝鲜、日本、越南称之。本文主要谈四个问题:其一,中国小说史中各时代小说在东亚三国的影响;其二,中国古代小说体裁、题材方面在东亚三国的影响;其三,东亚三国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过程与接受方式;其四,东亚三国受中国古代小说影响在其小说创作中产生的模式与类型。前两个问题侧重于从小说输出国角度立论,后两个问题则侧重于从小说接受国角度立论。
一、中国各时代小说在东亚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朝鲜、日本的影响,就中国小说史角度而言,并非是按中国小说史的进程而呈现出均衡式或依次递进式的特征的,而是有选择有起伏的。三国间体现出一定共性化的特征,即中国唐前以杂史、杂传、志怪书为主的作品,唐人小说,明清小说,三个阶段的小说对三国影响较大,影响最大者为明代小说,宋元小说的影响最低,明清小说中明代小说的影响又大于清代小说。
东亚三国的小说萌生,也基本都以杂史、杂传、志怪书作为小说的“前源”,这也更加印证了中国文化对三国文学的深深滋养。作为越南汉文小说开端的《粤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属于此类作品,朝鲜汉文小说开端的崔致远的《新罗殊异传》,以及后来的李奎报、李齐贤、李仁老、崔滋、林椿等人的“稗说体”、“假传体”等也属于此类,日本现存最早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记、纪神话”也是含有一定小说元素的史传志怪类,而且也属于日本小说的起步,这些都在说明中国汉晋六朝的一些准小说性质的作品对东亚三国小说的萌生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人小说的影响以日本最具典型性,唐人小说的早期作品张文成的《游仙窟》在作者生前可能就已传入日本,而日本同一时代的小说《浦岛子传》就受了《游仙窟》的影响,《浦岛子传》也是日本最早而成熟的汉文小说。而东亚三国汉文小说史上还有一个足以引起重视的现象,那就是明初小说集《剪灯新话》对三国汉文小说创作皆产生了巨大影响,越南受其影响产生了世界性名著阮屿的《传奇漫录》;朝鲜名作金时习的《金鳌新话》是其影响下的产物;日本名作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乃至《伽婢子》之前的《怪谈全书》《奇异怪谈集》等,皆受《剪灯新话》的影响。这里必须作一个明确判断,《剪灯新话》虽是元末明初作品,但它的题材上有宋文言小说烟粉灵怪类特色,而它的文体特征、运笔风格、美学风范,尤其是小说的诗化特色都是继承于唐人小说的。东亚三国小说创作皆青睐于《剪灯新话》,与其说是向明代小说学习,毋宁说是通过时间差最近的范本借以向唐人小说学习,则更为恰切。
宋元小说即使在中国当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研究者虽探掘其数量庞大,但传世者并不显见。从中国小说在东亚三国的传播情况看,宋元小说也是其中的罕见现象,自然三国小说受宋元小说影响的痕迹亦不易寻觅。宋元小说从某种角度而言,堪称明代小说之母体,而明代又是中国小说大繁荣时期,从域内到域外,宋元小说的这种命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比较而言,明代以及清初小说对东亚小说尤其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最巨,既有少数名作如《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等对东亚三国汉文小说影响下的“点”上的高度,也有全类小说影响下的“面”上的广度,还有于中国国内并不甚显著的小说于域外独被青目的个性化影响,如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所形成的“越南热”现象,中国的情色小说对日本小说影响所产生的“好色”系列,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家庭小说对朝鲜小说影响所产生的“家门”系列等。在下文小说体裁、题材方面的影响中还要重点论述。
东亚三国受清代小说的影响比明代为逊,有其诸多原因。清代小说尤其是清代初中叶的小说传入东亚三国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三国的文人到中国交流的也仍然相当频繁,这主要缘于商业与交通条件的改善与提高,尤其是民间渠道的兴旺已胜过官方,也非官方所能绝对掌控。但此期缘于中国的文学传播与文学影响并不一定总处在一个相辅相成的正向关系上,传播的规模并不必然决定着受影响程度的大小,因为三国受汉文小说影响而在创作上的表现,将更强地受到本国社会现实的影响特别是国政的调控。三国间既有一定的共性体现,也有各自的个性展示。
其共性体现主要有:一是由对汉文化的向往自然对中国的汉族政权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满清自然有一种违和感。与之为邻、知之更深的朝鲜更称清为“胡”、为“夷”,因而在国家文化层面,对清朝文化会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性;二是该期三国各自的民族文化独立情绪更加高涨,如日本、朝鲜都有不同程度的革新,致力于完善本民族文化、文学品格;三是三国小说皆主要是借明代小说而先于汉文小说领域成熟起来,同时也自然带动了本民族语言小说文学的成熟,而成熟后摆脱外来依赖,产生排“汉”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四是清小说逊于明小说对三国的影响,还有一个客观事实,即文学有一定惯性,不会戛然而止,但从源地创作到传播流入再到借鉴模仿之作出现要有一个时间差,明小说在三国的影响而产生的本国创作,大都在相对应的中国清朝初中期出现即是例证;五是随着小说艺术的成熟及各国各自民族元素的增强,其受中国小说如清小说的影响已化用无痕而不知。
具体各国又有所不同。朝鲜曾于1627、1636年遭清朝两次入侵,在俯首称臣中严重损伤了民族自尊,对比与明朝的和谐关系,更增强了其排满情绪。至18世纪末,朝鲜又由于内外矛盾而实行“锁国攘夷”政策,企图与外隔绝;日本恰于明清之际进入幕府王朝的江户时代,此后亦实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此期的日本又出现了与朝鲜因乱而趋弱所不同的稳定而迅速强盛的局面,民族自信心亦迅速升温;日本与朝鲜本就比较早的产生了本国文字,在与汉文学的共存共长中本国语言之文学比越南有了自立的更早更足的底气,其去汉化也表现得更突出;越南也恰于明、清易代之际,在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却陷进了后黎政局最为复杂的长期的南、北对峙和郑、阮纷争局面,颇有自顾不暇之势,到19世纪又遭法国入侵,并成为其殖民地,文化亦被迅速殖民化;越南脱离中国版图后的自立王朝时期又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藩属,比很早就不受中国约束的朝鲜和始终独立的日本又有不同,其民族独立情绪更加高涨,尤其在明初入侵之时。但越南的本民族文字产生较晚,而且其民族文字喃字又严重依赖汉字而难以全面普及,结果其文学、其小说不得不比其他二国更依赖于中国,但18世纪毕竟是越南喃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综合而言,其小说受清代的影响仍然弱于明代。
二、中国古代小说在体裁、题材上对东亚小说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朝鲜、日本的影响,就体裁、题材角度而言,有其各自的选择与侧重。
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形式一般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类。在东亚三国,笔记体小说皆是小说史的首起和三国共选的文体,并藉此领域而使小说走向成熟。三国此种小说,大致有三类:一是粗陈梗概式的杂史杂传而又以志怪为主要特色的“准小说”类,此近于中国的晋;二是构思繁细文采华美的烟粉灵怪类,此近于中国的唐;三是其他文人笔记体,此类又颇为庞杂而难以尽归小说一体。这些都与中国的小说发展史颇为相通,尤其前二类,又都构成三国小说由初起到成熟的相承相递关系,与中国由魏晋六朝的杂史杂传志怪类到唐小说的成熟有一致性,只是有一个时间差而已。越南的汉文小说初起于《越甸幽灵集》《岭南摭怪》等,成熟于《传奇漫录》;朝鲜的汉文小说初起于《新罗殊异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成熟于《金鳌新话》;日本的汉文小说初起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成熟于《浦岛子传》,皆可为证。
话本体小说在中国,不仅有鲜明而独具个性的文体特征,而且由于其来源于宋“说话”艺术,而保持着讲说特色与主要面向市民的生活化、通俗化与劝诫化品格。这决定着此种小说文体有更苛刻的条件选择性,而且需要从内容到形式的双重满足性。因而对东亚三国来说,它也是最难以消化吸收的一种小说文体,故此种文体在三国的表现为弱,其学习的主要对象是“三言”、“二拍”,但文体形式上的变异还是显见的。越南从现存汉文小说中还未见有明显而集中式的学习模仿之作;朝鲜受“三言”、“二拍”影响的小说如《东野汇辑》《青邱野谈》《青野谈薮》《破睡篇》《海东野书》《此山笔谈》等,并不是话本体,而是笔记体,只是其选材与文笔上的市民化、世俗性上与“三言”、“二拍”相通。个别篇章如《还狐裘新旧合缘》与《喻世明言》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月峰记》与《警世通言》之《苏知县罗衫再合》,《轿中纳鬟俇贼师》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彼此间都有明显的借鉴模仿关系,但也只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作为话本典型文体特征的入话、头回等形式上的东西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无法复制。话本小说内涵上的鲜明市民化色彩,在日本倒有很好的士壤,日本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兴盛,这与中国晚明社会的市民文化兴盛所推动的话本小说杰作“三言”、“二拍”出现的背景颇为相类,因而日本有更为成功的受“三言”影响的杰作出现,如都贺庭钟的《英草子》、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等,都堪称典范。但也只是与“三言”相关作品在市民化的精神内涵上的相通,及人物、情节层面的模仿等,也不是从文体内容到文体形式上的全面借鉴。《雨月物语》即是鲜明例证,同一部书有些篇章模仿了《剪灯新话》,有些作品却模仿了“三言”,而《新话》与“三言”在中国却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区别的两种小说文体,至少在语言上一是典雅的文言一是通俗的白话,而《雨月物语》皆统一为雅致的文言,语言风格上就非话本风范。因而,话本体在东亚三国既借鉴应用少,又难以达到吸收全化,文化传统与应用土壤等有别使然。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只有章回体一种体制,因而受此影响的东亚三国的长篇小说,也几乎都采用了章回体的体制,甚至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所遗存的说话艺术的痕迹,诸如一些套语、事件发展的节点控制等,也都有所袭用。但毕竟国情有不同,文化有差异,且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晚出者,源出者与接受者也有一定的创作功力上的差距,因而东亚三国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文体形式上“集”、“卷”、“章”、“回”、“节”混用不一,乃至回下分节、有卷无回、有回无目等同时存在;且大多回数不多,不像中国明清两代的长篇,动辄上百回;尤其在语言使用上,亦无法达到像中国小说那样运用适时适俗的白话如盐入水般无痕,严格说,这些国家的长篇章回体小说语言,只可算是学习于中国书面式的浅近文言,即使与中国汉文传统始终如影随形的越南也难达到。
至于小说题材方面的影响,则与东亚三国各自的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的联系更加密切,或者说,题材上的偏爱与侧重是基于其本国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中国古代小说进入明代全盛之后,其题材一般总括为四大类: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清中叶后则演变为侠义公案)、神怪、世情,个别分类如世情类太过笼统庞杂。东亚三国汉文小说题材未必全合于这四大类,但以这四类为观测平台仍有合理性。从三国小说史看,志怪类题材是共同的选择,因为三国都有这样的小说史开端,都藉小说的形式解释生民创世神话或婚姻家庭等基本的社会关系,出之以怪异也可看作是小说虚构性的锻炼。至于其他与中国小说题材的或强或弱的对应关系则不作赘述,只以其基于本国国情而于小说题材上的个性化选择作一简述。
这种个性化选择也是其国汉文小说题材表现上的亮点。越南独立之后的历代王朝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即使王朝内部亦常纷争不息,再加之外侵他国与他国入侵,社会始终处于板荡之中,故一部越南独立史也是一部战争史;越南史学著作颇富,却缺乏连续的断代史,这既开拓了修史补史的风尚,又留下大量空白可补。同时即使被称为正史的书籍,也往往有引杂史杂传甚至志怪题材入正史的不严谨处,亦形成一种创作影响。以故,比之朝鲜、日本,越南汉文小说中的战争历史类题材更加集中而突出,也成为其汉文长篇小说的主体与代表。从最早的《驩州记》,到《皇越春秋》《越南开国志传》《皇黎一统志》《皇越龙兴志》等,形成完整的断代史系列。因其写战争的特性,又皆有明显的向中国典范的战争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借鉴模仿的痕迹。
日本自1192年进入镰仓室町时期,自1603年进入江户时代,不管是武人政权的室町时期,还是幕府政治的江户时期,共同造就了社会两大阶层的出现,一是武士阶层的壮大,一是町人阶层的崛起,文化亦由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家文化向江户时代的庶民文化转型。这一时期贯穿了中国的宋末到清代,而转折期恰是中国晚明小说全盛期,又是日本小说的成熟兴盛期,因而中国小说中的两大题材——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类,以《金瓶梅》为瞻首的艳情类及以“三言”为代表的市民类(此两者皆可归于世情类),恰适应日本此期的社会现实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而日本小说史中有这样几类小说成为其亮点:一是英雄传奇类,主要受《水浒传》影响,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忠臣水浒传》《南总里见八犬传》等;二是世情类,有受17世纪末日本开创的“浮世绘”直接影响,同时也不排除受中国艳情小说影响的“好色”系列,如《日本永代藏》《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等。有受“三言”影响的《英草子》《雨月物语》等。日本小说的杰作也基本包含于这几类中,如《南总里见八犬传》《英草子》《雨月物语》等。
朝鲜受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颇深,其与中国明朝的关系也比日本、越南更为亲近、融洽,故其以婚姻、家庭为取材特色的汉文小说创作有出群之誉,这类小说从影响源看,受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家庭小说的影响为大,代表性的有《九云梦》《春香传》《谢氏南征记》等。而且,婚姻、伦理又常与社会动乱、时代政治相联系,虽体制不一定宏大,但反映的思想内涵却颇为深广。
越南、日本、朝鲜皆出现过“《剪灯新话》热”,越南有“《三国演义》热”,日本有“《水浒传》热”,朝鲜有“才子佳人小说热”,这些有趣现象见微知著,亦能说明东亚三国小说的取材偏好。
三、东亚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过程与接受方式
从接受国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三国的传播与影响,有一段比较清晰的接受史。
一是各种注解、训点、翻译等。
前提是本国语言产生后,对传入的汉文小说,就字词语句、专名专号、典要故实等,以本国语言注解,目的是帮助一些汉文程度不高者理解原著。在朝鲜的有“谚解”,在日本的有“和训”等。
朝鲜以谚文所做的“句解”已成一种传统,《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太平广记》等皆有,或名“句解”,或名“谚解”,或名“语录”,名虽不同,实则同归。《三国演义语录》收词条159个,《水浒传语录》收词条1371个,《西游记语录》收词条1856个,《太平广记》有《太平广记详节》,还有《太平广记谚解》,连《镜花缘》这样的书也被训译成《第一奇谚》。
最具典型性的是对《剪灯新话》的谚解,朝鲜文人林芑于1549年就完成了《剪灯新话句解》,另一朝鲜文人尹春年亦参与了此项工作。其影响之大在朝鲜壬辰倭乱时传入日本,日本曾两度以活字翻印该书,还配合着将朝鲜版的《剪灯新话》也进行了翻排,成为中国小说对外传播中的一道靓丽景观。
除了对中国小说作一对一式的“谚解”、“和训”外,朝、日间还出现了一些针对汉语学习及中国小说群体的带有综合性、工具性的辞书。朝鲜早在15世纪李朝时就刊印出学习汉语的用书《朴通事谚解》,1669年将《水浒传》《西游记》两书中的难词难句辑成了《小说语录》一书。日本于18世纪末,为配合“三言”等明清白话小说在日本的传播,而出了一本中国俗语辞书《小说字汇》,19世纪还有《小说字林》等。
如果说训解还只是对汉文小说作局部难点的处理以助于汉文水平低者对其理解的话,翻译则是对与汉文无缘者尤其平民及女性阶层的一种更全面普及。日本的“唐通事”就是兼具汉文翻译的人员,尤其江户时期,入籍日本被称为“住宅唐人”的明清商人,因通晓日汉双语而承担此职。日本对汉文小说常采用摘录而重编的“编译”方式,以“软化唐言使之成为日语”。朝鲜则更为规范,李朝开国之初即设“司译院”,订立制度以培育汉译人员。他们对传入的汉文小说,或全译,或节译(类于日本的编译),或谚解,以国家行为促进汉文小说的内化。
以上注解、训点、翻译诸方式在越南是一个可以省略的过程,因为越南始终使用与中国同一的汉文,其在汉字基础上诞生的喃字、喃文并没有普及成为全民语言,既难以承担训译之责,也实无必要。
二是改写、仿作、翻案等。
上一环节的注解、训点、翻译等仍属于传播接受方式,此一环节则是进入由汉文小说所引导的小说创作层面了,是东亚三国汉文小说史上的普遍而共有的现象。
“翻案”一词盛行日本,也最具代表性,但其义域却颇为宽泛,既指将汉文原著脱换地名、人名及背景等,使之变成发生于本国的人和事,这种表面的局部文字改动式,类于“改写”;又指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脱胎于中国原著而实为本国题材式的创作,类于“仿作”;还指或整体或局部引入中国小说元素的创作,如人物的模仿、情节的套用、结构手法的借鉴,甚至直接借中国元素以言说的移植等,类于“借鉴”。总之皆与中国小说相关。而实际创作中,三个方面的表现又非截然分明,亦可能是一种综合运用。但“翻案”的这三种表现形态,对东亚三国的汉文小说创作皆有覆盖作用。
三是作品中汉语与本国语言的双语并用。
日本的本民族语言“假名”文字在三国中产生最早,始创于9世纪,到10世纪才逐渐得到普及;越南可称为民族文字的“喃字”最早见于12世纪末,直至15世纪初才略有发展;朝鲜“谚文”始创于15世纪,虽略晚,但发展远好于越南。三国民族文字在其初,都有相似的命运:或处于以汉字为正统的非正统地位,或用于下层民间而不登大雅之堂。日本文字以“假名”称之,对应的是汉字的“真名”。假名文字最初只用于下层与女性,又有女性文字之称,假名文学亦属于女性或私下场合之文学。越南人称汉字为“儒字”、“圣贤的字”,喃字多用于以土语方音口头记诵的文体。在朝鲜,汉字写成的文学才是文学,而谚文作品只是“俗讴”、“俚语”而已。
而在民族文化逐渐发展自立的过程中,三国以汉文为主的小说,有些又不同程度地杂以本国民族文字,形成双语并用现象。这其中寓含着不易觉察的意义:一则说明民族文字地位的提高,可以接轨于高雅正统的汉文学;一则说明民族语言欲借成熟的汉文学而走向文学征途上的自立;一则说明汉文学在其文学史上的由强而弱并最终淡出的必然趋势。
于汉文小说中又产生了若干形式:
日本的“歌物语”式。“歌物语”是指日本某些小说借鉴唐代传奇小说模式,于结尾处附加作者的论赞,而将论赞换成一首和歌。如《浦岛子传》《伊势物语》等即是。
日本的“汉和混合体”。汉语中夹杂着日语,或以汉字标注日语读音,或用汉字表达日语语法特点,如“万叶假名”。
朝鲜的“汉文悬吐本”。基本为汉文,又夹进民族语言的虚词(或词尾),以帮助读者阅读。
民族文字的比重逐渐加大,乃至以民族文字为主汉文为辅。如越南受中国青心才人小说《金云翘传》影响而生产的《桃花梦记——续断肠新声》(又分为《会真记》《桃花梦》两篇)一书,其结构形式是:汉文回目、汉文回前评、喃文正文、汉文回末套语,则喃文成了主体。此种演进发展至极致是完全以民族文字改编汉文小说,如越南阮攸将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改编成同名“喃传”,除此篇外,喃传中还有大量改编自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品。
四是同一作品的双语互译存在状态。
这种双语互译并非指将汉文小说原著译成本民族文字的方式,而是指在汉文小说影响下的本国创作的小说作品,有的原初创作是汉文,同时又译成了本国语言,有的则相反,原初创作是本国文字,却又译成了汉文。而且这种双语互译式,又不是简单的直译,常是一种再创作式的编译。也就是说,同一题材,有出自不同人手、不同语言的两种存在状态,甚至形成各自语言的版本系统,一种先出,后出者以先出者为蓝本。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极为鲜见,它出现在古代朝鲜。
朝鲜小说《九云梦》最早出以汉文本,后出以韩文本。《壬辰录》最早出以韩文本,后出以汉文本。金万重《谢氏南征记》始以韩文,其堂孙金春泽又译成汉文,汉文本仿中国章回体作了体制上的规范,内容上也比原作大为丰富,由此才广为流传。《玉楼梦》有版本十余种,多为韩文本,也有汉文悬吐本。朝鲜名作《春香传》的版本有数十种之多,既有朝鲜国语本《谚文春香传》、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京版《春香传》,又有汉文本《广寒楼记》和《汉文春香传》等。
不管是初为汉文体而译为韩文体,还是初为韩文体而译为汉文体,既显示着汉、韩两种语言在小说创作中的纯熟运用,又透露着汉文小说优越地位的惯性。这种奇特现象显性体现于汉文小说朝鲜接受史的末期,民族语言的小说已登堂入室,却对以汉文进行小说创作仍有无限留恋,亦足以说明中国小说的影响力。
四、东亚受中国古代小说影响在其小说创作中产生的模式与类型
仅从中国小说在东亚三国的传播接受角度观测,还不足以深悉其所受影响的程度,还要从其整个小说创作史角度去考察中国小说在其中的深化与内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观测点,即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在其小说史上所形成的一些独具内涵且带有主导性的创作模式,这些创作模式融会贯通着小说输出国与受容国的双边因素,主要体现于其汉文小说史中,同时也影响着其本国语言小说的创作。
朝鲜汉文小说形成的主要创作模式有:
(一)假传体小说
假传体中的“假”应为假借以虚构之意,即借非情感类的器物以拟人化手法描写,以表达某种寓意,发抒作者的感慨。它既有小说文体属性的标示,也有题材与创作手法的独特性的标示。假传体实际是学习中国文学基础上的创新性文体,系杂揉中国史传和寓言而成,其作为“传”体来自于史传,其拟人以寓意的选材与手法来自于寓言,主体上仍具有寓言属性,但中国的寓言在先秦为诸子文章中用以说理的片断,独立成体后主要隶籍于散文领域。朝鲜此体已突破了寓言的文体框架,而呈现小说化,甚至发展出按鉴演义的远比寓言本体更宏大的小说体式,因而可为朝鲜独立之小说一体。高丽朝是假传体的发展期,林椿、李奎报、崔瀣、释息影庵等堪为代表;李氏朝鲜是假传体的繁荣期,林泳、安鼎福、李颐淳、柳本学、李钰等可称作家。
(二)梦游小说
梦游小说,顾名思义,即涉梦小说,它有固定模式:入梦——梦境——梦觉,对应于现实——梦幻——现实,其内容是借梦幻形式,或感人生,或言功名,或写战争,或诉恋情,以详于梦境,来强烈对比于现实,总以士人心态为依归。此类小说是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樱桃青衣》等影响下的产物,结构、主题、风格乃至诗笔都有承袭与借鉴。但不是对唐人此类小说的步趋,唐人小说多为独立单篇式,篇制不宏,多短篇小制。而朝鲜此类小说是继承中的创新,发展出带回目的章回体长篇体制,内涵更为丰富。《九云梦》是典范。且此类小说自李氏朝鲜初期出现,历三个世纪而不衰,亦有中国所不及的规模,也可证见其茂盛生长的朝鲜社会土壤。
(三)家门小说
家门小说是指以家庭生活、家庭伦理并兼及社会现实为创作题材的小说。此类小说是古代朝鲜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影响,并结合朝鲜社会现实的产物。小说源则来自于中国家庭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世情小说的多元化影响,故体制上多为长篇章回体。它在小说内涵上有所新变,其婚姻政治化的特色比中国同类小说更为浓郁。此类小说主要兴盛于17至19世纪,正是朝鲜外患于清倭、内忧于党争的动乱时期,因而借家庭以反映现实的小说内涵不弱。《九云记》《谢氏南征记》《玉楼记》等都是有影响的力作。
(四)军谈小说
军谈小说是以军事战争为题材,以历史和民族英雄的军人为描写对象,以表达民族情感为主要立意的小说。显然以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为主要参考,也不乏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子。与中国同类小说相比有新变,一是不重战争史实本身,而重在“谈”,即重在传达对历史与战争的理解与评判;二是小说的主人公往往从生写到死,有“一代记”的特色。此类小说多以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为背景,有汉文的,也有谚文的,汉文军谈小说的力作有《壬辰录》《帷幄龟鉴》《南洪亮传》等。
越南小说模式从借鉴中国又有所创新与强化的角度而言,有两种颇值得言说:
(一)传奇小说
传奇小说本来自于唐人的一类小说。在中国,传奇小说是小说的一种体制还是小说的手法与风格向存争议,在越南则颇有向小说体制强化的趋向,这主要源于阮屿的名著《传奇漫录》的影响。阮屿此作从题材、手法、风格乃至篇章数目都趋步瞿佑之《剪灯新话》,而在越南,趋步阮屿者,又有段氏点的《传奇新谱》、托名黎圣宗的《圣宗遗草》、范贵适的《新传奇录》等,从而形成一个传奇小说系列。阮屿虽直接模仿明初瞿佑的作品,但他的诗笔运用以及于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浓郁的诗化色彩却是直追唐人,后继者段氏点更是将这种诗化性发展到极致,其《传奇新谱》甚至达到一个短篇加入四十余首诗歌的程度,题材的传奇性倒不是首要,小说诗化风格的追求反成为重要特色,这种文言散体文中加入诗歌韵文所形成的诗文小说,就是唐人传奇的文体本质。由阮屿到段氏点的创作,实际已有了一个更重形式特征的小的转变,虽然都直接由瞿佑而来,但瞿佑的《新话》首重的还是题材上的传奇性,而段时点却更触摸到唐人小说形式上的本质属性,因而有向小说体制强化的表现。越南于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还属于中国版图,因而比之朝、日两国有更纯正更悠久更强大的汉诗传统,此类诗化小说在东亚三国中唯越南得天独厚,显示着汉文诗、汉文小说两相结合于越南汉文学中的高度。相比之下,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志怪体、历史演义体,倒较少发明。
(二)喃传体小说
诗歌影响小说,小说影响诗歌,相互影响而达如盐化水,东亚三国中,唯越南达此高度;而诗与小说渗透交融开拓出具有本国民族特色的新型文体,也唯越南所独有。这就是越南“喃传”。喃传是喃字文学的代表文体,喃字借鉴于中国汉字而产生,喃传则借鉴于中国诗歌而成体,出新为“六八体”和“双七六八体”两种格律体。其用于长篇叙事,则有似长篇叙事诗;但它又体现为小说式的虚构性与重人物形象塑造性,从现存作品看,其题材源主要来自于中国,其题材特色主要改编自中国的小说戏曲,而尤以改编自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为最具特色,其杰作阮攸的《金云翘传》(亦名《断肠新声》)就改编自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因而它实际是一种诗体小说;它又以越南方音演唱,是一种演唱文学。所以,喃传实为一名而兼三体。喃传充分体现出中国诗歌、中国小说交互影响的魅力,惜喃字以汉字标越音的先天局限,限制了喃字文学的发展规模,不然的话,它将是中越文学最值得称道的“混血儿”。
日本小说史上出现的一些创作模式最值得作综合研究,主要有:(一)物语小说,(二)草子小说,(三)读本小说,(四)翻案小说。与朝鲜、越南的小说模式具体指向文体、题材、手法与风格等方面有所不同,日本的这些小说模式则指向了综合性的文学创作传统,而在其传统中又附载着许多关联。如物语小说、草子小说、读本小说关联着日本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三者自前而后形成日本古代小说史的主导脉络。又关联着小说文体内、外,即这些概念涵盖的主体是小说,有的也兼及其他文体;翻案小说则既关联着与汉文小说的关系,又关联着对汉文小说的态度与原则。
“物语”一词有“讲述”、“故事”等多种义项,它很难说是一种具体的小说文体,因为它既指散文体小说,也指其他文体;既有古代的物语,也有标为物语的近世作品。它又有多种细类,而又纷杂不一:历史物语、军纪物语是题材的标记,传奇物语、写实物语是笔法的标记,而说话物语又有表达与传播方式的标记性,等等。倒不如把物语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创作传统更为贴切,它的义项虽有多种,但“讲述”与“故事”是主要特色,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恰是中国宋代“说话”艺术的特色,宋说话艺术对明代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为其母体,而中国人对明清小说的一个最通俗、最朴素的认识,便是“无巧不成书”,此语是说故事写得好、讲得好。所以繁荣时代的中国小说“故事性”是第一位的,注重情节的发展与故事的构建,也是中国小说尤其是宋以后小说的最大特色。日本古代物语小说与此也不无关系,日本平安至室町时期,是物语小说的主要时代,正好与中国的宋至明相对,11世纪初的《源氏物语》是物语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镰仓时期的《平家物语》是物语文学的另一杰作,其时对应于中国的南宋,而它又是一部说唱之作。可以说,日本古代的物语小说与中国宋代“说话”艺术有关联,讲述式、故事性正是这类小说的创作传统。
草子文学之草子小说也不是一种确定的文体概念,广义的草子是指用“假名”写成的物语小说及其他文体,狭义的草子指日本中世与近世以通俗小说为主的通俗读物。因假名文字在初始期属于女性与社会底层大众文字,它影响了这类草子小说的世俗本色与市民趣味,特别是“浮世草子”,于草子小说中产生了央央大宗的“好色”系列,颇与晚明艳情小说的世俗本色与市民趣味相通。在日本,这类小说也越来越滑向低级趣味之渊潭,故有读本小说出以纠之。因而草子小说体现的仍是一种小说创作传统——世俗性、市民化传统。
读本小说以案头阅读为主,以区别于讲述性的物语和伴有浮世绘图画的草子,故名读本。繁荣于江户时期,又分前期读本与后期读本,前期读本受中国“三言”、《剪灯新话》的影响颇大,后期读本则受《水浒传》的影响为巨。从影响源看,通俗性仍是此类小说的创作传统,但已纠正了草子小说的过分世俗而流于低俗的缺陷,而走入通俗正道,《雨月物语》等作品既模仿《新话》又模仿“三言”,就是走出低俗的例证,虽仍属通俗一途,但俗而有训。
“翻案”一词被日本人赋予了新意,它把古代日、越、朝小说与汉文小说的关系作了一词定性,而不是只适用于日本本土。它所标示的对翻案原体——中国小说所持的态度与原则在翻案成体中的指导作用,已见上述。除此以外,翻案一词在日本还关联着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即所谓翻案,是“翻”中国小说之“案”,而不是其他,所以,凡是翻案之作,皆是针对中国小说为蓝本的再创作。
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三国的传播,由传播而接受,接受是观测的平台,有接受过程,有接受方式,则“传播”才有立论之基础;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三国的影响,由影响而创作,创作是观测的平台,有汉文创作,有本土语创作,则“影响”才有立论之基础。此为总原则。
注:
①东亚包括细分之的东北亚、东南亚等国家。从文化角度言,东亚地区常以“汉文化圈”称之,而从文学角度言,越南、朝鲜、日本历史上皆曾使用汉字,进行汉文学创作,故本文认为称之为“汉字文化圈”更为合适。
②稗说体,古代朝鲜15、16世纪笔记体叙事文的一种,多以闲话、野谈方式反映社会热点,题材涉及名人秩事、野史杂记、寓言笑话等,颇具小说因素。假传体,见本篇后文。
③参见[台湾]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④参见[台湾]陈益源《王翠翘故事研究》,台湾里仁书局2001年版。
⑤[日本]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⑥参见[韩国]赵东一《韩国文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町人,即城市市民,崛起于日本江户时期(1600-1868),町人中大部分为工匠、徒工、自营商人及佣人等。参见日本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5页。
⑧ 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
⑨[韩国]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⑩韦旭升《谈朝鲜古典小说〈谢氏南征记〉》,《韦旭升文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