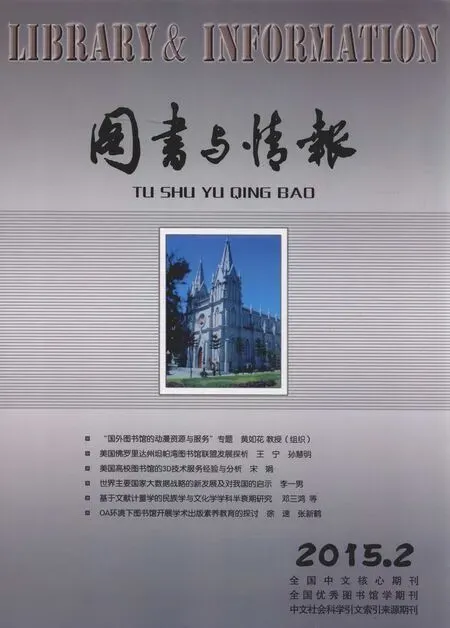研究对象的在场: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引入参与式行动研究
2015-11-14刘济群
刘济群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研究对象的在场: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引入参与式行动研究
刘济群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参与式行动研究法将研究对象纳入到了研究框架的设计过程,在参与和行动中强化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实现了研究对象的真正“在场”。参与式行动研究所蕴含的“研以致用”、“为弱势群体赋权”等特点,有助于弥合图书情报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间的鸿沟,加深学者对信息社会边缘群体的认知与理解,拓宽学科的研究领域。现有图书情报学的行动研究实践说明了二者交叉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中更大范围地应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法,还面临着研究者对方法的驾驭能力、研究对象的能力与素养以及研究资源支持等方面的限制。
图书情报学;参与式行动研究;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中,定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基于扎根理论视角建构的面向整个研究过程(从数据分析到理论框架建构)的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挖掘核心构念(Construct)与关系,并进一步发展理论时所常用的有效工具。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作为一种以定性倾向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其他类似的研究方法相比有显著区别,其侧重点在于:第一,它强调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而非只是被“外在的他者(Outsider)”研究;第二,它要求研究中形成的知识成果对所研究的社区要有可用性(Usability),并能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步骤(ActionableSteps),进而有效地支持相应的科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工作进步。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图情职业的实践者和各种类型的服务对象。上述行动研究的特点可以激发研究对象(例如,作为图情职业实践者的图书馆员,以及作为图情职业服务对象的普通读者、科研人员以及其他纸质资源或数据库系统的用户等)的主体性与创新精神,鼓励研究对象在研究问题挖掘和研究框架设计的过程中更多地“在场”,使实证研究的成果与研究情境中的工作实践能更快速、更有效地结合。因此,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在实证研究的情境下借鉴并引入参与式行动研究,有助于使研究问题更贴近于目标研究社群的信息实践本身,也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建构以及其对研究过程的情感态度,进而拓展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自身的方法论体系,提升本领域学者在跨学科交叉领域中的研究能力。
1 参与式行动研究:特征与应用
参与式行动研究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对经典实证主义(Positivism)所存在之问题的争论。与传统实证主义视角下强调感觉经验与客观调查,进而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严格对立不同,参与式行动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对象也纳入到研究设计的过程之中,从而为研究对象及其所在的社区或组织带来实际的效用与帮助。在实际的研究操作中,研究者秉承了为研究对象赋权(Empowerment)的哲学理念,关注研究对象的行为和表达而非简单地量化测度(Measurement),使研究对象的建构与行动以多种形式参与到了研究活动的范围内,进而将传统的由研究者指向研究对象的规范控制式研究情境转变为了融合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符号互动式和“共同建构”式的“参与情境”。由此可见,基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思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Partnership),而不再是单纯的、机械的“研究—被研究”(Researcher—the Researched)关系。被研究社区中的参与者可以基于其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Expertise),发挥主体性,为研究问题的发掘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提供启发。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式行动研究就被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问题的识别(Identify)会更接近于社区和研究对象在日常实践中的实际需要,而不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知识结构与主观认知所建构出的前提假设。因此,参与式行动研究相对于经典的实证主义研究更有可能弥合学术研究与社区实践之间的鸿沟,增强相应领域研究成果的生命力和应用性。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下,对参与式行动研究之特点的考察可以从“参与式”和“行动研究”两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1.1 研究对象的在场:参与式研究
参与式研究无论是作为具体的操作方法还是形而上层面的哲学理念,都与经典的实证主义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在抽象的哲学理念与方法论层面,传统的实证研究学者认为:研究者在知识搜集、研究方法实践以及理论建构方面具有独有权(Ownership)和排他性(Exclusion)特征,研究问题的挖掘、表达以及相应的研究设计都应该由具备必要知识和理论素养的研究者来完成。这种思想和理念延伸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则表现为:研究者自始至终主导着研究过程,在研究设计、理论建构以及成果描述的层面上与研究对象保持严格的分离;研究对象作为研究结果的生成方,基本只有被动的参与和特定条件刺激下的反应;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都是研究者在真正介入研究社区之前基于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主观倾向以及预存立场而预先设定的,因而在理论上就存在着与社区生活实践相脱离的风险。
与传统的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式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对社区的熟悉以及相关实践经验作为可被用于研究过程建构的重要资产。他们认为,研究者应该在与研究对象的不断互动、知识交流以及共同建构中完成研究问题确定、数据搜集以及分析方法选择等多个研究的子环节。就研究者而言,为了让研究对象实现更充分地参与,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甄选方面保持充分的民主。在参与式研究的实践中,这种态度或倾向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倾听研究对象的真实问题与需求,体会研究对象对社区生活的理解、建构与感知,从而为后期搭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其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Participation)与简单地涉入(Involvement)是有本质区别的。真正的参与式研究指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问题概念化、行动与实践以及研究嵌入个人生活世界(Life—World)等多个子过程中的共同建构、分享以及协同合作。在线性研究过程的情境中,研究对象的真实参与(Authentic Participation)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在调查的流程设置中扮演重要角色、参与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对整个研究流程以及相应研究成果的控制与利用。通过上述三方面因素的组合,参与式研究创造了一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参与的情境,传统的实证研究与知识生产的形式在这种情境下受到了冲击。与经典的实证主义研究相比,参与式研究同时具备了对话性(Dialogical)、主动性(Proactive)以及建构性(Constructivist)等不同特点,使研究对象的参与从仅限于数据搜集阶段的被动参与发展到了覆盖几乎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动、创造性的参与,研究对象也因而脱离了“特定问题表达者或描述者”这一传统的限制性角色,实现了在研究中全方位、多维度的真正“在场”。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本质就在于逐步放弃对知识生产和研究方法的垄断或绝对优势地位,改变自身与研究对象在传统研究情境中由研究指向被研究、由观察者指向被观察对象的简单映射关系,从而不断平衡二者在整个研究设计中的价值、作用与表达。
1.2 研以致用:行动研究
相对于参与式的概念而言,行动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中的历史更为悠久,相关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积累也更为丰厚。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着力于将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之中,区别于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行动研究也就由此起源。在早期探索行动研究方法的学者中,库尔特·勒文(Kurt Lewin)通常被认为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这一正式概念的最早引入者。勒文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性角度出发,将行动研究描述为一种可以将已有的或成熟的社会生活理论或法则投入实践进行检验的有效方法。基于此定义,他进一步指出:行动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流程,而是一个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过程,它包括了计划、行动以及关于研究结果的事实发现(FactFinding)等多个交替进行的步骤。在螺旋式循环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问题、研究社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单次的映射(如一次性的数据搜集:研究者通过访谈、实验或问卷抛出问题,研究对象被动地做出反应或回答),而是这些主体之间的不断互动、反复迭代以及逐步拟合。由此可见,行动研究在它的初步形成之时就已经蕴含了验证性、适用性等核心特征,其研究目的就在于:将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知识与理论放入相关的实践领域之中,以检验它的实际有效性(Practical Effectiveness)。
起源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行动研究虽然关注到了社会科学理论与专业实践之间的鸿沟并尝试用检验的方式弥合这种鸿沟,但它依然没有摆脱经典实证主义的局限。行动研究的性质(行动式、针对特定社区问题的适用性研究)决定了其不能完全适配于经典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大规模普遍化的定性研究方法,这也就引致了此种实证研究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迅速消退与边缘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解释性的研究方法论(Interpretive Methodologies)在英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行动研究才重新获得活力,并开始在一系列相关领域,尤其是教育学研究领域(如教育学理论[22]、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方法以及教育中的技术运用等)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从实证主义方法到解释性方法的核心理论视角转变,也引起了行为研究在实践主体、研究目的与研究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变化:研究者开始将研究对象也纳入到研究设计的过程中,社会性因素和研究对象的主观视角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参与式的因素也由此被实质性地纳入了行动研究的范畴;行动研究的目的不再聚焦于已有社会科学理论的验证,而是转向了实践者自身的实践理论或操作经验的验证、应用与推广;与研究目的的转变相互联系,在行动研究的情境内,面向特定研究问题、基于深度挖掘思路的质性研究逐渐取代了传统定量化研究的主导地位,螺旋式循环的研究模式的重心也转向了如何让实践者(包括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行动中验证自身的隐性(Tacit)知识或理论,进而提升这些知识或理论的适用性,实现最大效用,达到“研以致用”的目的。因此,在解释性研究方法的框架下,行动研究不再只是针对已有社会科学理论的验证行动,更是对实践者隐性知识或理论的应用与发展;行动研究不再局限于经典实证主义中研究者的绝对权威立场,而是基于研究对象在研究社区和专业实践中的知识与经验,将研究对象的观念、视角与分析思路也纳入到主动的研究架构之中,从而为行动研究和参与式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技校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中等职业学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文化课,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学好各科知识,形成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能力,以及今后的工作、生活和继续学习,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段话明确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并强调语文是技校教育的“必修的一门文化基础课”。
2 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图书情报学的交叉:意义与可行性
面向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与图书情报学之交叉的可行性评估,应该根植于对参与式行动方法的特点与图书情报学相关研究领域、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范畴之间适配性的分析。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之间的结合不应是机械的、生硬的,而应是灵活的、有机的以及相得益彰的。图书馆学与情报学都是面向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传播以及利用规律,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这与参与式行动研究所蕴含的诸多特点是不谋而合的:强调研究对象(例如图书馆员、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等)在研究中的知识贡献而不是片面的数据输出,重视研究对象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以及主观感知(例如,图书馆员在参考咨询中的感知与建构)、关注研究成果与研究社区、研究对象的有机结合(例如,如何将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成果嵌入高校图书馆服务之中)等。
基于以上对参与式行动研究法在深层哲学理念、操作步骤特点以及各主体间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分析与阐释,笔者认为,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交叉价值可以从主体间的交互、研究领域拓展以及研究成果的可能价值等方面展开分析。
(1)在主体间的交互以及研究成果的可能价值方面,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实用性特征有助于弥合图书情报学研究与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日常工作实践之间的鸿沟,在研究领域与实践领域的不断对话中为研究成果融入更多的实用价值。就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主体而言,一方面,研究者通常包含图书情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作为图情职业之反思主体的图书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等;另一方面,研究对象通常覆盖了各类信息服务的实践者和接受者,以及作为图情职业之实践主体的图书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等。传统实证主义框架下的图书馆学研究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相似,研究问题的提出、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都来源于学者的已有知识框架、预定前提假设、甚至是即时的主观情感倾向,研究问题与组织机构、目标社区的适配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相关知识储备与实践经验。这种情况往往会促发“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现象,从而使研究成果与实践问题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节,造成人力、时间、以及资金等多项研究资源的浪费。在参与式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并不提前完成研究问题设定(Problem Setting),而是身处于研究对象、专业人员以及项目参与者的旁边,作为研究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专业知识等)的提供者协助他们完成研究问题的挖掘与界定,这就为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之间的对话与交叉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在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实践的情境下,参与式行动研究可以在研究人员与馆员之间的关系博弈中定义自己的角色,并发挥作用:一方面,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指导图书馆员日常工作中的问题识别与定义,并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化、系统化的学科工具。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规范化的研究思路可以激发图书馆员的科研灵感,其专业知识素养、核心职业技能以及对图书馆职业本身的认知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基于参与式的研究思路,图书馆员作为研究对象和专业领域的实践者可以被纳入到研究问题界定、研究框架设计等多个与整体研究架构相关的核心步骤之中,他们在长期工作中积累的大量技能、经验与主观感知(如参考咨询、图书采访、文献检索以及信息编目等职业知识与技能)将为研究者提供学科领域之外的启发,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使研究者在认知目标对象、定义研究问题、设计研究过程以及建构学科理论框架等方面更贴近于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实际情境,从而能在更大程度上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较强应用性的操作步骤与方案,避免图书情报学研究与信息服务工作、图书情报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相脱节的窘境。
(2)在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参与式行动研究十分强调在研究情境中“为弱势群体赋权”的理念与行动法则,有助于增进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对信息社会底层或边缘地带的理解,丰富信息社会弱势群体研究的方法体系,延伸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参与式行动研究善于将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的话语建构、情感表达以及主动行为融入研究的各个部分,在研究情境下为弱势群体赋予更多表达的权利,从而拉近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之间的距离。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概念体系中,与弱势群体直接相关的研究范畴主要是信息贫困、数字不平等、数字化贫困等。由于缺乏对信息贫困群体的深入调研与关注,研究者凭借自身知识和直觉确定的研究框架往往与目标社区的实际状况存在差距,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界定也因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例如,长期以来在面向信息贫困与信息不平等的研究中,诸多学者都倾向于将社会经济贫困与信息贫困等同起来,直接通过主体的社会经济贫困维度定义其信息贫困状况,从而使这一研究范畴中的概念界定与研究架构都顺理成章地偏向了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范式。于良芝通过一系列的田野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贫困与信息贫困在作用机理、表现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信息贫困的归因与表现维度研究应以行为主体的“个人信息世界”为基本理论框架。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信息贫困现象,其他相关学者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深入地挖掘了情境性因素,并将信息贫困主体的主观感知与自我归因(Self-attribution)也纳入到了研究范畴与理论框架之中。在此类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介入,可以在纳入情境、主体感知等范畴的同时作进一步地拓展,将信息贫困群体的行动也加入到研究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从而为信息贫困群体的表达提供更丰富的渠道,增进他们参与研究、引领研究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通过共同行动(例如,共同完成一个信息搜索任务或阅读行为等)的方式增进与信息贫困群体之间的互动,在更为全面的框架和维度(客观特征维度、主观建构维度、行为实践维度等)中理解信息贫困现象,丰富已有的学科理论。
3 在图书情报学领域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实施步骤与经验研究实例
参与式行动研究法虽然很少在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但其在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多个子研究领域中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此研究方法在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已陆续出现,例如: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教育行动研究(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以及加拿大行动研究学刊(The Canadian Journal of Action Research)等。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传统的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方法依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应用则相对稀少。在这种情况下,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引入较为新颖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便要以分析和考察具体的实施步骤为基础。
系统规范的实施步骤是一项科学研究方法得到学界承认的重要前提,而关于参与式行动研究如何实施的争论几乎是从这一方法的诞生之日就已开始:勒文(Lewin)作为行动研究的最早引入者,将其划分为研究计划、行动、以及事实发现三个相互循环的核心步骤集合;考夫兰(Coghlan)将情境因素融入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实施过程,提出了定义情境和研究目的、计划行动方案以及采取行动三个步骤;苏斯曼(Susman)基本认同勒文等人所提出的关于参与式行动研究是由多项研究步骤的循环所构成这一观点,但他认为,行动研究应该由识别与诊断问题、设定研究目标、执行研究行动、专门化学习(Specifying Learning)以及整体评估等多个步骤构成,其中评估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和目标社区对研究成果有用性的反馈,为行动研究的终止或下一轮循环的开启提供参考。在已有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实践中,科米斯(Kemmis)对实施步骤的定义得到了相对广泛的采纳:他认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应包括计划、行动、观察以及评估或反思这四项核心步骤。这四个步骤之间的循环是螺旋式加深的,每一次循环都可能增进学者和研究对象对研究问题、核心概念以及数据资料的理解。笔者认为,这个过程类似于扎根理论研究中的从开放编码到轴心编码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每次编码的筛选与比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加深研究者对文本资料的解读,拉近概念类属与原始资料之间的距离。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参与式行动研究包含了更多的行动性和实践性因素,强调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而扎根理论则侧重于挖掘构念(Construct)并发展理论;参与式行动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在场,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囊括更多关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目标社区之间互动的内容。
在引入参与式行动研究法的少量图书情报学经验研究中,绝大多数都围绕着公共图书馆服务、高校图书馆工作以及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等图书情报领域主流研究问题展开。以信息贫困和数字不平等为核心研究范畴的信息贫困群体研究虽然亟需社会和学术界在话语表达上的赋权,但在国内外却都很少受到参与式研究项目的关注,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由此可见,考虑到方法本身所蕴含的潜力以及目前应用广度的局限性,参与式行动研究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实践机遇和极大的拓展空间。本文中,笔者分别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教育以及信息贫困研究领域中摘取了经验研究的实例,以期能相对全面地描述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领域的应用现状。
李(Ook Lee)参与建设和运营了一个由韩国政府注资的数字图书馆,并在“信息服务系统研究”(RISS)项目的经验研究中引入了参与式行动研究法。依据苏斯曼(Susman)和艾福德(Evered)所界定的行动研究实施阶段(从问题诊断到整体评估,共五个具体步骤),李按照如下步骤开展了自己的研究:首先,在问题诊断阶段,通过在线问卷调研评估用户对数字图书馆在线服务的满意程度,并在用户反馈中识别潜在的问题;进一步地,在行动计划与实施阶段,让韩国研究信息中心(KRIC)实际运营和维护数字图书馆,并进一步挖掘其中的问题所在;最后,在整体评估与专门化学习阶段,研究者评估了数字图书馆的运营绩效,并将各阶段识别出的技术漏洞、服务缺陷、以及管理失效等问题加以整理,从而在数字图书馆研究与运营领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研究方面,王(Wang)和陈(Chen)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学院开展了探索性的E-learning研究生教学计划项目,以满足在职图书馆从业人员在高校中学习图书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需求。本研究以六门E-learning课程设计为主要研究范畴,并采用了包含五个核心步骤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法开展项目研究:首先,结合课程学习者的体验与建议,确定研究的问题与焦点;其次,基于学校的学习资源和授课情境,探索可以解决问题的行动选择集(Action Options),并组织合作者、教师以及学生等群体就行动设计的方案展开讨论,以搜集贴近于网上学习实际的多方建议;进一步地,实施行动步骤:五个授课讲师基于网上学习系统开发出了六门E-learning核心课程;最后,开发出的核心课程接受了领域专家和学生的共同评估,研究者根据领域专家的建议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对课程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从而成功地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成果嵌入了实际的课程设计实践之中。
在面向我国农村信息贫困现象的经验研究中,闫慧和洪萍蟑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开展了实地调研,并借助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思路探究了当地农村居民的信息贫困状态以及他们对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使用行为。研究者根据受访居民在信息需求、ICT使用能力等方面的具体状况(问题诊断与分类),基于行动式研究的思路选取了符合信息贫困标准、较为典型的15人,在当地的网吧开展了电脑操作技能的基础培训(行动计划与实施)。在培训结束后,研究人员对培训对象进行了关于培训实验的效果访谈(评估与反馈),并总结了农村信息贫困群体所急需的电脑操作技能,旨在为后续可能开展的农村地区大规模电脑培训提供有价值的经验(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与拓展)。
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核心优势就在于有效地把握了目标组织或群体中丰富的互动性因素。在前文所述的数字图书馆运营研究和E-learning课程设计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组织起来,通过统一化的研究问题充分激发了他们的互动、交流与讨论;进一步地,研究者还将自身也融入到了组织实践的情境之中(例如数字图书馆维护、图书馆学在线课程学习试验等),增进了学术研究与专业实践之间的直接对话,显著地提高了后续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可操作性。与前两例有所不同,面向信息贫困群体的经验研究虽然借鉴了参与式研究的思路,但只是将其作为田野调查中数据搜集阶段的补充,而非核心的研究过程;以电脑培训为核心的行动研究虽然增进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但行动研究的内容和操作还是由研究者完全主导,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居民在研究情境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在场”。
4 图书情报学领域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挑战
本文从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参与和行动两方面的价值出发,探讨了该方法与图书情报学领域相交叉的可行性和可能贡献,并在已有的经验研究分析中阐释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一般实施步骤,指出了该方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仍存在着较大的应用空间。考虑到参与式行动研究目前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应用领域有限、实例稀少的现状,再结合方法自身的特点与要求,笔者认为,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领域引入该方法可能面临着一系列的限制与挑战。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研究情境中主体之间的充分互动。因此,应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挑战则可以从各个行动主体的角度展开分析。
就图书情报学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对研究过程的适度引导与把握是其核心职能所在,这个适度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研究者应该像田野调查中的人类学家一样,保持对社区环境、人际关系以及话语建构的敏感性,以免忽视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研究问题。在访谈与讨论中,研究者应该密切关注和记录观点的动向,捕捉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与主观感知,并将其与社区或组织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联系;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要保持对研究对象、社区环境的开放性,努力适应研究实践中的生活与发现给自身已有价值体系、知识结构带来的冲击,防止自己因缺乏安全感(Insecurity)和控制力而退回传统实证主义研究中研究者霸权的舒适定位,使研究对象和目标社区重新归入“失语”的状态。
就研究对象的角度而言,并非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具有参与行动研究的基本能力与积极性。这个问题在面向信息贫困群体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访谈过程中,部分受访者持续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回答问题十分简短且拒绝做解释,在小组讨论中也很少发言;在问卷调研中,部分受访者因为不识字、文字理解能力有限等原因,在解读问卷题目和答案时存在着不小的障碍。研究对象充分地参与互动、并在行动中贡献自己的知识与实践经验,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当研究对象在研究中的参与、行动能力有限时,研究者则更需要保持耐心,提供更多知识解读和操作技巧上的帮助,引导研究对象更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问题,并协助他们参与到行动研究的项目之中。
就研究环境与资源的角度而言,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运用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在陌生环境中开展行动研究,需要研究者同时保持开放与批判的态度,而不是谨慎地躲在预设问题与结构化研究设计的“保护”之下。在这种态度或思路的指引之下,研究者就需要持续的、长时间的研究资源支持(例如研究场域的持续开放、合作者与研究团队的长期运作等),以在富有挑战性的研究情境中开展参与式研究项目,将时间与资料的积累转化为研究的深度与价值,得出富有创造性且切实可行的研究成果。例如,在李(Lee)参与的数字图书馆项目中,政府的大量注资、韩国研究信息中心(KRIC)的长期运作以及数字图书馆本身提供的技术支持,都为该项参与式行动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并积累出数字图书馆运营维护经验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保障。笔者很认同这种类似于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式的长期跟踪与深度参与的思路,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资源支持图书情报学的参与式行动研究,鼓励研究者减少短期的、急促的、以及碎片化的研究尝试,将更冷静、更有持续性的分析与思考嵌入到目标社区或组织的实际问题之中(例如:中国农村的信息贫困现象,民间图书馆的定位与贡献等),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领域贡献更扎实、更有说服力、且更具备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1]Berg B L,Lune H.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Boston,MA:Pearson,2004:7-9.
[2]Wildemuth B M.Applic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to questions i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M].Santa Barbara,CA:Libraries Unilimited,2009:308-310.
[3]邱五芳.中国图书馆学应进一步弘场实证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1):16-21.
[4]Charmaz K.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M].Sage Publications Ltdci edition,2006.
[5]Whyte W F E.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M].New York:Sage Publications,1991:19-55.
[6]Baum F,MacDougall C,Smith D.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J].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2006,60(10):854.
[7]洪星,邓喜清.行动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研究的新范式[J].图书情报工作,2008,52(10):29-32.
[8]Susman G I,Evered R D.An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merits of action research[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8:582-603.
[9]Borda O F.Participatory(action)research in social theory:Origins and challenges[J].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2001:27-37.
[10]Rappaport J.Community psychology:Values,research,and action[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7:115-131.
[11]Kidd S A,Kral M J.Practic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5,52(2):187.
[12]McTaggart R.Principles for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J].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1991,41(3):168-187.
[13]Reason P,BradburyH.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M].Thousand Oaks,CA:Sage,2001:1-15.
[14]Bryant C G A.Posi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research[M].London,UK:Macmillan,1985:37-65.
[15]Tolman D L,Brydon-Miller M E.From subjects to subjectivities:A handbook of interpretive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s[M].New York:New YorkUniversity Press,2001:238-256.
[16]Tandon R.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articipatory research[J].Converge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1988(21):5-18.
[17]Cornwall A,Jewkes R.What is participatory research?[J].Social science&medicine,1995,41(12):1667-1676.
[18]Wallace M.A historical review of action research: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in their managerial role[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1987,13(2):97-115.
[19]Lewin K.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46,2(4):34-46.
[20]Carr W.Philosophy,methodology and action research[J].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2006,40(4):421-435.
[21]Sanford N.Whatever happened to action research?[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0,26(4):3-23.
[22]Elliott J.Educational theory,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action research[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1987,35(2):149-169.
[23]Zuber-Skerritt O.Action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examples and reflections[M].London,UK:Kogan Page Limited,1992:17-51.
[24]Groves M M,Zemel P C.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An action research case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Media,2000,27(1):57-65.
[25]Kemmis,S.Educational research,methodology,and measurement: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M].Oxford,UK:Pergamon Press,1988:15-43.
[26]Glanz J.Action research:An educational leader's guide to school improvement[M].Norwood,MA:Christopher-Gordon Publishers,2003:13-23.
[27]吴慰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开拓前进——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5):3-6.
[28]蒋永福.人文图书馆学论纲[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4):9-13.
[29]Hjφrland B.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practice,theory,and philosophical basis[J].Information Processing&Management,2000,36(3):501-531.
[30]丛敬军.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及对策[J].图书情报工作,2001(3):89-91.
[31]Fine M,Torre M E.Intimate detail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prison[J].Action Research,2006,4(3):253-269.
[32]Chatman E A.Life in a small world:Applicability of gratification theory to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1,42(6):438-449.
[33]Chatman E A.The impoverished life-world of outsiders[J].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6,47(3):193-206.
[34]Yu L Z.How poor informationally are the information poor?Evidence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of daily and regular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individual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6):906-933.
[35]于良芝.“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1):4-12.
[36]闫慧,闫希敏.农民数字化贫困自我归因分析及启示:来自皖甘津的田野调查[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68-81.
[37]Coghlan D,Brannick T.Doing action research in your own organization[M].Thousand Oaks,CA:Sage,2014:27-59.
[38]Susman G I,Evered R D.An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merits of action research[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8,23(4):582-603.
[39]钟丽萍.行动研究法——促进图书情报专业实践与研究的融合[J].情报资料工作,2011,32(2):19-22.
[40]Kemmis S.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public sphere[J].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2006,14(4):459-476.
[41]Lee O.An action research report on the Korean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J].Information&Management,2002,39(4):255-260.
[42]Wang M L,Chen C L.Action research into E-learn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aiwan[EB/OL].[2015-01-02].http://www. slis.tsukuba.ac.jp/a-liep2009/proceedings/Papers/a16. pdf.
[43]闫慧,洪萍蟑.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数字化脱贫的影响[J].情报资料工作,2014,35(3):89-93.
[44]Kock N F.The effects of asynchronous groupware on business process improvement[D].University of Waikato,1997.
[45]Rabinow P.Beyond ethnography:anthropology as nominalism[J].Cultural Anthropology,1988,3(4):355-364.
[46]Rahman M A.People's self-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A journey through experience[M].London,UK:Zed,1993:115-134.
[47]Smith S E,Willms D G,Johnson N A.Nurtured by knowledge:learning to do participatory action-research[M].New York:Apex Press,1997:32-58.
The Presence of Research Subjects:Employ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tudie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incorporates research subject into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design,which can augm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earch subject and researcher,and realize the authentic"presence"of research subject. The attributes of PAR,such as"study for application"and"empower the disadvantaged",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down the divide between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enhance scholars'understanding of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in information society,and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Previous PARs employed in LIS research have demonstrated the valid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is particular method,and the factors which include the researchers'ability and skills in employing PAR,research subjects'capability to engaging in the action research,and the valuable resources for supporting PAR,seem to be the extrusive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expanding of PAR application in LIS researc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empirical study
G250
A
10.11968/tsygb.1003-6938.2015047
刘济群,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2015-03-16;责任编辑:刘全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