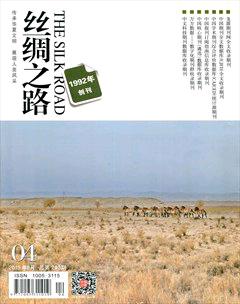试论武威在中国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及其贡献
2015-11-05宋立彬
宋立彬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汉辟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后,武威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姑臧(今凉州区)一直作为武威郡的治所。从汉至隋唐,历代王朝在这里或设郡置府,或建立国都,致力经营,使它成为长安以西的大都会、中西交通的咽喉、丝绸之路的重镇民族文化交融的熔炉。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逐步传入中国。汉代以后,中外僧人来往日益频繁。他们为了“法流东土,泽及众生”,不惜逾越沙险,涉渡流波,为中国带来佛教文化。威武地处中西交通要津的甘肃河西走廊东端,一度高僧云集,开坛说法,卓锡译经,佛学盛行,在我国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武威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第二故乡”
佛教从公元前6世纪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诞生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在我国西北龟兹、于阗等地已有了传播的迹象。佛教何时传入中原内地,历来说法不一,笼统地讲,佛教入华当在汉通西域之后(约在公元纪年前后)。张骞出使西域,“始闻浮图之教”。后汉明帝夜梦金人,“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楚王英首皈佛教,“楚王刘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至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那就更晚了。据史书记载,约在2世纪末,佛教开始在凉州民间传播,而且也影响了一批致力于经学的名人儒士,如凉州经学大师马融开始研究佛教,他不但支持僧人翻译佛经,而且在学馆内讲说佛法。
佛教传入武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5)《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记载:“自周至晋,千有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纪,张轨称制凉……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自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就其地建塔……巍巍宝塔,肇基阿育。”清康熙二十一年(1681)立的《重修白塔寺碑记》记载:“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甘州之万寿塔与凉州之姑洗塔居其二焉。”唐天宝元年(742)《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记载,凉州有白马寺,据推断,凉州白马寺应早于洛阳白马寺。以上诸多记载反映了武威早期佛教的一些情况。
中原佛教转盛之际,武威佛教亦趋兴旺,与中原佛教相比,亦属较早较盛之列,这是由武威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武威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是古代西北各族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散地,西方传教士由陆路入华,首先到达武威。因此,这里较早接触了佛教,在安定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其次,河西地区是“华戎所交”的重要地方,域外僧人进入中原之前,在这里学习汉语,熟悉民风,西行僧人也在这里打点粮秣,熟悉西域语言。于是中外僧人在此直接交流,使武威佛教文化发展获得良好条件。再次,武威地区有较强的汉晋文化传统,当佛教传入时,这里的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一种信仰形式。此外,少数民族容易接受佛教,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武威是西戎(羌族的祖先)部落的驻牧之地,秦汉时期,被月氏所占据,之后,北方匈奴逐渐强大起来,赶走月氏,统治了凉州及整个河西走廊。武威是匈奴、氐、鲜卑、羌等族居住的地方,这些少数民族不仅容易接受佛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儒教统治产生了一种抵制。而后,汉族统治者逐渐明白利用佛教可以帮助和维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所以佛教较早地得以在武威顺利发展。多识教授曾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站:第一站是中国境内的高昌、龟兹、于阗等国,第二站便是凉州。他说:“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古凉州,在中原和西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曾经起到过交通枢纽和货运中转站的作用。从西域传来的佛教从河西走廊凉州,二次辐射到了中原各地。因此,河西走廊凉州可以称作佛教的第二故乡。”
二、武威是十六国时期中国西北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
西晋建立不久,王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相互攻打,史称“八王之乱”。地方势力和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反晋,形成了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这一时期,五胡内迁,内地呈现一片混乱,河西地区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政权控制,史称“五凉”。除西凉之外,其余渚凉均曾建都于姑臧(今凉州区)。这一时期,佛教事业发达,各政权统治者又崇信佛教,凉州成为我国西北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
前凉政权代踞凉州,自张轨永宁元年至张天锡咸安六年(301~376),凡九主,计76年,非常重视佛教事业。《开元释教录·总录》卷4记载:“外国优婆塞一人,译经四部六卷,见存一部,亡三部。优婆塞支施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癸酉,以凉州内正厅后湛露轩下,出须赖经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常慧、释进行同在会证。”《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轨后,世信佛教。”张天锡还舍宫建塔修寺。唐景云二年(711)《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记载:“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本名宏藏寺,后改置大云。”宏藏寺“花楼院有七级木浮图,即张氏建寺之日造,高一百八十尺,层列周围二十八间,面列四户八窗,一一相似。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敞……”可见当时前凉信奉佛教的盛况。不仅如此,当时在凉州佛经写译成就也不小,晋咸安二年(372),在凉州的沙门慧常写出《关赞》、《渐备》、《须赖》、《首楞严》四经,送给襄阳的释道安,释道安所撰经录中专门列有《凉土异经录》,有59部79卷之多,可见凉州译经既早又多。
前凉以后,武威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不仅表现在石窟开凿、寺塔兴建,而且还表现在许多著名高僧在这里长期停留、开坛讲经、翻译著述等方面。河西一带遗存至今的石窟不下数十处,其中一部分就是北凉时期开凿的,如凉州区东南40公里处的天梯山石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北凉沮渠蒙逊“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法苑珠林》卷14亦载,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于州南百里开凿石窟,规模宏大,千变万化,警弦心目”,说明当时天梯山石窟开凿的规模。据明正统十三年(1448)刘永城《重修凉州广善寺铭》可知,天梯山石窟在明代还有窟龛26个,但因地质不佳,后经地震,崩塌不少。20世纪50年代修水库搬迁时,仅存13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还载:“凉州石窟瑞象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其最久盛。专崇佛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室,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又载:“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释迦方志·通局编》也载:“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现存。有塑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其旁侧足迹纳尔,斯徒众矣,不可具云。”上述关于北凉石窟的记载,足以说明当时佛教的盛况。姑臧为北凉都城,今武威周围还应有不少北凉石窟遗存,但是只见于文献记载而未发现遗址。除此之外,在现存河西的石窟中,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金塔寺石窟都有北凉开凿的早期洞窟。
寺塔的兴造也不少。《魏书·释老志》载:“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寺,盖其遗迹焉。”姑臧阿育寺,还有现存的凉州大云寺、尹台寺、罗什寺、安国寺等,都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寺院。《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记载,423年,僧人昙摩密从龟兹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榛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净。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可以看出当时武威等地的佛寺规模。
佛教文化的传播不仅表现在石窟的开凿或寺院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对佛经的翻译和著述。从敦煌出土的许多写经可以看到,有些经卷上标明写经地点就在凉州。最早在西域和河西等地译经的是魏晋之际的河西名僧竺法护(231~308),他一生所译佛经有159部之多,是佛教入华以来译经最多的一位名僧。晋“永嘉之乱”后,他携带所译诸经避居凉土,专门从事佛经翻译,为佛教在中西国的传播、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凉时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344~413)。鸠摩罗什在龟兹时,前秦苻坚已然素闻其名,乃遣骁将吕光率师7万西伐龟兹,而敦请鸠摩罗什入中原。东晋太元十年(385),鸠摩罗什随吕光旋师回京,吕光闻苻坚“淝水之战”遭到溃败,被部将姚苌所杀,便不再东进,在姑臧称王,建立后凉,建元太安。此后,鸠摩罗什滞留凉州17年,研习佛学,学习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秦时期,他在长安翻译佛经70余部、384卷,成为我国历史上三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佛教史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公元397年,段业建立北凉,400年李暠建西凉。沮渠蒙逊先据张掖,412年据姑臧,乃迁都姑臧。421年,蒙逊灭西凉,完全控制河西。北凉控制范围较大,社会稳定繁荣,统治者崇尚佛教。因此,北凉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凉佛教主要表现在对佛经的宣译上。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人,其中最负盛名的为昙无谶。沮渠蒙逊定鼎河西,昙无谶遂于玄始(412~428)中到达北凉都城姑臧,在此学习汉语三年。“河西王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以后他与河西沙门惠嵩、道朗等合作,相继译出《大般涅槃经》36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云经》4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优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1卷。昙无谶在姑臧所译的经卷影响颇大,《法苑珠林》载:“沙门讲道,驰往敦煌,躬自接受,凉州道朗,西土之望,感有瑞梦,亦屈年从进受戒,于是受者有三千人。”沮渠牧键是一位信奉佛教的君王,对译经非常重视,在译《大毗婆沙经》时,邀请本地300多名僧人通力合作,用了15年时间译完这部长达1万卷的巨经。后沮渠兴国又组织500多人翻译《优婆塞戒经》,规模空前宏大。像北凉这样译经者颇多、统治者又重视的现象,在十六国时期是绝无仅有的。
三、武威在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地位及巨大贡献
武威作为历史上西北军事、经济、政治的重心,是西方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东传的必径之路,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中原相对隔绝,也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崇奉提倡,佛教首先在这里留驻兴发,然后开始了它中国化的进程。佛教流寓敦煌,月氏人竺法护能“口敷晋言”,自译佛书,被称为“敦煌菩萨”,说明外来的佛教在这里已经生根。苻坚命吕光西征龟兹迎回的鸠摩罗什,因前秦败亡而停留凉州17年,期间他精习汉语,后来在长安译经时,译文“文美义足”,适合汉人诵习研讨,扩大了佛教在中原的影响,促进了佛教的广泛流传,从而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439年,北魏灭北凉,“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并且“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其中包括数千僧侣,从此“沙门佛事皆俱东”,魏文成帝时,相继任僧统的师贤和昙曜皆为凉州高僧。迁都洛阳之前,在平城活动着很多凉州僧人,如太武帝灭佛前曾隐居麦积山的著名禅师玄高被迎至平城,聘为太子拓跋晃师。值得一提的是,昙曜在平城西武州塞主持修造了现存云岗石窟最早的一批石窟,北魏灭北凉后迁徙去平城的凉州居民,多为达家士族和能工巧匠,为北魏开凿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提供了技术力量。宿白先生在《云岗石窟分期试论》中说,这一时期石窟“从窟的安排到各种形象及其细部的雕刻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决不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一组石窟及其造像和各种特点,看作是前一期特征的延长”。这里所说的“前一期”应包括北凉灭亡以前凉州地区的石窟兴造,如果是这样的话,云岗石窟源于凉州也是很清楚的。北魏时期凉州僧人进入中原,直接推动了中原佛教的发展,凉州僧人还多出入于北魏权门之间,从上层对北魏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
《高僧传·译经篇后论》曰:“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译经对于佛教传播的作用很大。武威地区民族众多,语言交流较为方便,以语言特长为传译做出贡献是对中原佛教积极作用的又一种表现。北凉时译经甚多,所译经典之中,有《大般涅槃经》、《菩萨戒本》、《大毗婆沙经》等,先后流入中原内地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为凉土所出经典之最重要者,也是4~5世纪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所译大乘《涅槃》,是大乘中观宗重要的典籍,乃中国所谓涅槃宗之根本经典。《大般涅槃经》阐发“一阐提”(缺乏信心者)皆得成佛的学说,认为一切人皆有佛性,开中国大乘佛教之一派,重要之极。据《释迦方志·教相篇》载:昙无谶持《涅槃》原本至凉土后,“盗者夜窃,举而不超,稽首谢焉”。说明当说《涅槃》已引起僧俗的高度重视。《出三藏记集》曰:“《大般涅槃经》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凉土此经,在中国佛教文化传播之中意义非同小可。
另外,由于河西地区相对安定,使许多早期珍贵的佛典得以保存,这也是对我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东晋高僧释道安说法护的《光赞般若经》“寝逸凉土九十一年,几至泯灭”。3~4世纪,北方战乱,兵革不息,唯凉州安定,保全了重要经典。我国的早期写经,遗存至今者为数不多,择举最早者,只有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前凉升平十二年(368)《法句经》、上海博物馆保存的后凉麟嘉五年(393)《维摩经》、安徽博物馆收藏的北凉神玺三年(399)《贤劫千佛品经》、北京图书馆保存的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律藏初分第三》等。这些较早而又宝贵的写经,均出于凉州,既可说明当时凉州佛教相对于中原地区较为发达,又可说明凉州保全早期写经对我国佛教发展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