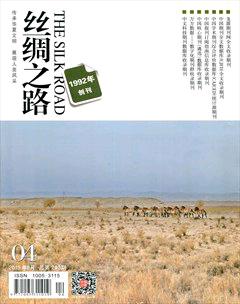魔幻世界或者更多
——解读《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2015-11-05谭金柳
谭金柳
魔幻世界或者更多
——解读《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谭金柳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 445000)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通过创造魔幻人物、魔幻动物、魔幻植物等魔幻意象、魔幻意境,营造时间叠置的叙事环境,为读者构建了一个魔幻世界,并且由此传达出作者对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人性的深层思考。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魔幻世界;时间叠置
为什么他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冯玉雷先生深深地热爱着他脚下这片土地,多年来,他用手中的笔创作了《敦煌百年祭》、《敦煌遗书》、《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等反映敦煌文化的小说,表达着他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以及他对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人性的深层思考。其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目前学界关于该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该书的叙事特点,即以散点透视为结构特征的多元叙事视角,及以此为基础的叙事逻辑的非逻辑化,并且二者共同促成了叙事结构的散文化,加之象征性表达手法、戏仿、解构式的叙事策略等现代主义艺术的运用,形成了“叙事的迷宫”;二是该书的思想性,即通过刻画形形色色人物的百态生活与心灵状态,及由此爆发的精神力量,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性、世界性和人类性等普遍性思想关切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美学意义,可谓“心灵的交响”;三是关于诗意化和性灵化语言的研究;四是“知人论世”式的作家本人研究。
笔者认为,该书以西方探险者(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掠夺者)在中亚的探险考古活动为历史背景,为读者构建了一个魔幻世界——这里有变幻莫测的布隆吉、雅丹地貌、苏巴什古城、魔鬼城等异域风光;也有关于罗布泊、昆仑山、祁连山、鸣沙山、月牙泉、悬泉、楼兰国、黑水国、圣树的传说故事,道爷鬼冲气的巫术习俗、魂归灵坛的仪式,以及富有生命力的地域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等;还有普尔热、赫定、梵歌、马继业、阿克亨、唐古特、香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六千大地上的百态生活……一切都具有魔幻性,一切都让人震撼,当我们穿梭于这个魔幻世界,并为之动容的时候,不禁要思考作者是如何营造这个魔幻世界的。一方面,他利用一系列神秘意象来构建这个魔幻世界;另一方面,他采用叠置时空的方法,营造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呈现的叙事环境。
一、神秘意象
在作者笔下,泥人讲着古经,风患上了高血压,死去的人、楼兰的衣服、麻雀、鸵鸟、旋风、空气与荒地都可以说话,濒临死亡的杰恩可以被死人救活,盐碱滩还可以出庭作证,骆驼和胡杨甚至可以充当翻译,梵歌与香音、唐古特与楼兰相距千里甚至处在不同时空却可以在草原上相遇。东方多次出现佛光的情景,赫定在梦里与楼兰相会的场景,山神欢迎赫定的情景,甚至男人生子的情景,如此多的魔幻情景不可计数。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大体将这些神秘的意象分为魔幻人物、魔幻动物、魔幻植物。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作者为我们刻画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骆驼客这一群体,誓死守卫象牙佛的吴根栋道长、马荣贵道长和郭元亨等人,普尔热、赫定、梵歌等执着于理想的考古探险家,五十年如一日向游客送出那一篮土豆的易喇嘛,马继业、阿克亨、唐古特、香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是六千世界活的灵魂,这些人中有些具有魔幻性。
楼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既是现实生活中罗布泊少女楼兰,又是历史中的楼兰,她忽而是现实生活中昆其康伯克的女儿、奥得的初恋情人、唐古特的老婆、西海和忍冬的母亲,忽而又是沉睡千年却指引赫定走出险境的楼兰女王。作者巧妙地将二者叠加交糅在一起,亦真亦幻,让人眼花缭乱,分不清现实与梦幻、现时与过去,她就这样穿越时空微笑着活在历史中、活在现实中,活在赫定的灵魂里。
香音这一活在历史中也活在现实中的美丽女子,也是这样一位具有魔幻性的人物。她是最美丽的女子,她不染铅华的美丽足以迷倒放荡不羁的杨恕昌,足以使漂泊无依的梵歌找到心灵的归属;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女子的苦难:“中国汉族女人一生苦难深沉,其实草原上的女人更是多灾多难,文成公主、王昭君、蔡文姬是宫廷女子,命好,有文人给她们写文章,写诗,唱戏,而我们的苦难只有六千世界才知道。”聪慧如她却依然纯净如初;她生为王爷的女儿,本该丰衣足食享尽荣华,但却遭遇家庭变故,几经波折,最后死于非命。死去的她常常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作品中,用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如此美好的女子却命途多舛,那么美好却那么凄婉。
另外,丹宾几次死去几次投胎的奇幻经历,罗布奶娘摘下两只耳朵送到糜田里的情节,泥人昆仑舵主几乎洞悉一切世态变化的智慧,这些无不具有魔幻性。
在这片土地上,天地万物、有生有灵的一切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生存着。不单人具有魔幻性,物也是如此。被夸大了的动物语言、行为形成了一个神秘奇幻的动物意象系统,也增加了这个世界的魔幻性。
湖上牦牛用身体奋力展演,它不断变奏音乐,不停呼喊“人文关怀”,以此刺激、惊醒麻木的人群;骆驼也疾呼“人文关怀”,它驮载着永恒的“人文关怀”;小美羊发出“我是自由的羊,才不像沽名钓誉的人类”的呼喊……这些既具有象征性又具有神秘性的叙述融入了作者对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人性的思考。
除了动物,植物也在这个魔幻世界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糜子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植物意象,也是作者重点描述的对象。书中《在揉搓中呻吟》一节,作者以糜子的口吻讲述了蒲昌揉搓糜子的过程,其间还融入了传说化的关于糜子的种植历史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以及六千大地上流传的故事和人们的百态生活。这些糜子是六千大地生命的种子,为这片土地注入生机、注入活力。生命力顽强的胡杨树则是罗布泊饱经沧桑的纪念碑,它忽而幻化成宫殿,忽而幻化成人形。当爱情、梦想消逝,胡杨却毅然慷慨悲壮地在荒凉、酷暑、严寒中坚守永恒不变的信仰。
书中还有佛法显灵的神奇场景:“雇工抡起刀,正要砍,忽然,洞窟充满亮光,中央端坐一位胖大和尚,鼻大如斗,两耳垂肩,无声地微笑……和尚又变成一个夜叉,夜叉又生出千眼,每个眼睛都发出威严的光芒。接着,又生出千只手,手里拿着宝物、兵器、经卷、佛像、狮子、老虎、蟒蛇……”还有反反复复出现的那首带有神谕性质的诗歌:“我是那洁白的莲花/在光辉中诞生/被神的呼吸所饲养/升起/进入了光辉/从污秽与黑暗中/我在六千世界开放……”这些也能体现出这个世界的魔幻性。
二、时间叠置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认为历史上有三种社会形式,或者有三个历史时刻,即传统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这原本是历时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主要是前两个阶段)却以共时状态在六千大地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同时奏鸣,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恰恰是这种共时状态强化了这个世界的魔幻性。
在传统社会,个体行为受其他人影响,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这样做,因此,人的行为由传统引导,若你的行为与社会格格不入,你就会感到羞耻,同时也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斥,整个社会呈现的是“羞耻文化”。《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以骆驼客群体为代表的六千大地上人们的心理状态正是处于传统社会阶段,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由传统引导。
散布在六千大地上的骆驼客真诚勇敢、吃苦耐劳、重义轻利,他们为信仰而存在,视信誉为生命,忠于自己的雇主;骆驼客一生、几百年、几千年来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在路上行走,跋涉在荒凉严酷的环境中,随时都面临死亡的考验,有的甚至出去以后再也回不了家;他们用生命和灵魂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他们卑微而悲壮的生命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之所以能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克服利益诱惑与重重困难像神经一样把六千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受传统引导,即祖祖辈辈都这样以对祖先、对历史、对家园、对信仰的责任和虔诚守护着这块大地,所以生来是骆驼客就注定要断奶,注定要循着先人的路漂泊一生,否则就会遭到排斥,而这一群体的叛逆者如丹宾、羊蛋以及后来的阿克亨都是遭到其群体排斥的。
另外,王圆箓的行为也受传统引导。就像他自己所说:“我是人,但多年来像鬼一样生存。”无论他的形象多么猥琐,他的行为多么让人心生憎恨,潜在支配他行为的正是传统,他卑微的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娶个漂亮的老婆,有个一官半职,而这正是传统社会一贯的人生道路。罗布奶娘的行为也是由传统引导的,除却她身上的魔幻色彩,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渴望与家人团聚的传统母亲。为此,她甚至不惜自孩子出生起,就试图阻止他们成为骆驼客,最终为远行的孩子们哭瞎了双眼。
而这些人的状态正是六千大地上人们生存现状的缩影,扩大到整个社会则是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社会的写照,当时中国还处于传统社会,整个社会都是受传统引导的。
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新目的和新动力促使实业家不停地赚钱,开创新的企业来赚钱,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无需求助于任何人的同意,也即人的行为受“内在引导”。非商业界人士也同样具有这种精神——追求成功,成功是个人得以拯救的外在标志,失败则意味着整个生命都一钱不值,并有深深的负罪感,社会呈现的是一种负罪文化(从内部对个人的惩罚)。书中西方探险者正是受内在引导,才会不断追求成功。
俄国军人普尔热身上有种近乎狂热的精神,他野心勃勃,执着于事业,为了理想(为俄国侵略中国开辟路线,从而赢得无上荣誉)牺牲了健康,放弃了幸福,最终倒在了探险的路上。另一位和六千大地结下一生之缘的赫定有着厄尔布尔山一样坚韧不拔的意志,他顽强拼搏、孤独倔强、永不服输,为了真理牺牲了一切。可以说赫定才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发现者,但命运捉弄,他没有及时发现敦煌藏经洞,使它遭受劫难。日本僧人河口则追求佛理,他响应六千世界神圣的召唤,克服千难万险去朝拜神圣的佛国圣地。梵歌起初也是一位醉心于探古寻宝的探险者。斯坦因、荣赫鹏、格威等人也受内在引导,追求自我的成功,为了成功甚至不择手段,而由此爆发出来的力量则是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所不能比拟的。
传统社会与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在六千大地上的相逢势必会引起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格威和马继业的谈话中可见一斑:“有时候,我真不敢面对这种伟大胸怀。在沙漠边缘一些村子里,我们刚到达,村里人全都出来欢迎,并且已经做好饭等着……后来才知道,他们看见沙漠里出现一个黑点,判断出有客人要来,就互相告知,并准备招待客人……而我们却只把他们高贵的善良当作无知愚昧。”
梵歌也表达了这种感受:“西方世界的文明让人感到很压抑,让人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家,灵魂永远处于飘摇状态,所以,我宁肯长年累月浸泡在沙漠和古城的荒凉中寻找真实,让西伯利亚的刺骨寒风告诉身体,我的神经还发生着作用,我的血肉之躯还存在着。现在,我遇到香音我有了回家的感觉,所以,其他任何东西,甚至王位,对我来说都多余。”六千大地的淳朴使他有了家的感觉,找到了心灵的归属。
作品中的辜鸿铭说过这样一段话:“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1899、1900两年,中国确实不平凡,发现鲍尔文书、楼兰古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可以说,1900年是清朝政府最黑暗的时候,而在文化上却爆发出奇异的光彩。古代文明给衰落的中国打了一支强心针,使这个民族重新获得生机。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架巨大机器,人性被完全异化,所以,我宁可沉醉在古典文化里。”这段文字可谓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他渴望一种人文精神的重建,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身上。
作者独具匠心的时间设置不仅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而且模糊了时间界限,为构建魔幻世界创设了亦真亦幻的叙事环境。
三、结语
作者为我们呈现的仅仅是这样一个魔幻世界吗?显然不是。当我们融入这个魔幻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被这个魔幻世界震撼了,同时也获得了无限的精神力量——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力量。书中充满灵性的灵台不仅是六千大地的灵台,而且是人类心灵的故乡,而今,全人类都面临着生存困境,我们感到精神迷惘、内心恐惧。简言之,人类失掉了根。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人类的孤独、恐惧和苦痛?我们的灵魂应该寻找一个怎样安谧和谐诗意的精神家园?
“文化寻根”无疑是找回人类文化信仰之根的办法,也是今天“新神话主义”写作的一致趋向——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对原始淳朴的破坏,呼唤神圣感的复归,用人类学写作寻找人类失掉的根,用文艺作品给当代人疲惫的心灵以慰藉,帮助当代人找回那个失落的信仰世界,回归心灵的家园。冯玉雷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他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找回失落的信仰,为信仰而活,给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家。也许只有复归到这种最真实、最简单、最朴素的环境里,我们才能洞见人性中最初的淳朴与善良,才能找到自己,找到信仰。
[注释]
①冯玉雷:《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所引原文皆出此本。
②赵录旺:《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的新实践——冯玉雷小说书写艺术的一种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③〔美〕大卫·理斯曼著、王崑译《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I207.42
A
1005-3115(2015)04-0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