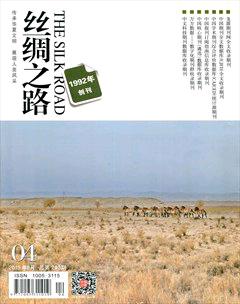铁穆尔:尧熬尔的灵魂歌者
2015-11-05杨旭
杨旭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星空下的乌拉金》①堪称裕固族史诗般的著作。铁穆尔是一名地道的尧熬尔牧人,儿时草原牧民的生活经历是他创作的全部灵感和素材,他走遍亚欧大草原,亲眼目睹、感受了现代化铁蹄下牧民生活的异常艰辛,本民族的生存日益艰难,同时在社会化大熔炉中众小民族的存亡更是在夹缝中残喘。作者将这些感受和牧民以往的生活状态全部汇聚于《星空下的乌拉金》中,并从生态发展、古老与文明、众小民族存亡的高度展现了草原上的裕固族在现代社会中的漫漫长路。
一、文化寻根精神
铁穆尔作为一名尧熬尔人,从小骨子里流淌的是牧人不羁而又伤感的血液,淳朴天真、善良勇敢又敢于牺牲的精神是尧熬尔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尧熬尔的历史后,感受到的是这些牧人内心一种近乎绝望但又荡气回肠、生生不息的复杂情怀。尧熬尔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几千年的历史不说,这半个世纪的、一百年的、整个民族的不说,就这一个部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人的命运,已够我辈思考几辈子”。②裕固人自称尧熬尔,在历史、文化和民俗方面,尧熬尔人都是典型的逃亡者和异乡人。在尧熬尔人理解和领会的民族意识里,他们曾是亚欧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牧人,公元13世纪蒙古统治时代进行政治改组,形成了今天的尧熬尔。他们是古代一系列战争中失败了的英雄们的后裔,他们从阿尔金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一路流浪、逃亡,最终祁连山收留了他们,古老的尧熬尔人就在祁连山下洗涤岁月留下的伤疤,但是他们仍然操着古老的蒙古语和突厥语,在这里繁衍生息。
多少年来,这些牧民无时不刻不在想念着北方,正如“游牧人的神在北方,游牧人的魂在北方”。(《北望阿尔泰》)阿尔泰山脉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腹地,但是茫茫阿尔泰只能无数次出现在尧熬尔人的梦里了,“我魂牵梦绕的阿尔泰杭盖,是如此强烈的吸引着我,令我无限神往”。(《北望阿尔泰》)多难的尧熬尔人本以为栖息在祁连山下就可以安稳度日,不再颠沛流离,但是上世纪50年代,游牧在腾格里大坂南路腹地的尧熬尔鄂金尼部落经历了大规模的强行搬迁,他们离开了鄂金尼故土,往后的岁月更是生活在浓烈无比的乡愁中。历史就这样强行让无辜的尧熬尔人只身来到一片陌生的地方,而几十年后当作者再次踏上曾经的友爱草原时,已是时过境迁,“如今,在先辈们的故乡草原,我只是来自另一片陌生草原的异乡人”。(《山那边有个地方叫友爱》)作者伫立在这片草原,思考原住民与外来人的变迁关系,也许现在生活的人民是和本来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完全不同的,原住民迁走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好像这里从来没有生活过这样一群人,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群人,这些外来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就像他们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一样。
无论是裕固族颠沛流离的逃亡,还是铁穆尔对自己民族不幸历史的拷问,其中都深藏着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追求。裕固族的文化身份几百年来如草原上空飘忽的云朵,每个牧民都可以仰望,但从未真正定格在尧熬尔的头顶。铁穆尔正是一位自觉认同民族文化身份的作家,他将自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本民族复杂的灵魂中,挖掘民族传承中隐藏的秘密,追寻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怀乡精神。但是当作者于孤独艰难中走遍亚欧草原,回溯祖先们迁徙的漫漫长路时,发现整个尧熬尔都变得连尧熬尔人都认不出了,作者在无数个夜晚回忆起儿时的草原生活,心中流淌的是潺潺甜蜜的草原声响,但是“我在群山草原间度过的童年,是那么幸福而又忧伤,亲近而又迷茫。昨天竟是那么遥远”。(《杜鹃飞渡》)
二、深沉的忧患意识
米兰·昆德拉说:“众小民族不曾体验过从来和永远就存在那里的幸福感觉。他们在历史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们的傲慢与无知;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③在历史上尧熬尔曾经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族群,后来他们不仅坚毅地生存了下来,并且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其他人数众多的族群淹没,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历史文化像是大洋中的一座孤岛”。(《苍天之子》)
除了这份与生俱来的孤独,裕固族经受更多的是来自异质文明的压制和不被理解,“无止境的开垦、庞大而密集的灌溉农业、林木的滥砍滥伐和采矿,引起的是祁连山水源的干涸,雪山雪线的不断上移或消失。而近几年各种文件和汇报材料中,都说是因为牧民的超载放牧引起了植被毁灭,导致祁连山地区水源干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几个老实巴交的山里牧民和山羊牦牛身上,世界的荒谬以至于斯”。(《失我祁连山》)古老的尧熬尔人从一开始只是善良安稳地生活着,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充满温情和爱,认为挖地和乱砍乱伐是莫大的罪过。但是多少年来,尧熬尔人生存的空间已经满目疮痍,在现代工业发展的巨大齿轮下他们无力抗争,只能默默接受岁月带来的这一切,这份痛楚也是尧熬尔民歌深沉忧郁的源泉,他们的民歌大多是悲歌,因为人民的历史本来就是一曲悲歌,人民对苦难的感受记忆永远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和生态保护、种族多样性似乎一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的局面是“社会越是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越高,社会发达的程度就越高”。④在这一点上,古老的尧熬尔人早已有了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天地之道、世界潮流、历史发展都是无法违逆的,人只能顺应天地之道、世界潮流、历史发展。尧熬尔人从混血到消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人只能顺应历史发展”。(《草原挽歌》)但是当生存环境不在,牧民失去的仅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栖息地吗?他们丧失的不仅是精神的天堂,更重要的是生活依托的沦陷,这双重的压力使类似尧熬尔这样的民族,生存犹苟延残喘。“苦难的民族、神秘的历史、忧郁的歌谣。那一个个在荒原上孤影飘零的优异的生命。”(《失我祁连山》)这是一位苦难的见证者写下的铮铮力证,更是一个守望者呐喊出的不朽歌谣,守望着一个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草原部落的最后历史。
三、奔腾的草原情怀
在《星空下的乌拉金》中,铁穆尔倾注了自己对本民族游牧文化所有的热爱之情,他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激情澎湃地谱写一曲曲哀婉动听、沁人心脾的草原之歌。尧熬尔人对于草原的热爱源于他们一代代人内心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情感,就像对亲人的不离不弃和对家乡的无限眷恋,草原就是他们永恒的归宿。“生于帐篷之下,死于苍茫荒原”是每一个尧熬尔人一生的始终,他们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交付于草原,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葬于草原之下。“草原!草原!三十多年来你使我这条好汉的生活充满了欢乐,是你把我引上了这条鄙视世俗前程的路,是你让我汲取了神一般的力量。我无法酬谢你,我只有一腔燃烧的血尽情泼洒在你的沃土上来祭祀你。”(《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杆上》)草原就是尧熬尔人的母亲、恋人、挚友、老师、乐园、天堂、归宿,如同这样的文字:“我日夜渴望同草地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拥抱,那才是我的亲人,我狂放的心与暴风雨最真挚的爱情。草原帐篷旁边度过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荒无人烟的群山草原就是我的爱人,我的初恋,我永远的爱。我的心灵从未背弃过它,它是我至死不渝的恋人。”(《车凌敦多布手记》)
正是尧熬尔人这样的情怀,注定了他们豪放多情但坎坷悲凉的一生,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草原在岁月流逝、世间变迁中一点点退化、消失,陪伴他们的牲口更是生存异常艰难,整个牧区都在沦陷。就像那首尧熬尔古歌:“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为草原哭泣。”曾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已经一去不复返,尧熬尔人只能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侵占而毫无反抗之力,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惆怅悲伤,是一个时代的错位感引起的迷失感:“这是源于日益破碎的草原,源于一个古老的部族慢慢消失在这个偏僻的群山,源于个人生活中的过失、错误、期待、恐慌和痛苦——原来就这么简单。”(《长满狗牙草的冬窝子》)作为一名有着纯正思想的尧熬尔人,铁穆尔也只能默默坚守自己民族仅存的生存之本,心中一边眺望,一边悲叹。“我的目光越过山峦和天空几乎看见了那新的灾难,远处的流沙,它又在悄悄地逼近祁连山下仅存的草原和森林。有谁知道祁连山的那一片片最后的草原,有谁知道这一个个小小的古老的部族,将面临怎样的苦难。”(《乌拉金的笔记》)但是,也许灾难才刚刚开始,从未结束,因为现代人时至今日似乎都没有觉醒,他们自恃清高的民族观还在控制着现代社会发展,草原战争、生存战争、生态战争的硝烟仍在继续蔓延,正如铁穆尔所说:“我的目光越过山峦和天空几乎看见了那新的灾难——远处的流沙,它又在悄悄地逼近祁连山下仅存的草原和森林。”
[注 释]
①②铁穆尔:《星空下的乌拉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版。
③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王锐.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诗性写作[J].民族文学研究2009,(1).
[3] 刘朝霞.游牧文化的歌者——论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创作[J].民族文学研究,2011,(4).
[4] 刘青汉.当代甘肃生态文学论[J].交通大学学报,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