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写实”一生中国绘画
2015-11-02张菡
文_张菡
高居翰:“写实”一生中国绘画
文_张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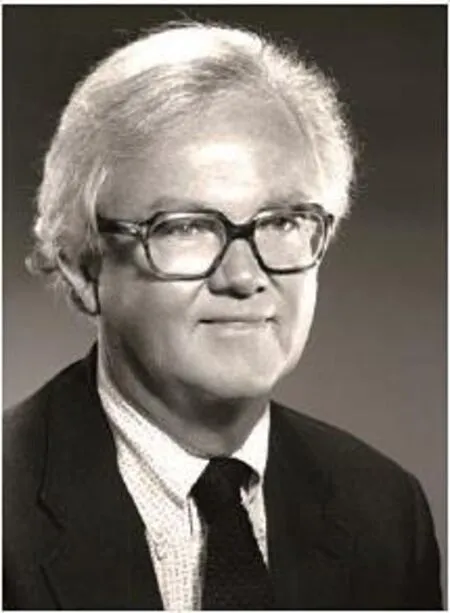
高居翰
有传闻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还需300年,姑且以此为前提——而许多西方人浸染其中,无意间推动了复兴的脚步,高居翰就是极重要的一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返归其心,也许应该从学习西洋画的热潮里抽身出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绘画,重逢我们自己的瑰宝。
如今这世道,艺术已不再被待见,艺术史研究也日渐式微。各国政要与宗教领袖的反艺术言论甚嚣尘上。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长说“艺术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世界”;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里尔说“当代艺术家显示了一些白痴行为”;奥巴马发表演讲时称“比起拿个艺术史学位,美国人熟练掌握制造业或者商业技能挣的钱要多得多”。
今天,任何一位采用水墨、毛笔在纸上作画的画家都要承担被低估的风险,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命运。
西方脉络
刚逝去不久的美国人高居翰,本名James Cahill。师承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和绘画的权威学者罗樾(Max Loehr)以及日本著名东亚艺术史学者岛田修二郎。
岛田在日本汉学界属“京都学派”,重训诂、考证。自古以来中国人治画史,看重题跋、印款与画论。
高居翰,成功将海外汉学研究与德国传统艺术史研究相结合,树立了以“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而被人诟病最多的是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历史与文献。
要了解他,得从中国绘画说起。高居翰与之共度了一生。他的头衔是“中国美术史学家”“中国绘画史专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国绘画受到西方“写实”风长年冲击,被普罗大众所熟悉的国画标签“写意”逐渐被“摘下千年帽子”。而中国传统画技中,不仅有写意,更有工笔。
知己知彼,何谓西方绘画的“写实”风格?
西方美术以“写实逼真”著称乃至传承于世。傅雷先生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里,筛选近20位名家正是写实美术(尤其绘画)充分发展而形成体系的五百年。
在文艺复兴初期,恢复古希腊重视形体之美的思想,通过焦点透视学、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色彩变化等法则,发展出刻画分明、平衡严整的写实风格。
17世纪,以鲁本斯、委拉斯凯兹、伦勃朗三家为代表,继续扩大写实对象,丰富画中的意境,倾向于用敏感的变幻、丰富的色彩表现形体和气氛。与此同时,油画的写实技巧也大有进展。
18、19世纪,“写实”概念不断变化,有了更多曲折、微妙的变化与发展。
读完此书,会对西方美术的“写实风格”有全面了解。书中所要强调的,是各个时代、各家各派谨守“写实”风格的各种规律,由于取材、手法、风格以及体现在这些因素中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不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不断的进入“写实”也正是西方人的思维脉络。
研究中国
到高居翰这一代,世界已进入20世纪初。1926年生于美国加州,同时也是一位“中国通”。要了解他,了解他对中国绘画的解构,先从其教学生涯说起。
《南方都市报》曾约稿美国普吉海湾大学艺术系教授洪再新,对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的高居翰作品系列做一个介绍。
洪再新在文中写道:“说到高居翰教授的为人,我和许多同仁有一个共识,就是一代大学者的风范。”
1992年,高居翰邀请洪再新作为美中学术委员会访问学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半年。他申报的研究课题是宋元绘画,但并不清楚究竟要做什么。
到了伯克利,高居翰就像对待所有他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一样,让洪再新用他办公室的资料,按英文字母顺序编排的各种中国绘画研究论文外文出版物,以及他本人占满几格书架的未刊手稿。
高居翰对别人阅读其手稿的要求是提出批评建议。在这些论著论文稿中,不但有别人的各种批注,还常常夹有他和有关学者的通信,呈现某个学术争论的来龙去脉。
敞开学术批评与争论,会成为激励学术发展的一个动力。如此这般开阔的学术襟怀,洪再新还是头一次亲身感受,至此终身难忘。
开放的图书资料和富于批判性的学术氛围,使洪再新对原来的研究计划产生了新认识,课题也日渐明确,力图找到一个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书画家关系的突破口。
每次和高居翰见面,第一句话就被问住:“你的命题是什么?”洪再新的“问题意识”逐渐强化,他明白,需从各种图像文献中确立值得一为的命题,并兼顾其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
当洪再新提出要对纳尔逊-埃特金斯美术馆所藏一幅元代蒙古画家的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时,高居翰马上就提供给他许多相关信息。在他离开伯克利前,高居翰又特意从香港利氏基金会找来一笔差旅费,保证洪再新能去美国东岸继续收集材料,最后完成《元代蒙古道士张彦辅〈棘竹幽禽图〉考略》的个案。
伯克利自由的学术氛围,使高居翰能最充分地展示其襟怀与才学,在中国绘画研究领域中,开宗立派,自成一家。(他曾经谢绝哈佛大学给他最高等级“大学教授”的聘任,坚持回到他钟爱的伯克利。)
去年2月14日下午两点,西方情人节当天,高居翰离世了,享年88岁。
在最后一篇博客的开头,他写道:“我现在差不多被床困住了,不得不意识到未来也将如此。”而“未来”也只有一个月这么短。
高居翰去世前已与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谈妥,捐赠了藏书。继 “贡布里希图书室”之后,那里会再成立一间“高居翰图书室”。
2006年,一次心脏手术后,高居翰的身体未能完全恢复。病榻上,他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套论述中国早期绘画的演讲视频。他把演讲视为自己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以及最为重要的成果:“如何才能将我头脑中的东西传达出去,这些信息、图像和想法无法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脑海里,所以需要以交流的形式保存。”
高居翰生前计划撰写一套五卷本的晚期中国绘画史,时间跨度从元代写到 1950年,但完成前三卷后,他对中国绘画史的看法以及研究重点发生了转变,因此改变了写作计划,并未把后两卷整理成书,读者只能在他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一些相关的论文和记录。
高居翰爱争论,坚决维护自己的学术思想,但同时又很活泼,有很多朋友。他与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在学术上争论了 50 多年,后者第一时间答应撰写回忆他的文章。
高居翰多年好友、同为中国艺术史学者的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说:“他是一个多面的人,不是窄窄的学者,个性和他的人一样,胖胖、多多的。”
对于高居翰慷慨的个性,班宗华与徐小虎深有体会。他们都不是高居翰的学生,但若要请教问题,都尽量详尽回答。徐小虎说:“他很大方,你不是他的学生,要跟他学,他也会带你。为了中国艺术史这门学科,他毫无保留,不惜自己的时间和体力。他去拍画,拍出来就是给大家,不会私藏。有些学者,拍出来就是宝贝资料,不给人家看。”
2009年,徐小虎最后一次去高居翰家里看他,那时候他在温哥华,已经不能爬楼梯了,但是拼命在做“溪山清远讲座”,也就是现在网上可看到的中国早期绘画免费视频。“他可能感觉自己时间不够,要赶紧把所有的东西都免费提供出来。目的不为成名,而是让世界认识他的最爱——中国绘画。”
欧美中国美术史界讨论与争鸣的风气非常之盛,从高居翰与班宗华之间的一来二往可见一斑。班宗华与高居翰通信50年,也争论50年。
班宗华在回忆高居翰的文章里写道:“我第一次写信给高居翰是在1962 年,那时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已决定硕士阶段要研究中国艺术史。卡希尔(高居翰原姓氏 Cahill 的音译)教授当然已经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的著作《中国绘画》在1960年出版,影响力和普及程度惊人。
关于研究生教育,我向他征求意见。他用一贯的周到向我说明,包括中国艺术方面著名学者各自的优势弱点,以及摆在我面前的多种可能性。最终他推荐了一个一年的课程,这一年我将跟着他在弗瑞尔艺廊学习,能够得到由他负责管理的助学金,接着我会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罗樾的博士,罗樾是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
我忽略了他的建议,选择了另一个课程。这是我与他第一次意见相左,我们在其后50年一直意见相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不同意高居翰有点像不同意上帝;他讲的话在中国绘画领域具有如此权威,以至于人们一想到自己与他持不同意见就几乎颤抖。)但我天生的本能一直都不信任权威,这种本能也存在于我们历史的根基里。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人们手写或用打字机打出信件,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从邮局寄出;在我与高居翰第一次通信后的数十年中,我收到他如此多的信件,其数量现在还令我吃惊不已。
他无疑是超级写手,对于每一阶段、每一流派的中国绘画,都非常了解,他的信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教学形式。
那一时期他确实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他也同样喜欢争论,不必说,庞大的知识储备使得与他的争论既令人害怕又让人获益。关于中国绘画及其学问的争论,贯穿我们持续50年的通信。”
在这50年的争论里,二人都曾有言辞激烈,未顾及对方感受的情况出现。
为了表明与高居翰通信的性质,班宗华在文中附了一则高居翰手写于1992年6月16日的便条。其中论述了一个计划中的项目,把在伯克利图书馆里找到的一本日本的老拍卖目录中所列的全部中国绘画拍摄下来。硕士生裴珍妮(Jennifer Purtle)当时承担了这个项目。高居翰在信里也提到了她。

2013年,高居翰在家中庆祝生日
李可染曾撰文讲张大千想去拜访齐白石,齐白石拒绝相见,因为“我向来不喜欢这种造假画的人。”
班宗华认为,这封信展现了高居翰对于艺术史家必须寻找和更好地利用视觉研究材料的准确感觉,他对同事与学生接触这些材料的持续性鼓励,以及他对新项目自发的热情。
与中国交流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来看看高居翰对中国书画界巨擘的态度。
高居翰生前想办的最后一个展览是张大千书画展。张大千是现代首屈一指的国画大师,在技巧方面登峰造极。但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顶级的古画仿造家。
张大千毫不讳言自己早年曾大量作假,专仿石涛、八大山人的画,骗了不少大富豪。有次一位富商请了几位大藏家观摩他重金购得的石涛册页,结果张大千看了第一页,就轻松讲出后几页内容,然后告诉这位富豪:“惭愧,这是俺前天刚画的。”(李可染曾撰文讲张大千想去拜访齐白石,齐白石拒绝相见,因为“我向来不喜欢这种造假画的人。”)
高居翰对张大千的伪作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个人网站上,登载了他对张大千伪作的研究成果。他认定的伪作有63幅,不过出于学术严谨性,还是在这份研究成果上特别标明:“我并不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这个研究结果可能有错误。”
这63幅可能的伪作中,五代时期董源的《溪岸图》影响最大。董源是生活在公元十世纪的画家,被称为南方山水画派之祖,位列“五代、北宋间四大山水画家”。卒于962年,距今已经上千年。《溪岸图》为董源存世的唯一画作,史料价值巨大。
真正让这幅画产生国际影响的,还是高居翰。正是他对此画做出伪作鉴定,引发了长达15年的国际大辩论。
1997年5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裔董事唐骝千先生花重金购得《溪岸图》,并在大都会博物馆展览。同年8月《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引述高居翰的观点,认为此画并非十世纪的古画,而是张大千伪作的精品。由此,高居翰与《溪岸图》被联系了起来。
在张大千、徐悲鸿等人的描述中,故事是这样的: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于桂林购得《溪岸图》,后借与张大千带回四川观赏。张大千以金农的《风雨归舟图》与徐交换,得到《溪岸图》的所有权。50年代,张大千将其卖给了美籍华裔收藏家王季迁。这之后就是上文提到的,1997年唐骝千先生从王季迁手中买到了这幅画。整个过程流传有序,似乎无可指摘。
徐悲鸿在私人信件中也透露过购得这幅画的欣喜。1938年徐悲鸿致孙邦瑞的信中就曾说“弟得董源巨幅水村图,恐为天下第一北苑。……绢本颇损,但画佳极”(《水村图》是当时对《溪岸图》的命名)。这封信原件曾在2010年上海恒利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以26.88万成交,网上可查到。
在《〈溪岸图〉起诉状——十四项指控》一文中,高居翰提出了十四项质疑,内容基本可归为三类:从笔法、笔触、光影处理等细节看,与同时代的其他画作有异;而这些异处,与张大千伪造的作品雷同;在古人的书画著录或其他文字记载当中,并没找到此画的可靠记载资料。
一方是《溪岸图》流传历史;另一方是凭借专业基础得出的“张大千仿造”论。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高居翰需自圆其说。于是他展开推理,张大千伪造《溪岸图》,且同徐悲鸿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推理内容如下:
1、通过对笔法、笔触的细节观察,认定这是现代伪作;
2、但此画确实非常好,现代仿古画能仿得这么好的,只有张大千,而且张大千的其他仿画与此画有相似之处;
3、如果是张大千伪造,则与这幅画的流传历史有冲突(徐悲鸿买来,张大千用自己私藏与其交换),那么这个流传历史就是伪造的,徐悲鸿说谎了;
4、徐悲鸿为什么说谎?因为当时正与老婆离婚,缺钱。
高居翰在徐悲鸿身上,看到的是中西方风格交替出现,没有融合。“他的油画是写实的,水墨是中国的,两者结合有限。同时可以看到对学院派欧洲模特的依附限制了他的能力,也限制了中国画对二十世纪西方绘画的转变与成就的回应能力。”
而对另一大家吴冠中,他这样写道:“在将两种绘画介质,两种传统,两种风格的结合上,吴冠中前进了许多。在油画中,他找到了与中国画用笔相模仿的技法,在大片泼彩上作幼细的线条勾勒、讲究气韵等,都是典型的中国水墨传统。相反,在中国画近作中,发挥了用笔与泼墨能量造成类似后期印象派的平板,概括而不抽象。将吴氏八五年的油画《水乡周庄》作比较,可以看到绘画介质的差异已缩减到无关大局的程度。”

吴冠中赠送高居翰的画集

台湾出版的高居翰著作
我们再次还原《溪岸图》事件,会发现疑点。金农是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而清代金农与五代董源的艺术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徐悲鸿为何会接受张大千如此“不等价交换”;而徐悲鸿又是如何从广西购得《溪岸图》,期间发生了什么;以及是否他为证名此图为真作,伪造了与友人书信往来的证据……一切留待后人评说。
围绕《溪岸图》,学术界共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张大千伪作,一种认为董源真迹,而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它至少是一幅宋代古画,是否为董源真迹则无从考证。无论如何,这场由高居翰引发的旷世争论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学术问题,而争议向来可促进学术研究,也可丰富如今中国书画的鉴定技术。
方法论解构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书画总归“不分家”。书法被誉为“无图之画”。相传南北朝时期的陆探微,南朝宋明帝时的宫廷画家,擅肖像、人物,兼工笔蝉雀、马匹,亦写意山水草木。后人将他和顾恺之并称“顾陆”。据说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陆探微推崇备至,认为陆探微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外在形式的完美,将其置于上品之上。
唐朝人士张怀瓘曾这样评价:“象人之美,陆得其骨,张得其肉,顾得其神。”陆即陆探微,张指张僧繇,顾是顾恺之。既“超越了外在形式的完美”,又能“得其骨”,按此推论,西方绘画“写实逼真”这样的向度在陆探微的画艺里,早已不在话下。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在西方推进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者,高居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欧美已经有了许多对中国晚期绘画(主要指明清绘画)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了许多重要的明清绘画专题展览,但为何艺术批评家对中国晚期绘画依然如半个世纪之前一样在误读?
高居翰列出了三个原由:
其一,西方人有一个固定思维,认为中国绘画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宋代达到顶点,之后开始衰落。
其二,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晚期绘画中那些形式和表现方法(即文人画)。
其三,在元、明、清的许多画作中,都可以看到标明临仿某位前代大师风格的题跋,对此西方人当真了,从字面上加以理解,觉得中国晚期绘画总是陈陈相因,毫无创新。
在高居翰看来,西方人的理解可能有偏差,但确是晚期中国绘画的特点,是需要解答的疑惑。
为此,高居翰做出了他的解答:
宋以前,中国绘画以再现自然世界为最重要的方式,南宋末期,画家描绘真实自然世界的技巧已趋于完善,中国绘画风格发展的历史便“终结”了,但中国绘画仍在前行,依然富有创造力,画家们转而寻求“自我表达”、“复古”。
而“自我表达”并非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询绘画反映人的内心活动,“复古”也不是真正为了让前代画风复兴,这一切都是画家们面对不同社会环境的“策略”。
高居翰举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等重要画家,来说明如何与不同社会情境互动从而展开“策略”,同时力求阐述清楚他自己设下的问题:既然宋以后的绘画史“终结”了,线性发展的风格史不再,那么如何去描述依然在历史长河中前行的绘画?替代早期绘画连贯的风格史发展线索的究竟又是什么?
陈丹青曾说:“我从来没有传回任何关于成功的消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1985年美国纽约出版高居翰所著《中国绘画》精装本

高居翰认为躁郁症成就了八大山人的卓越风格
在高居翰看来,赵孟頫的两个“策略”为后来的画家提供了灵感。一个体现在《鹊华秋色图》中。赵孟頫以“复古”为口号,把南宋以来成熟的画风猛然转向一种精巧复杂的“原始主义”,抛弃原有的对空间、景物的视觉真实再现,而追求浅显的空间、稚拙的景物。
另一个高居翰称之为“风格的极端主义”。画家把干笔皴擦的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画中没有设色,没有水墨晕染,甚至也少有线条的描绘,景物简单之极。
赵孟頫的做法意味着中国绘画依然有别的方式展开新的创造。之后的画家也有所继承和发展,从元四家、明代沈周,到董其昌,弘仁、八大山人等。
高居翰强调这种“发展”不再是一种线性的前后相接,中国晚期绘画依然构成“无发展”的风格序列,其中关键是不同画家面对不同社会情境使他们在“复古”、“仿古”以及“风格极端主义”的“策略”之中自由地往返于古今,不同风格被单独拿出,被赋予不同象征意义。因此,他曾推崇明末变形主义,也认为躁郁症成就了八大山人的卓越风格。而历史虚虚实实,并不只停留于表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更易理解金灭南宋,蒙古政权建立;乃至明末清初,画风不时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家天下”的情怀,文人士子风的盛行,心有灵犀,隐之而不发——“国破山河在”、“只是朱颜改”……而这些,西方人无法参透,高居翰只能从方法论上来摸索,不断靠近中国绘画精髓的根脉。从他撰写过程中改变写作计划即初现端倪。
后记
陈丹青曾说:“我从来没有传回任何关于成功的消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
而高居翰作为一个美国人,一生挚爱中国绘画。作为中国人本身,更应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回归生命的本源。中西方文化同属一个世界,本应“和而不同”,此“和而不同”也正是为了相互生发,相互促进,世界本就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