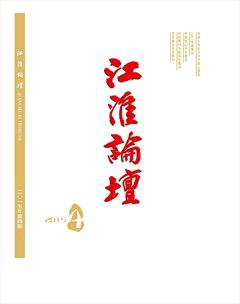本土语境中帮助犯处罚根据新论*——共同引起说之提倡
2015-11-02江澍
江 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武汉 430073)
一、问题的提出:犯罪构成理论引出的帮助犯处罚根据问题
在德日刑法“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中,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是刑法认定犯罪的基础。在罪刑法定主义导向下,为刑法分则规范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应是行为人单独亲自实施的行为,只有亲自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行为人才是刑法应当处罚的。[1]那么,对于非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教唆犯、帮助犯的理论处罚根据,应如何解释呢?
有德日学者主张,将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同样视为构成要件行为,直接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处罚根据问题,即在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上,提供了某种条件的人,都是正犯。[2]但是,多数德日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其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所言:“刑法的构成要件是法律安全的保障,如果说一切都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那么,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消失了,若再联想到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大致证明和特征,那么从上面的见解出发就会连合法和违法的界限也变得不清楚了。所有这些则意味着整个刑法体系的崩溃。”[3]所以,跳出犯罪构成理论,另辟蹊径寻觅共犯的处罚根据,成为德日学界的主流选择。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不同,但能够符合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一般也应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是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所定型化的行为。[4]因此,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亦无法解决帮助犯、教唆犯等非实行犯的处罚根据问题。目前,我国学界对教唆犯的本质问题研究较多,对帮助犯处罚根据问题着墨较少。基于行为构造的区别,两者虽有相通之处,但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自己去杀人的行为,与教唆他人杀人的行为和帮助他人杀人的行为是有区别的——伦理性的、类型的区别”[5]。基于实践认定帮助犯的需要,帮助犯处罚根据问题在理论上应得到重视,即如日本学者大越义久所言:“共犯论中的诸问题,归根到底是共犯为什么处罚的问题。”[6]6可见,无论在我国共同犯罪语境中,还是在德日共犯语境中,处罚根据问题均属根基性问题。借鉴德日刑法共犯理论,厘清我国帮助犯处罚根据问题,将有助于推动共同犯罪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二、贡献与局限:帮助犯处罚根据之现有学说的反思
德日学者在共犯处罚根据学说中论述了帮助犯处罚根据问题,形成了“责任共犯说”、“违法共犯说”和“惹起说”等代表性学说。
(一)“责任共犯说”的反思
德国学者H·麦耶是 “责任共犯说”的提倡者,他指出:“教唆者一方面对法益加以侵害,他方面对正犯者加以侵害,是双重形态上犯罪。与其将外部的损害的惹起看作犯罪的本质,不如将对伦理秩序的侵害看作犯罪的本质,这个诱惑的要素比客观的法益侵害,原则上还要重要。从而教唆者的类型的行为与正犯者的实行不同,从诱惑的观点说,不得不认为至少与正犯有相同的犯罪性,教唆者对法益的攻击,即使不超过实行杀人的人的程度。确实,教唆者制造了杀人者,所以教唆者与正犯者同样程度负责任。”[6]71
“责任共犯说”在解说帮助犯处罚根据时存在局限。一方面,当帮助犯犯意形成的时间晚于正犯时,如正犯主动向他人寻求对犯罪的助力,如按照“责任共犯说”的逻辑,不是共犯诱惑了正犯,而是正犯诱惑了共犯。另一方面,“责任共犯说”注重对正犯者主观犯罪思想的归因,却忽视了对正犯行为不法的溯源。在现代刑法中,单凭犯意的确立,而缺乏客观的不法行为,是难以体现刑罚处罚的正当性的。
(二)“违法共犯说”的反思
德日学者分别从法益与规范角度展开“违法共犯说”。德国学者莱斯(Less)认为,当一个共犯使正犯陷入不法时,便侵害了一个独立的且特别的法益——他人人格之尊重。人格的尊重和自由发展的权利是通过宪法保障的,因此是一种法益。教唆者通过使他人陷于不法而侵害了这一法益,即他侵害他人良心的平和,危及他人所享有的社会尊重,并且通过诱使他人形成犯罪意思动机而介入侵害他人人格的自由发展。[7]30日本学者认为,正如正犯是违反了“不能杀人”的规范,共犯是违反了“不要教唆他人杀人”的规范一样,共犯和正犯所面对的规范的内容是不同的。违法共犯论,本来是主张违法的实体是和行为人有关的“人的不法论”所主张的观点,认为亲自实施犯罪的正犯和让正犯实施犯罪的人,在违法性的问题上,不可能是相同的。[8]
(三)“惹起说”的反思
“惹起说”一般认为,帮助犯等共犯通过帮助行为等非构成要件行为惹起法益侵害是其处罚的根据,至于帮助行为惹起法益侵害的方式如何,惹起说内部存在分歧,分为“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与“混合惹起说”。
“纯粹惹起说”有“极端”与“折中”之分。 “极端的纯粹惹起说”将共犯行为视为引起构成要件事态实现的独立的条件,废止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彰显了“扩张正犯”理论的学术立场。“折中的纯粹惹起说”承认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强调共犯的可罚本质在于共犯者自身行为的不法上,而不应取决于刑法对他人行为的评价,并指出共犯有其独立的、特别的构成要件。[7]32-33“修正的惹起说”认为共犯的违法性不是由来于共犯行为本身,而是由于正犯行为的违法性。处罚共犯者,是因为其诱使、促成了正犯的行为,共犯的违法必从属于正犯的违法性。[9]311“混合惹起说”认为共犯通过正犯者间接地侵害了法益,共犯的违法性由来于共犯行为自身的违法性和正犯行为的违法性。“混合惹起说”一方面承认共犯处罚根据来源于共犯行为自身,另一方面指出共犯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行为,认为共犯行为通过正犯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是共犯处罚的根据,是对“纯粹惹起说”与“修正惹起说”的一种折中,也被称为“折中惹起说”。“惹起说”以行为为中心,打开了共犯处罚根据探索的正确之门,将问题的解决重新纳入正规,正如日本学者照沼亮介所言:“教唆犯与帮助犯在不法上的差异,应从行为构造上的差异导出。 ”[10]
“纯粹惹起说”撇开正犯行为,单独强调帮助行为等共犯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具有片面性。例如银行职员甲为乙开设专用账户,乙用于正常收支货币,甲的行为不会受到刑法的评价;但如乙将专用账户用于洗钱,甲便可能成立帮助犯。由此,决定帮助犯处罚根据的因素不仅在帮助行为,也在正犯行为。“纯粹惹起说”重视共犯行为的作用,但轻视正犯行为的价值,其结论并不恰当。“修正惹起说”的“修正”意义在于重塑正犯行为的主导地位,但矫枉明显过正,致使共犯行为完全成为正犯行为的附庸,无独立存在价值,共犯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事实联系会被割裂,共犯人的刑事责任难以被准确认定。在正犯者侵犯了法益而共犯者没有侵害法益的场合(如共犯者是被害人),根据“修正惹起说”,无疑会将被害人作为共犯处理,这就违背了法益保护原则。同时,“修正惹起说”过多强调了对共犯者的处罚谦抑,而忽视了共犯人自身的违法特质。正如姜涛教授所言:“刑法谦抑主义单一强调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也是片面的。”[11]
三、多因一果与平等位阶:帮助犯处罚根据之共同引起说的立场
(一)主从行为的定位:“混合惹起说”的法益侵害疑问
“混合惹起说”提倡的帮助犯的可罚性来自于帮助行为对正犯行为的依附性,体现在:其一,帮助行为无法主导法益侵害的进程,必须附属于正犯行为之后;其二,帮助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原因力是间接的。
本文认为,这种定位值得推敲。展开前文设例,坐在电脑前的甲试图通过网络侵入他人银行账户盗窃财产,却对电脑和网络知识一无所知,手拿鼠标不知如何操作。此时精通网络技术的乙便在电话中近乎“手把手”地指导甲如何操作,帮助其一步步进入他人银行账户,并成功盗得资金。甲操作鼠标侵入他人账户是盗窃罪的正犯行为,乙通过电话指导甲盗窃的行为是帮助行为。由于甲对电脑和网络知识的匮乏,乙的帮助行为实际上主导了整个盗窃进程。此例中的帮助行为并非依附于正犯行为惹起法益侵害,反倒是正犯行为在对帮助行为的逐步“依从”下引起法益侵害。可见,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于法益侵害的影响力并不存在远近之分、直接与间接之别。
(二)平等位阶的定位:共同引起说的法益侵害主张
“混合惹起说”的缺陷可以通过“共同性”予以弥补。 “共同性”是指当共同实施的犯罪是结果犯并发生危害结果时,每一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共同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是两个人以上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单独犯罪中一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比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共同犯罪行为是围绕一个犯罪目标,互相配合、互为条件的犯罪活动整体,正是因为这个行为的整体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换言之,这个行为整体是危害结果发生的统一的原因,而每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一部分。[12]借鉴“共同性”,在考虑帮助犯处罚根据时,引起法益侵害的行为应是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相结合形成的共同侵害行为之整体。这符合哲学中的多因一果定律,肯定世界万物处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客观事物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非只是双向的,即链条版的,而且是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13]
与“混合惹起说”定位不同的是,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位于导致法益侵害产生的同一位阶上,两者组成一个共同侵害行为,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可偏废、不可或缺。作为引起法益侵害的原因力,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但它们又不是单独的引起法益侵害,而是结合成一个整体导致法益侵害。两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无主次之分。这样,帮助行为与正犯的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该共同行为与法益的侵害之间具有“物理的因果性”。因此成立共同犯罪。[14]
四、结果与危险:帮助犯处罚根据之共同引起说的展开
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表现有两种类型:一是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结果,如甲提供手枪给乙,乙用手枪杀死了仇人丙,甲和乙的行为共同引起了生命权被侵害的结果;二是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如甲提供钥匙给乙,乙用钥匙打开办公室门锁准备盗窃时,被路过的保安抓获,甲和乙的行为共同引起了财产权被侵害的危险。其中,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应成为实践处罚帮助犯的刑法底线。
(一)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结果
有时,帮助行为之于犯罪结果的影响力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是不可替代的,主要表现为帮助者为实行者准备的作案工具是别人无法提供的但又是完成犯罪所必需的,或者实行者由于自身专业、技术、资质、地位的缺乏必须仰仗帮助者予以犯罪指导或协助的。此时,正如罗克辛教授所言,帮助行为对于结果而言,可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比如,帮助犯为他人提供无法得到的备用钥匙,没有这把钥匙,小偷不可能打开保险箱。[15]
有时,帮助行为之于犯罪结果的影响力是可以替代的,即使缺乏帮助者的贡献,实行者也能通过其他手段完成犯罪。例如乙得知甲意图杀人,便为其准备了一把手枪。实际上甲已经准备好了杀伤力与性能不输于乙提供的手枪的另一把手枪,但碍于乙的“好意”,甲仍然携带乙提供的手枪,赶往犯罪现场,射杀了被害人。此时,也许有人认为,即使没有帮助行为,危害结果也同样会出现,并无处罚帮助犯的必要。但笔者认为,这种基于因果关系条件说的假设并不成立,不可否认的是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在此情况下已然结合成共同侵害行为,并导致了法益侵害结果,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没有帮助行为的存在,实行行为也能单独完成对法益的侵害的说法毕竟是一种假设,无法抹去帮助行为的原因力已然植入犯罪结果之中的事实。对于因果关系而言,在考虑所有导致结果的中间因素的情况下,该种助力以完全具体的形式已经影响到结果,这就足够了。没有帮助犯的助攻最终也会出现结果,并没有改变其中的因果关系。本来可能取代现实因果的假设的因果流程,对于其因果性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二)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
当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时,虽然危害结果尚未出现,但帮助行为的原因力已实际融入与实行行为共同制造的危险之中,具有可罚性。例如甲提供一把手枪给乙用于杀人,乙进入犯罪现场后用手枪瞄准仇人丙射击,但因距离较远未击中丙。甲的帮助行为与乙的实行行为已经形成了对丙生命法益的威胁,将其置于具体危险之中,只不过因乙射术不精,未转化为实害。又如甲为乙入室盗窃提供钥匙,乙在开锁时不慎将甲提供的钥匙扭断,乙在惊慌中逃离了现场。此时,盗窃结果虽然没有出现,但甲的帮助行为与乙的实行行为对财产法益已经构成了足够的威胁,具有了违法性,有处罚必要。
[1][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775.
[2][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99.
[3][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M].王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1.
[4]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4.
[5][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王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84、92.
[6][日]大越义久.共犯的处罚根据[M].成文堂,1981.
[7]刘凌梅.帮助犯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8][日]高桥则夫.共犯体系与共犯理论[M].成文堂,1988:165.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11.
[10][日]照沼亮介.体系的共犯论?刑事不法论[M].弘文堂,2005:158.
[11]姜涛.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刑法父爱主义之提倡[J].江淮论坛,2015,(1).
[12]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4.
[13]温洪潮.事物是“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的统一[J]哲学动态,1983,(4).
[14]刘涛.片面共同正犯的成立及其范围[J].政治与法律,2014,(11):31.
[15][德]克罗斯·罗克辛.德国刑法中的共犯理论[A].劳东燕,李钢,译.陈兴良.刑事法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3.
(责任编辑 吴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