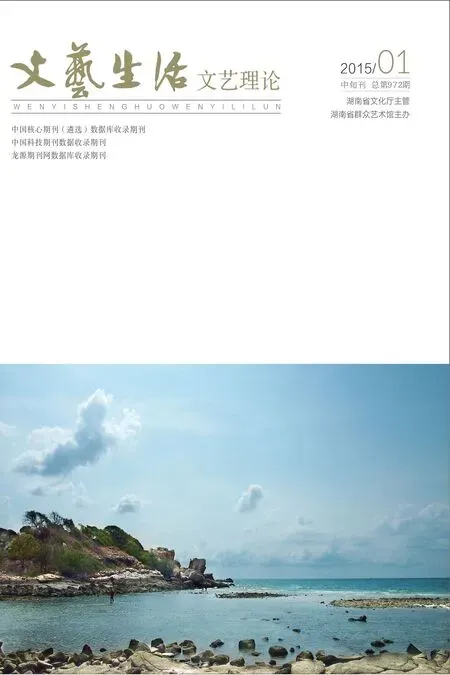论湖湘文化特质中的“霸蛮精神”
2015-10-28张丹
张丹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论湖湘文化特质中的“霸蛮精神”
张丹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仅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标准,从学术成就和政治贡献来解读湖湘文化特质是不够的。“霸蛮”也是湖湘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元素,不仅需要破除关于霸蛮的文化误读,还应将之列于湖湘文化中深层核心结构的地位。“霸蛮精神”的双重成因,一方面源于湖湘地区地理环境,另一方面源于湖湘社会阶级文化的构成,尤其是江湖文化、世俗文化的成分。“霸蛮精神”主要有三大重要元素,包括:独立无依、自我意识强烈、不轻易服人的“尚独”特性;强与韧的结合;不怕死、不要命的殉道精神。这些构成了湖南人“霸蛮精神”的源泉,是湖南人独特民风、民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使湖湘文化能傲立于地域文化之中的支撑力量。
霸蛮精神;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阶级构成;“尚独”特性;强与韧的结合;殉道精神
朱汉民先生说“湖湘文化首先是一种观念文化、精神传统。”对于湖湘文化的内涵,往往更强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一方面,更注重研究湖湘历史上知识群体的学术事功,更重视湖湘人士创造的巨大政治事功,尤其是注重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涌现出的众多思想先进、革命坚定的湖湘志士们。
纵观湖湘历史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从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到后来的推动湖湘文化或船山文化发展的周敦颐、王夫之;再到近代人物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以及现代的革命志士蔡锷、黄兴、杨昌济;还有中国革命和建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各自的个人轨迹、生平志趣;再看看现今社会对湖南人士的各种评价,我们发现:仅仅是学术成就和政治贡献,不足以纵贯整个湖湘历史,也不足以完全涵盖湖湘精神的全部内涵。贯穿整个湖湘历史的还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元素就是——“霸蛮精神”。
“霸蛮”这个词,而在湖南地区的口语中经常出现,它恰恰反应湖湘精神,是一种在这个区域存在并流传的文化特质。但是对于它研究还没有相当的重视,甚至这个词本身的意义还存在一定的文化误读。
一、“霸蛮精神”的文化误读以及正解
(一)对“霸蛮精神”的文化误读
很多人都听说过湖南方言中经常出现的“霸蛮”一词。“霸”,多衍生出霸道、强夺、不可理喻的印象;“蛮”,多有蛮横无理,强悍暴力之嫌疑,由此“霸蛮”二字常常使得外乡人对湖南人的脾气性格和行为方式多有畏惧心理。
事实上,中国古代“东方曰貉,南方曰蛮,西方曰羌,北方曰狄”,“蛮”仅仅指代方位上的南方。周朝建立后,楚人自称“我蛮夷也”,是对周人怀有戒心和敌对情绪的表现;同时,在中原人的文化自大心理作怪下,将“蛮夷”以讹传讹,成了现今含有诋毁、贬斥之意。
而“霸蛮精神”是指湖南人更多的体现出不依不傍、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轻易服人的性格特征,以及精神上强悍坚韧、百折不回、不怕难、甚至不怕死。
(二)“霸蛮精神”属于文化中的深层核心结构
一种特定的文化可以从结构的层次分析,即分为文化的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核心结构:表层结构主要是以这种文化相应“有形之物”,包括物质产品和劳动创造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文化的中层结构主要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产物,包括自然和社会理论、社会组织制度、人际关系、伦理道德规范等等;文化的深层核心结构就算是精神、心理意识方面的文化状态,包括社会心理、价值取向、人伦观念、思维模式、致知途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和民族性格。“霸蛮精神”体现在湖湘人士的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中,属于精神和心理的范畴,应该列于文化中的深层核心结构。
二、湖湘地区地理环境及社会阶级的双重成因
湖湘地区霸蛮精神源远流长,其成因如何,现代文明中又是否值得传承、提倡呢?
(一)湖湘地理环境的鲜明区域特征
一个区域的文化要和它的四周区别开来,首先要研究这里的山水、语言和技艺。钱基博先生就曾经评述过湖南的自然环境及其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他称:“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由此可见,湖南呈现出多山岭、多丘陵、多水系、少平原的地貌特征,这本身与中原文化的北方平原地理环境截然不同。
多丘陵山区的人,受山水之阻隔的自然地理环境,培养了湖南人的独立意志,沟通不便则干脆不依不靠;但同时湖南人对外部世界有强烈的渴望,一旦具备交流条件,则能将天生的外向、向上的冲动和向往转化为更强的行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湖南始终能焕发蓬勃的力量,保持快速、强劲的发展势头,敢为人先,当仁不让!
(二)湖湘地区的社会阶级情况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阶级来考察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就是庙堂文化和江湖文化的结合。湖湘地区的庙堂文化中融入了儒、法的文化系统,其文化特征较为精致成熟,但有着唯我独尊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道的意味。
另一方面,江湖文化是指世俗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系统。随着人口迁徙,湖南历史中一直存在“三苗文化”和“荆楚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也深深影响了世俗社会的各色人等,尤其是普通民众。这种潜流文化虽然从来没有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主流,但却使湖南人具有了某种反主流、犯规范的草莽野性气息,以及不受拘束的霸道意味。由此,每每民族危亡之时,湖南人的革命意识尤其强烈,革命意志坚定,不怕战,不怕死。
三、“霸蛮精神”的具体体现
“霸蛮精神”在湖南地区形成并传承千年,现在时湖湘文化的重要研究版块,那么它如何具体体现在此地的民风、民性中,这里总结出了几个方面。
(一)独立无依、自我意识强烈、不轻易服人的“尚独”特性
根据上述地理特征,湖南自古沟通交流不便,“风气锢塞,不为中原人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以独立。”性格中遗留下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根性,也就是辛亥革命中的湖南志士杨毓麟所称的“独立根性”。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至于直接之精神着,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立,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
近代辛亥革命志士中黄兴,本是信服孙中山先生的,在国内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立下不朽功勋;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坚决不如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对孙个人宣誓效忠,体现了他绝不盲目服从的性格。彭德怀和毛泽东同位湖南湘潭人,革命时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华,长期在毛的领导下进行军事斗争;但晚年也在庐山会议上上书,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郭嵩焘也是不顾被人垢弊为“辱国”而慨然楚人中国第一人大使。这些人都体现出湖南人士浓烈的自我意识,独立无依、不轻易服人。
(二)不畏艰苦、自强不息的强,坚忍不磨、百折不回的韧
湖南人口中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向上追溯到三苗部落,他们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从黄河中下游迁徙到湖南地区,不畏艰辛,不避艰险,并且顽强地作为一个整体,始终保持了部族的凝聚力。后来在湖南西南山区,以武林文起点,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自强不息,不畏艰苦,面对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也从不屈服的精神,对现在的湖南精神风气中的“刚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湖南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1.2%,丘陵及岗地占29.3%,所以有许多依山开垦的蓑衣田、斗笠田,有时一块地的可耕作面积不过2-3平方米。如此恶劣的耕种条件,使得湖南人忧患意识强烈,自古就明白必须通过不懈的与天斗、与地斗,才可能解决基本温饱。养成了我们坚韧不磨,百折不回的韧性。
这种“刚强”与“坚韧”的结合,塑造了湖南人的性格雏形,成为湖南风气的基本元素,使得“湖湘人士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产生“天下舍我其谁”的高度自信。”
(三)不怕死、不要命的殉道精神
湖南人不仅不怕苦,不怕难,而且还不怕死。自古以来,每每民族存亡的危险时刻,都有军人将士、文人志士挺身而出。陈独秀曾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句话高度评价了湖南人体现的不怕死,不要命的斗争精神。
曾国藩、罗泽南等,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黄克强历尽艰辛,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和子弹不足的两千士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这些都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呢!
孙中山先生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认为五年之内没有武装革命的可能了。可是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却不信邪。不到半年,他们就在武昌城头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多少爱国将士牺牲在此役中。因此,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湖南人“革命军人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日本进攻长沙,本以为长沙无险可守,称“纸糊的长沙”。可是当时的长沙守军却不信邪,偏要打一打。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连续三次长沙会战。其中,第三次击毙日寇5万多人,日本高级指挥官是靠直升飞机才勉强逃脱。这不仅仅是长沙的胜利,湖南的胜利,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同盟军队的首次胜利记录。英国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不怕流血牺牲也并非军人的专利,文人志士们为了真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也当仁不让,充分体现出湖南人骨子里的“殉道精神”。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参与者纷纷逃命之际,独自决绝逃走,并说“中国历代变法还没有流血牺牲的人,就让我谭嗣同做第一人吧!”后来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在湖南历史中,有多少革命先辈用自己的热血唤醒了民族的良知,改写了民族的命运。
四、结语
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是一个丰富又复杂的综合体。在此,湖南典型的“霸蛮精神”为依托,破除有关的文化误读。分析阐述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阶级文化的双重成因。最终,阐述了“霸蛮精神”的三大重要元素,包括:独立无依、自我意识强烈、不轻易服人的“尚独”特性;强与韧的结合;不怕死、不要命的殉道精神。这些构成了湖南人“霸蛮精神”的源泉,也是使湖湘文化能傲立于地域文化之中的支撑力量。
★此论文拟为2014年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项目的成果之一。
[1]蔡栋.湖湘文化访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陈代湘,黎跃进.胆识+霸蛮=湖南人:解读湖南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3]方吉杰,刘绪义.湖湘文化演讲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罗敏中.论湖湘文化之源及其“蛮”的特质[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05).
[5]聂荣华,万里.湖湘文化通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长沙:岳麓书社,1985.
[7]万里.湖湘文化大辞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8]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9]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10]朱汉民.湖南学派史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G127
A
1005-5312(2015)02-01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