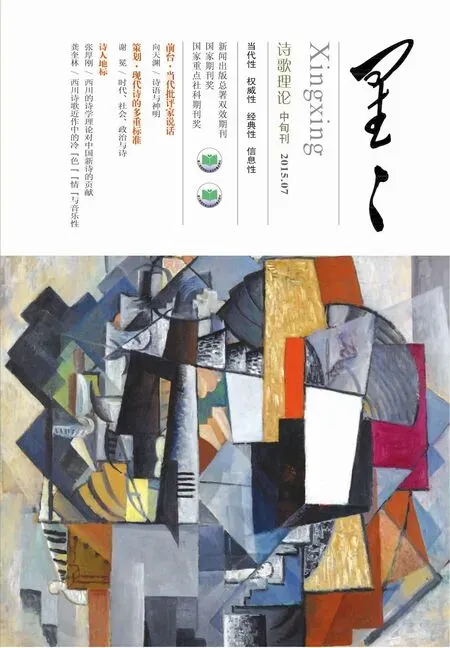时代、社会、政治与诗
2015-10-26谢冕
谢 冕
时代、社会、政治与诗
谢 冕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广西南宁,“南宁诗会”由几个高校联合召开,基本是民间状态,却是有史以来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第一个盛会。那个会上开展了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关于新诗潮的大讨论,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中国诗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改变了原先停滞的、封闭的、单一的状态,开始了充满活力的多元发展的局面。诗歌从未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缺席,而是充当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在新时期以来的各个阶段都带动和促进了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新时期如此,新世纪也是如此。
其一,在中国文艺的转型中,朦胧诗的出现,对新时期文艺的创新和探索,意义十分深远。其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诗歌始终坚持清贫的状态,诗人们始终坚持诗歌艺术的纯粹性。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艺术品质保持得最好的是诗歌。诗人当然也受到了物质的、物欲的引诱和干扰,但在所有艺术当中,比较而言,诗歌仍然是最清纯的。其三,诗歌的民间活动从未像现在这样蓬勃活跃。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除了正式的上半月刊以外,都出版了下半月刊,甚至有一月三刊的。无数的诗歌民刊、诗歌选本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每年都有多家出版社在出年度诗选。杨克坚持编了十多年的“新诗年鉴”。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太多了。企业家和官员参与到诗歌的写作和出版中来,诗歌的写作和出版波及到身居官位的人,他们对诗歌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些都在证明,我们的诗歌充满了活力。在众多文学艺术形式中,诗歌是最有生机的一个部门。
但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下诗歌众说纷纭,有迥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好得很”,一个是“糟得很”。说“好得很”的大多是诗人自己和诗刊主编和编辑们,是写诗的和编诗的人,说“糟得很”的是广大读者。我的态度,既不是好得很,也不是糟得很。我自九十年代以来始终对诗歌状态不满意,是持批评的态度的,我强调,诗歌应“慎言繁荣”。在一次会议上,我讲:有些诗正在离我们远去。有人批评我的态度,说:不是一些诗离你远去,而是你离诗远去。我自省,我未曾远离诗歌,我从来都是诗歌创新的支持者,我从来都和诗歌的敬业者站在一起,我总是为诗歌的繁荣祈愿,我怎么就“离诗远去”了呢?后来我还有一篇短文:《奇迹没有发生》。在新的世纪,我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但是没有。
现在,我要转换以往的姿态,我不能一例地讲好听的话,我要讲一些我对当前诗歌的批评意见。
首先,新诗过于沉溺于私语状态,有些诗人们总是热衷于自说自话,新诗的多数写作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生活和社会,他们只沉溺于自我,抚摸自我,极端自恋。我们的时代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变幻莫测的,中国的社会正面临非常巨大的转型期,而诗歌写作几乎是与此相游离、相脱节的,有时甚至是对周围的事件无动于衷的。有人听说此语,立即坐不住了,他们要追问:你究竟要诗歌干什么?诗除了抒发性情之外还要它做什么?你是否要诗歌回到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言者无心,听者却有点“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们过去讲文学为政治服务固然不对,那么文学与政治不发生关系就对吗?什么是政治?政治概而言之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诗歌不与它发生关系,就正常吗?
杰出的诗人都是站在他的时代前沿,用自己的诗歌高度概括时代的精神气象,让人们通过诗歌看到时代精神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我常常慨叹唐人了不起,他们的诗有大气象,有大胸襟概括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寻常物事,在他们却别有另一法眼:“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1],“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2],这是何等胸襟!写的是眼前景、心中情,却“无意间”展示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气象。至于杜甫、白居易,至于陆游、辛弃疾,甚至是苏轼、李清照,他们的笔墨从来都没有忽略过社稷安危、民生疾苦。诗人的心,从来都与社会、民生同脉搏,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对于自身的个人的悲欢哀乐的表达。
到了近代中国,列强虎视,国势凌弱,诗歌中充满了救亡图存的呼声,从晚清到民国,诗歌成为时代精神的先导。郭沫若的“女神”概括了五四时代精神,他的《凤凰涅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狂飙精神。艾青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的“太阳”也好,“火把”也好,都是中国人追求光明,把黑暗抛在身后这种精神的象征,表达人民不断抗争、争取民族自由、民族独立的愿望,高度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是特殊年代,即使是那些有点被放大、被虚夸的呼喊或“号召”的政治抒情诗,难道不也是那个时代非常夸张的“激情”的表达吗?贺敬之也好,郭小川也好,他们同样是不可替代的。八十年代的诗人,舒婷这一代诗人,用他们的诗歌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希望。批评舒婷的人说她写的是“小我”,颓废的、软弱的。但她所表达的美丽的忧伤,概括了一代青年的普遍的心理。这就是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希望通过当代的诗能让人看到时代浓缩的影子,一个声称只为“未来”写作而拒绝”“现在”的诗人是可疑的。写个人情感的诗歌,必定要有一个渠道通往大众的心灵,引起大众共鸣。
其次,我关注诗和语言的关系。诗人滥用口语已经把现代诗中残存的诗意荡涤殆尽。语言的美丽以及它的音韵之美,降低到零点。诗是语言的精粹,最美的语言都在诗中,因此诗歌被称为文学的皇冠。写诗的人应该知道每个字、每个词都是要千思万虑考虑出来的。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爱诗,但怕写诗,因为诗对于语言的要求近于苛刻,我深恐我达不到那个高度。而现在的诗歌怎么变得那么容易写了呢?对此我不理解。我们应该大呼一声:赶快停止诗歌语言的鄙俗化和游戏化,让诗歌回到精致、精炼、精美上来。诗绝对不是“到语言为止”,而应是到境界为止,到韵味、胸襟、精神为止。自由,自由,自由,我赞同杨克的意见,诗是最不自由的。
谈到诗歌标准。标准是很难建立的。目下的情况是诗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在没有主潮的时代谈主潮,在没有权威的时代谈权威,在没有标准的时代谈标准,怎么办呢?今天谈标准问题,是因为标准有重新提出的必要,这方面有焦虑。我们正处在焦虑当中。中国历代的诗话,都在试图建立标准,在古典诗歌中,客观的、好诗的标准是有的,例如:境界、性灵、韵味,等等。到了现代诗,因为语言的转换,因为格律的打破,以及彻底的提倡自由体,标准被无形地取消了,诗变成了谁都能写的“玩物”,遮挡是一种极大的误区。重建诗歌的尊严,应当从重新确立诗的标准开始。
我们今天是有好诗的。譬如史铁生《遗物》:“如果清点我的遗物/请别忘记我的老树/我的希望在那儿生长/又在那儿凋零/萌芽、落叶都是/如果清点我的遗物/请别忘记我的那片天空/我的生命从那儿来/又回到那儿去。”他是用生命来写这首诗的,个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诗中得到了深度的提炼。他的语言也是空灵的,在节奏、韵律上是考究的。可见,确实有好诗,但还未被发现。而评论家的任务是阅读、并且发现。
优秀的诗歌是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旗帜和号角,愿中华民族的汉语诗歌精神不朽!
注释
[1] 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2] 贾岛:《忆江上吴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