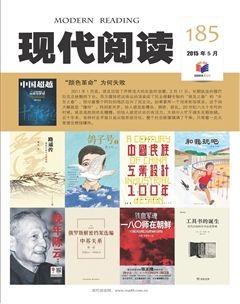大河出龙门
2015-10-21韩振远
韩振远
黄河水在狭窄曲折的晋陕峡谷里一路南行,经过壶口瀑布的飞舞张扬后,南行64公里,来到了峡谷的南端出口——龙门。龙门又称禹门口,两个名字都大气磅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意义却不尽相同。前者将中华文化中最神秘霸气的图腾崇拜与黄河联系在一起,虽然龙是帝王之象征,至少还相对含蓄,形象上与黄河相关。后者则干脆明明白白以帝王之名命名,分明是要超越自然力,表现出人的意志。我更喜欢的是龙门这个名字。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又在晋陕峡谷中盘桓腾跃,恰若一条巨龙受困多时,到了这里,早就急不可耐跃跃欲试破门而出。因而,龙门,分明就是龙腾之门,龙跃之门。
来到龙门,最令人感叹的是山势与河水浑然一体,山的险峻与河的惊涛交映生辉。壶口带给人的是激越,龙门带给人的则是大气。黄河在晋陕峡谷中奔流千里,还没有哪一处将山水结合得如此完美。坐船在龙门行驶,只觉得壁立千仞的河岸好像朝河水拢来,向人头顶压来。大河开始涌动,两岸的山崖也随之涌动,伴随大河行走千里,峡谷好像决心在最后的一段行程中掠去河流的风光,用险峻、奇绝、壁立千仞将狂放桀骜的黄河挤压成一缕。人在河中,便忽略了河水的湍急与汹涌,看到的只有悬崖峭壁造成的大河之门。
即使行驶在河水中,也忘不了山陜之分。龙门两面,一侧是陕西韩城,一侧是山西河津。有如此胜景险关,两地都因龙门而显得格外骄傲。而在龙门两侧,两地也将自己的个性表现得格外分明,山西这边重实际,在峭壁上开出一条公路,名龙虎路,满载煤焦的重型车辆带起尘土隆隆驶来,让大河在功利中颤抖的同时,又给激越的黄河蒙上另外一种色彩。陕西那边重韵致,山崖陡峭得像刀砍斧斫一般,直直插入河中,让游客震撼的同时,又能想到大禹的神力。
河水来到这里,被晋陕两省的山崖紧紧束缚,激起狂傲本性,腾跃咆哮,翻滚奔涌,河水颤抖着,号叫着,激起层层巨浪,又重重摔向谷底。河水好像已然忘情,一起涌动欢呼,簇拥翻腾,跃出龙门。
龙门宽不足40米,是千里黄河最狭窄的地方,自然也是山陕两省离得最近的地方。龙门出口处有两块巨石,早年,两面石上分别建有两座庙宇,供奉的都是大禹,都在用另一种形式向后人讲述大禹凿龙门的故事。两座属于不同省份的庙宇,用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信仰和同一种方式隔河相望,表现出两省共同的文化取向。如今,两座庙早已不存在,一座现代桥梁飞跨东西,桥基正好就在庙址上,不由分说地用这种方式将两省连在了一起。
出了龙门,河谷豁然开朗,两岸的山崖悄然后退,从容向南流淌。
黄河出龙门至潼关这一段,按照水利术语,叫小北干流,全长133公里,流经晋陕两省的2市9县(市)。西岸分别是陕西省渭南市的韩城、合阳、大荔、潼关;东岸分别是山西省运城市的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
这一段也是黄河河谷最宽的一段,有的地方东西两岸相距近20公里,由最窄骤然变为最宽,由最紧束变为最随意,由最激越变为最安详,黄河在一张一弛,一宽一窄之间,创造出了古老的黄河文明。
黄河出龙门不远,就是我的家乡。每次来到这段黄河边,总会被河水的雍容感动。河水在不紧不慢地流淌,泛起一波波水纹,好像根本不在乎什么,也不担心什么,像一位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又成竹在胸的将军,按照自己的节奏,缓辔而行,信马由缰。对岸的山崖远远躲在芦苇后面,在雾霭中露出一丝神秘。从这边看,那个雾濛濛的地方是陕西,从那边看,这个雾霭遮掩的地方是山西,两片古老的土地,被黄河这么一隔,便都化做模糊朦胧的意象,深奥得不可预知。
平静的河水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温文尔雅。出了龙门后,两岸不再是晋陕峡谷那样坚硬的石岸,相对松软的黄土崖远远地躲开黄河,退到远处,给河水让出了宽阔的河道。黄河便有了更多的选择,任性恣肆,自由驰骋,忽东忽西,摇摆不定。河谷中,有时是葱绿的滩涂,有时又是汹涌的河水,有时是绵延不绝的沙洲。一片河滩有时属于河东,有时又属于河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便来自这一段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