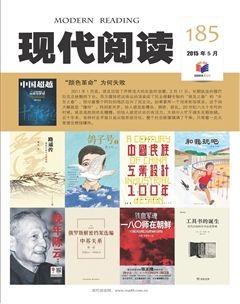莫言小说中带着诱惑与毁灭的少女形象
2015-10-21叶开
叶开
在莫言的很多小说和散文里,都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浮现着“一个”特别的少女形象。这个少女在莫言的笔下幻化成了许多种人物形象,似乎都是他的“初恋”对象。“她”就像一头神秘的小兽,出没在高密的丛林里、田野间,给目见者以欣喜,让错失的人倍感惆怅。作为高密东北乡王国的自封国王,莫言身兼目见者与错失者两个角色。他的叙述是一种悲喜交加的情感。
莫言小说里最早出现“超级”少女形象的,是创作于1984年10月的短篇小说《石磨》。
《石磨》里,少女“珠子”是“我”的邻居,青梅竹马,从小打打闹闹一起上学,一起拉磨,一起慢慢长大。到了青春期,两个人好上了,“我”父亲却不允许。小说接着牵出一桩悬案:珠子的母亲四大娘和“我”父亲曾青梅竹马,自由恋爱得死去活来,后来虽然各自成立了家庭,关系仍然很暧昧,珠子很可能是“我”的亲妹妹。小说在这里出现了多种可能性走向。其一是“我”父亲和四大娘的孽债未了,珠子果然跟“我”有血缘关系,于是“我”和珠子的爱情化为泡影。这是悲剧的写法。莫言那时比较仁慈,也比较人性,一仁慈一人性,就把父亲和四大娘的爱情给生生化没了——他们必须给将要得到幸福的“我”和珠子让路——莫言必须证明他们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为珠子和“我”的血缘障碍清出道路,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了人见人爱的女儿。在这部小说里,悲剧性的因素被放大之前就及时地消除了,留下一个美好的尾巴。美好的少女美好的结局,这是传统写法——其中隐约看到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多情少年段誉和几位“妹妹”的故事。
小说里那种略带一点悬念的叙述,在莫言小说里比较罕见。美好的爱情和美好的故事在莫言的小说里,就此打住了。莫言后来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有浓重悲剧色彩。
与《石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短篇小说《枯河》。
《石磨》里,少女珠子给“我”带来了幸福,《枯河》里,少女小珍却给“我”带来了厄运。《枯河》的故事来源于莫言自己的亲身经历。莫言把这段经历中相对美好的部分写成了《透明的红萝卜》;悲惨的部分写成了《枯河》。作家和故事的分裂,是写作的秘密之一。
在《欢乐》这部中篇里,莫言语言如网如织,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因此而受到种种误读与误解。女主角之一的“冬尼娅”取代了路遥小说《人生》里的“薄情寡义”的城里姑娘黄亚萍,给予农民之子齐文栋以粉碎性打击:《人生》可以从道德上谴责黄亚萍的轻浮和薄情,《欢乐》却失去了这种道德评判基点。因此,齐文栋是彻底的被拋弃者,是孤独的绝望者——没人给莫言以可以成立的道德支点,更没有一根称手杠杆,可以让他撬起齐文栋的卑贱人生。对他施加最后一棒的人,是有着精美名字的“冬尼娅”。“冬尼娅”这个名字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走出来,变成了一个精妙的隐喻。对齐文栋而言,当美好的人儿如“冬尼娅”,她跟权力和不公有意或者无意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其杀伤力也是致命的。小说里,农村女子鱼翠翠的惨死和城市女子“冬尼娅”的“飞扬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莫言深刻地揭示了横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现代阶级鸿沟,是怎样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的。
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农村青年高马和农村少女金菊的爱情以悲剧告终:高马被抓捕关押,金菊怀着一个即将临盆的婴儿吊死在门框上——那个令人压抑的场景有着深刻的震撼力。
《枯河》里少女小珍是书记的女儿,身份无比贵重。她指使小虎爬到树上,小虎就乖乖爬到树上。小虎从树上摔了下来,把小珍砸倒了,砸伤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件,小孩子之间在相互玩耍经常会发生,却因為小虎父亲的上中农的卑微身份,使得这个小事件演变成了一次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莫言戏仿了旧电影里“反动派”对“革命义士”上刑的经典场景,使得这一场拷打失去了正当性。本来是美好的小人儿小珍,给小虎带来了致命的厄运。
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通过黑孩的视角,在石匠、铁匠和菊子之间,温婉地进行叙述,并且通过对美好景象的通感表达,掩盖了小男孩遭到痛打的事实——黑孩所遭受到的迫害,事实上远不如小虎。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还保留了一种描写美好事物、并将这种美好事物结合到人物命运里去的传统愿望。比如,小说在写黑孩拔起红萝卜时,对金色的红萝卜进行了诗情画意的抒情。黑孩眼睛里看到的少女菊子,却对他造成了震撼。菊子以失去一只眼睛的代价,在小石匠和小铁匠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性的解脱。这种对美好进行摧残的手法,即让少女菊子失去一只眼睛的“恶劣行径”,早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莫言就对少女“暧”实施过了。失去了一只眼睛,美少女就成了残废,美女就成了丑女——这种惊人的转换,被莫言细腻地发现了。在乡村里,瞎眼、哑巴、瘸腿等,都是遭到鄙视和唾弃的对象,无论你之前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高贵。“暖”因为瞎了一只眼睛,而不得不嫁给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哑巴。这使得原来的崇拜者,后来衣锦还乡的叙事者“我”——某军校的教官——备受压抑的精神获得了解脱,而在无形中拥有了怜悯者的道德优势。这种心态是不正常的。军官的痛惜和怜悯,建立在了“暖”的不幸之上。
可以看到,莫言对少年时期的少女形象有一种犹犹豫豫的暧昧态度。少女既可能带来幸福,也会招致厄运。少女自身也会遭受不幸,从而填平了“我”和少女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莫言小说里,除了《石磨》里的“珠子”之外,乡村少女都没有幸福的人生。得到幸福人生的,都是“干部”子女。
最让莫言感到畏惧的,显然是小珍这种干部后代的少女。
少女是一种特别的动物,是美好的集大成者。在散文《世上什么气味最美好》里,莫言借谈论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长篇小说《香水》的机会,把这种对少女的敬畏表达了出来:“科学家说,自然界大概有四十万种气味,好闻的和不好闻的各占一半,而在这二十万种好闻的气味中,最高贵、最难合成的,是少女的气味。这是一种鲜嫩如花的气味,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气味,这是一种生命青春的气味,这是一种象征着世界未来的气味。”
《香水》里的邪恶天才格雷诺耶出身卑微,天生而具有超级敏锐的嗅觉,能够分辨十万种不同的气味。他自己却没有气味。格雷诺耶认为香水能够支配人的情感,进而支配人的意志和灵魂。他潜心山林修炼七年之后,下山杀死了二十五个妙龄少女,用独特方法萃取她们的气味,制成世间最奇异最有魔力的香水——无论什么人一嗅到这香水的气味,爱心就会像大海一样泛滥,就会对香水的拥有者疯狂地顶礼膜拜。这样,格雷诺耶就能毫不怜悯地驱使他们,驱使他们残酷杀戮而统治世界。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小说的精妙结局:汹涌的爱让人疯狂,也产生致命毁灭——那些无限热爱他的人蜂拥而至,崇拜他,占有他,把他撕成了碎片。最美好的东西因此具有两面性:诱惑力和毁灭性。
莫言对少女的美和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摄人心魄的美好气味是有敬畏的。他在文章中不无冷酷地继续说:“少女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她一旦长大成人,就如鲜花盛开,而盛开的鲜花总是在放出浓香的同时也放出衰败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