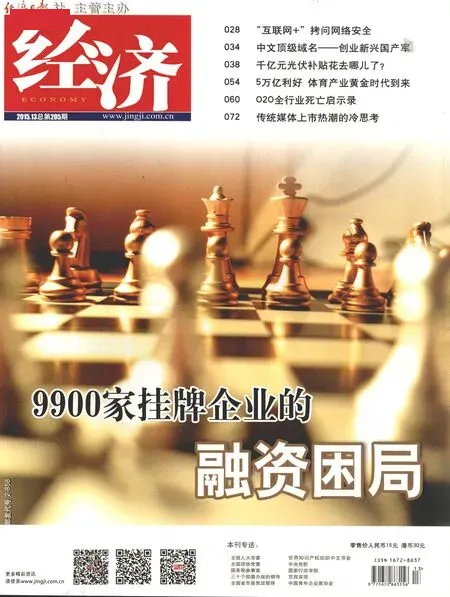一个孤独到极致的故事
——《心是孤独的猎手》
2015-10-21刘稚亚
文/本刊记者 刘稚亚
一个孤独到极致的故事
——《心是孤独的猎手》
文/本刊记者刘稚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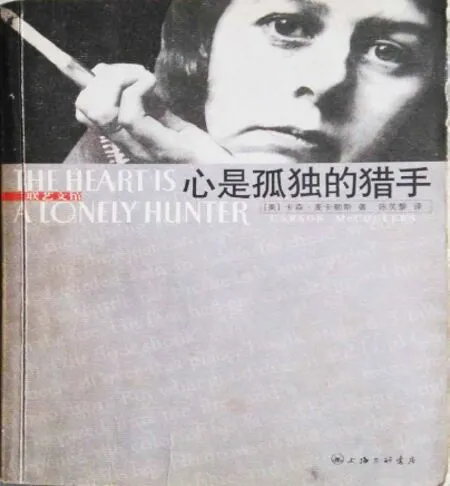
孤独的人就像哑巴,悲天悯人地看着喧闹的世界,看着那些一张一合的嘴巴。形形色色的面庞,看起来平静安详,内心却始终不安地在翻滚着。
上学的时候连上厕所都需要人陪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很害怕孤独。可是,当我终于可以做到一个人去医院挂两个小时水再旁若无人地连续吃3个小时火锅以后,似乎孤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一个人待着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观察身边的人,猜测周围发生的事,听觉和嗅觉都变得比以往更敏锐。把眼妆哭花的女孩,暴露着赘肉的大妈,偷瞄美女胸部的大叔,戴着耳机的叛逆少年……都曾是我饶有兴致的观察对象。
当然了,“孤独”对我来说,只是忙碌生活的调味剂而已,平日的生活被大量信息充斥绑架着,能把自己塞进一个封闭的套子里竟成为了一种可以享受的逃避。毕竟,怎么逃都逃不离这个城市,怎么躲都躲不开手机。
可是如果生活里只剩下孤独呢?
22岁的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就是如此。
1917年出生于佐治亚州哥伦布的她,一生备受病痛折磨,经历过3次中风之后,29岁就瘫痪在床,与疾病和孤独挣扎了50年之后,1967年她病逝于纽约。《心是孤独的猎手》是她22岁的作品。
美国南方的小镇,漫长沉闷的八月,一个总是温和微笑的哑巴辛格。这就是整本书的全部。任由酒吧里的喧闹沸腾,共产党萌芽带来的启蒙动荡,对纳粹的忿恨抱怨……他始终一言不发,对每一个人都微笑,永远都不会有情绪的起伏。
因为他是孤独的,他不在乎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个看起来懦弱却对白人充满怨恨的黑人医生,那个浑浑噩噩的“纽约咖啡店”老板……在辛格看来,每个人都太忙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是他们的脑子里装着太多事了,让他们无法休息……我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人可以这样不知疲倦地动嘴皮子。”辛格写信给安东尼帕罗斯,哑巴,他唯一的朋友,却不识字。
可是安静温和始终一言不发的他在安东尼帕罗斯面前却充满激情,他疯狂快速地打着手语,他分享着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尽管他的朋友是个智力低下的痴呆儿,可是辛格觉得他能懂。
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不懂”才让辛格的孤独有了发泄的出口。正如辛格的沉默让所有人都把他当做倾诉的对象——还有谁比一个哑巴更懂得保密呢?这和自言自语又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前者却可以得到若有若无的呼应(你也可以把这份呼应想象成对自己的理解和赞成)。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完美的想象体存在,只是大多数人无法把它具体化。有的人误以为是多年前丧失的一段感情,有的人沉醉于工作和创作,因此辛格这样的完美存在满足了多少人对孤独的释放——他们把辛格想象成了自己,那个自己永远达不到的完美高度。
“……她喜欢音乐。我希望我知道她听得到什么。她知道我是聋子,却以为我懂音乐……”辛格继续抱怨道。每个人都是这样,他们认为辛格是最懂自己的人,他们不在乎辛格是不是听得懂。
辛格最后还是死了。自杀。因为安东尼帕罗斯死了,陪伴着他的,唯一的朋友死了。这就像一条食物链,全镇人的感情寄托在一名哑巴,而这个哑巴的感情寄托是一个痴呆,这个痴呆的感情寄托却只是一杯杜松子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