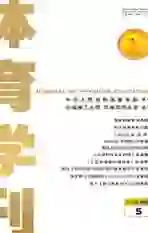竞技非此即彼
2015-10-20刘欣然余晓玲
刘欣然 余晓玲
摘 要:词源学中得出游戏概念的分离,并不能作为定义竞技概念的基础,玩耍和游戏都不具备定义竞技概念的优先性。同时,游戏意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随意性,在对“游戏”概念区分过程中,被再次得到证明,游戏不是竞技最合适的属概念。游戏概念“此与彼”之内的分辨,解构游戏本身却没能使竞技获得概念上的建构;而游戏概念之外的甄选,才是解决竞技概念不清的理性道路,技艺在竞技定义中更具优先性。中西语境的差异,使得游戏概念模糊、晦涩且多义,竞技本质非游戏论、竞技本质技艺论,是竞技在逻辑定义中得出的结论。
关 键 词:体育哲学;本体论;竞技;技艺;游戏;玩耍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5-0011-06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ame derived from etymology cant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athletics, while both play and game are not provided with the priority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athletics. In the mean time, the complexity, variability and randomness of game meanings are proven again in the process of distinguishing the concept of “game”, hence game is not the most appropriate generic concept of athletics. Distinguishing the concept of game within this and that, and deconstructing the game itself, failed to enable athletics to be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concept; while screening beyond the concept of game is really the rational way to resolve the 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of athletics, and skill is provided with more priority in the definition of athletics.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 make the concept of game ambiguous, obscure and multivocal, 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athletics being not game, and 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athletics being skill, ar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logical definition of athletics.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ontology;athletics;skill;game;play
学术不争不明,问题不辩不清。陈璐等[1]以论文《此游戏论非彼游戏论》(以下简称“陈文”)与我商榷,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思想交锋,我有回应的必要。《竞技本质非游戏论》[2](以下简称“刘文”)主要观点是排除“游戏”在定义“竞技”概念时,本质不清内涵空洞的干扰,使“竞技”引向确定的“技艺”知识领域,从而建立起竞技概念的本质内涵和感性外观。“陈文”认为在游戏概念之中,应该区分play和game的内涵,并试图寻找“竞技”与两者之间的联系。对比发现“刘文”立足于本质主义的立场,寻找到“游戏”不可定义的证据,并重新建立“竞技”概念的定义路径和基础;而“陈文”从词源学或语言学的视角,证明“游戏”耐人寻味的多样性,而主张与“玩耍”概念的区分,从而导致“游戏”虚无泛化概念的不证自明。“刘文”以本质主义为据,关注“竞技”概念的本质内涵;而“陈文”以语义词源为证,重视“游戏”含义的内容区分,立场不一这自然导致“陈文”深陷“关公何以战秦琼”的自问之中。寻找“竞技”本质内涵,在“游戏”和“技艺”中必然是“非此即彼”[3],据此作出回应。
1 基本观点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索,会以“某某是什么”的形式出现,这一符号性的解问形式,涉及到事物的普遍性(共相)问题,成为人类认识的首要思考方式。对于“竞技”是什么?“刘文”的观点是“非游戏”乃是“技艺”,而陈文的观点是“游戏”,并用“此游戏和彼游戏”来进行说明。
“刘文”的主要观点:1)“游戏”是人的活动天性和本能,“竞技”是人的运动传习和经验;2)本质主义立场寻找“竞技”的本质,而反本质主义正好借语言描述拆解“游戏”的本质;3)“游戏”的目的在于内在性的呈现,而“竞技”的目的在于外在性的表现;4)“竞技”在于身体行为的实践;而“游戏”在文化中走向易变多义;5)竞技是身体性运动竞争的技艺。从中可以看出,“游戏”和“竞技”存在着某些不一样的特征,使得本质上两者能够得到区分,重新建立“竞技”的概念,会对“竞技”在知识体系上的建构有所帮助。
“陈文”的主要立场:1) play和game应该分别翻译为“玩耍”和“游戏”;2)动物可以play,而只有人能game;3)在游戏理论中应该区分玩耍(play)和游戏(game)的含义;4)玩耍(play)在西方学者中的定义应该被重视;5)竞技是身体活动性游戏。综合以上观点,使“游戏”囿于自身的概念之中,并进行含义支解,导致本身混乱的“游戏”概念,又增加了易变的证据,使得定义的基础更不牢固。
不论从篇章结构、陈述观点,还是论述立场、引证文献,两篇文章都存在差异,同时,本体论和词源学立场上的不同,也使得两文探讨的重点不一致。但是,唯一的观点交锋在于对“游戏”的本质认识,也是“陈文”所质疑的重点,即:游戏是什么?并寻找凯洛易和爱德华的定义进行论述。通过词语流变中play和game的不同含义,证实中文翻译的不合理和两个概念混用的状况,以期达到对“游戏”概念的确认。但是,事实上却将“游戏”定义引向多样性、易变性和随意性的领域,殊不知“语言存在着两不性”[4],即不能证明事物本体的存在和不存在,它只是认识事物和表达思维的工具,是一个旁观者。在后现代分析哲学的影响下,语言哲学试图解构本体,但在此过程中其解释的对象又形成新的本体。因此,语言翻译中得不到事物的本质,必须回到本体论的定义方法中,寻找“竞技”的应有之义。
2 概念定义
在“竞技是什么?”的问句中,“竞技”与“什么”之间是等值的,并且互换位置后其意义保持不变,“什么”成为了定义寻找的重点。于是,“属”概念被提了出来,在“什么”的全部意义之中,“属是定义中的首要部分”[5]。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6]进一步解释道:“属的属差不是偶性,属、种和属差,作为宾词,对于它们的主体是‘一义的。”属比种更真实接近定义项,属在定义的构成中更具普遍性。
“陈文”认为:“玩耍、游戏和竞技都是一些自明的概念”,并借用爱德华的观点来论证。玩耍是“自愿参与明显不同的活动,活动在任意的时间和空间领域中进行,与日常生活的角色、关心的事项、影响相隔离,对于参与者来说除了沉浸在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之外具有非严肃性、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的特征”[7]。从爱德华的观点表述中,发现了对“游戏”定义无序、混乱和不规范的特征。根据“属加种差”的定义原则进行检验,发现:1)本质属性不清,对于“活动”含义范围没有清晰表述;2)定义过宽且不能表达固有属性;3)语言晦涩、歧义,如明显不同、关心的事项、任意的时空领域;4)基本特征中无一肯定用语,如:非严肃性、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这一定义全面违反了“属加种差”的原则,将“游戏”抛弃在生活之外,如果用以定义“竞技”只能是虚无主义盛行,混乱、混淆和混沌蔓延,无法使“竞技”进入人类价值生活的中心领域。
同时,在凯洛易[8]的定义“玩耍是一种自由、与日常生活分离、不确定性、非生产性、由规则控制并且虚拟性的活动。”其中,也同样出现本质属性不清、定义过宽、否定用语过多的问题。难道“竞技”真与日常生活分离,不是生活的一部分?“竞技”中的非生产性如何体现?“竞技”是否真存在虚拟的空间?不确定性是在“竞技”之内还是“竞技”之外?
胡伊青加[9]深刻认识到“游戏”的复杂性,定义时十分小心慎重,认为:“游戏是生命的一种功能,但却不可从逻辑上、生物学上或美学上加以准确界定。游戏概念必须总是有别于我们借以表述精神与社会生活结构的一切其他思想形式。”从中感受到“游戏”问题的多样化、随意性和复杂性的倾向,在对游戏问题的阐述中,几乎都是从语言、现象、功能和特征上进行描述,将“游戏”设置在人类文化生活领域,揭示“人与游戏”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竞技”定义也需要保持这种谨慎的态度。
3 此与彼的观点
此(this),是这个、这里的意思;彼(that),指那个、那里的涵义。两个词经常连用为:此起彼伏、厚此薄彼、此生彼世、非此即彼等。海德格尔[10]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用以表明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此在”成为生存论结构中的重要环节。在此意义中,“人的竞技”就是“此在”中对于存在论的解释,而对“游戏”的认识则成为这一结构的方案选择。在“此与彼”的观点中,“陈文”显然是“play和game”之间的区别,而“刘文”集中在“游戏和技艺”之中的区分。这一论争,无疑赋予了“此与彼”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在游戏之内;一种在游戏之外。
3.1 此游戏之内
“陈文”注意到,在英文中“游戏”有两种表达方式,“玩耍”(play)和“游戏”(game),并认为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视野”。这样就至少出现了“三游戏说”:1)游戏(play+game);2)玩耍(play);3)游戏(game),“游戏”在概念上出现分离,那现象上的多样性、无序性和随意性就显得更无法琢磨。
“陈文”所倡导的“游戏”区分:1)没能证明“竞技”与“游戏”本质上的联系;2)陷入“游戏”概念泛化的现实之中;3)未能找“游戏”自身共有的本质依据;4)“游戏”概念上的支解必然导致现象上的分离;5)在中国人的语义中,“游戏”真有区分的必要吗?在这一系列的论证中,都没能得出“游戏”在“竞技”概念中的首要性,其固有属性必定不在语言翻译的错误语境之中。
因为,语言自身就具备与表述对象随意性的特点,语言描述本身只是一项工具性的活动,与事物本质没有必然、首要和决定性的联系。所以,语言表达的新奇,可能源于任何的思想形式,在创设的环境发生改变时,语言也在变化,新语言就产生于随意之中,如:正能量、点赞、悲催、拍砖、酱紫、坑爹、土豪、女汉子等。而“语言游戏”恰恰又证明了这一特点,于是,维特根斯坦[11]就利用“语言游戏的家族相似”的观点,建构起反本质主义的立论依据,“语言”和“游戏”都被认为是无本质的东西。在“游戏”的前缀任何词语,这个语言等式都是成立的,如同猜谜、打斗、情感、行为、数字、欺骗、思维、本能、表演等。这必然导致,你无法说清楚体育游戏、竞技游戏、休闲游戏与数字游戏、欺骗游戏、杀人游戏等的本质区别,它们被混合成“游戏”概念泛化的不可知物。
作为一种方案,将英文“play”翻译成“玩耍”,“game”翻译成“游戏”,也无法对应中文“游戏”的真正内涵,反而导致语义的重复混用,“game”中体现不出“游戏”的普遍性,因此,只能用奥卡姆的剃刀“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将其剔除。在现实生活中,区分“游戏”现象内“play、game”的具体形式,本身就存在模糊性,而要将这种模糊性放置到“竞技”中,必然导致本质不清。将“游戏”拆解成“玩耍”、“娱乐”、“嬉戏”、“消遣”等,最终的结果是游离于真正寻找的“竞技”本质之外。在概念定义中,“竞技”到底是“玩耍”还是“游戏”?理解“竞技”的真正基础何来?在“玩耍”和“游戏”中如何区分“竞技”本质?这种对“游戏”概念的区分,难道不是概念混乱的进一步加剧和延续。
3.2 彼游戏之外
不可否认,“陈文”关注英语“游戏”概念“play和game”的区别,对于研究“游戏”本质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定义“竞技”时却会显示出相反的效果。同时,没能真正理解胡伊青加用荷兰语(属日尔曼语族)所表达出的“游戏整体观”,和“游戏”在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意义。胡伊青加认为“游戏”在生活中所反映出的现象、性质和功能才是根本的、首要的任务,其文化表现才是主要的研究重点。
同时,“陈文”也没有发现“刘文”所持的“游戏整体观”立场,并利用“游戏”之分离进行争辩。在游戏整体观中,“游戏可能是体育起源的一种解释,但是‘游戏却不能解释为‘体育,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反映在社会属性之中”[12]。从中传递出,“游戏”和“体育”在现象上联系,本质上区别的观点。“游戏”和“竞技”并非没有联系,但是作为定义“竞技”的基础,“游戏”显然不是最合适的属概念。因为,“游戏”(play和game)不具备在定义“竞技”概念中的优先性,自身却表现出不稳定、不准确和不一致的特点。
而“陈文”将“游戏”概念由一元统一,变成二元对立或多元分化,将“游戏”解构为:game、play或play+game,使得“游戏”自身立场随意分解,定义的基础也同时被解构。概念不同,必然导致方向性的差异,使得真正的本质无法显现。因为,“如果语言要成为可能,我们就得指向对象、辨认对象才行”[13]。这已经提醒我们,在辨认“竞技”时,到底是“play”或“game”,毕竟“陈文”在“游戏”中显现出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导致在本体论意义上,“竞技”概念无法在“游戏”中得到证实。
在现实的生活中,“游戏”的意义实在是太过泛化,就连生活、文化、思想和存在都是游戏的范畴,并且,语言交流中的随意运用,用来定义“实体”的概念实在不可取,因此,在定义“竞技”概念时就显得无意义了。如同经常在语言中运用到:竞技是生活、是文化、是知识、是运动、是游戏等,但表述概念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游戏性只是“竞技”的内在功能之一,如同:竞争性、目的性、观赏性、娱乐性、主动性、功利性等,游戏性在“竞技”中并非首要特征。
无论是“此游戏”还是“彼游戏”都未能跳出“游戏”固有思维局限,“游戏”概念自身的混淆和双重定义,必然导致定义“竞技”时无立场的出现。因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语言是趋向于使用逐渐简化的过程,而将“play和game”在“游戏”定义上的区分,必然导致概念运用上的混乱。在定义“竞技”时,我们关注“游戏与技艺”之间的“是与非”,而不是游戏之内的“此与彼”。
4 是与非的认识
4.1 “竞技”非动物性
“陈文”认为“动物可以play,唯有人game”,“游戏”被分割成两个部分,难道人真不可以“play”吗?在“竞技”中,又适用于“游戏”的哪个部分?这显然是不可取的。“竞技”必定是人的实践活动,而动物不“竞技”只“游戏”,“陈文”自然注意到这一点,并以此为据证明“play和game”之间的疏离。但却并不能为“竞技是游戏”提供更多的证据,反倒是将“游戏”概念拆解。同时,“竞技”却与“play和game”在现实中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运动项目和赛会名称中词语运用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动物可以play,唯有人game”必定是假命题。在“游戏”概念中,所显示出的动物性,并不能证明“竞技是游戏”,而“竞技”非动物性特征,却能在“技艺”的概念中反映出来。
4.2 “竞技”非随意性
“游戏”中体现出随意性、非生产性和无目的性的特征来,“游戏”只局限在自我的价值空间中,在自身中证明并完结。而“竞技”却是人有目的、严肃和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它需要追求人性的完善、生命的卓越和能力的塑造,在体力竞争中获得尊重、敬仰和荣誉。古里奥尼斯[14]谈到:“体育的意思是使身体变得出众的努力行为,倡导有道德、有尊严、完全尊重对手的比赛方式。游戏的意思也是使身体出众的努力行为,但是方式充满伪装、狡诈、虚伪、谎言和讽刺。”从中感受到,在社会生活中“游戏”不严肃、不正经和世俗的文化品质,而“竞技”却始终置于高尚、德行、荣耀和显赫的文化氛围之中,成为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竞技”本质动因在于竞争获胜、追求最佳成绩和体现极限能力。而这一些特性是“游戏”所不具备的,“游戏”中不必体现最佳的竞技水平,只需要在“游戏”获得乐趣、戏谑和玩笑而已。“竞技”不是随意的活动,并非存在于虚拟的空间之中,而是人生命力价值的自我确认。
4.3 “竞技”非虚拟性
“游戏”在特定的空间进行,并且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虚构出欢喜、游离的场景,实现某种精神的愉悦,当“游戏”结束后似乎“游戏”并未发生过,“游戏”在自身中得到完结。而“竞技”带来胜利和失败,追求荣誉、释放力量、获得尊重、赢得赞美,当“竞技”结束之后,现实生活中依旧回荡“竞技”时的景象,并且可能因此获得永恒的声誉,“竞技”中体现出极限能力。因此,“竞技”不可能存在于虚拟的空间之中,它是跨时空的因素,无法在自身中获得完结,并且还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持续的影响效力。没有人会认为运动员艰苦的竞技训练,是无目的、无意义和非生产性的事情,花十年或十几年的时间进行艰苦训练,难道是在“玩耍”或是“游戏”。在现实生活中,“竞技”已然成为了一项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体质、群众的休闲、身体的教育都是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而非是在“游戏”中度过光景。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玩耍的游戏,而是“体育人”的工作和事业,它不存在于虚拟的场景和空间之中,而应该是我们共有的价值存在。
综上认为“竞技”本质非游戏。因为,“竞技”和“游戏”本身具备两种不同的特性,“游戏是天性,是先天具备的能力;竞技是习惯,是后天练习的结果”[15]。“竞技”不依靠艰苦、持久的身体训练、思想锻造和技能磨练,是无法战胜对手并获得竞赛的优胜,因此,竞技更多地体现出“技艺”的品质,“竞技本质技艺论”才是对抗“游戏论”的真正观点。
5 竞技是技艺
“竞技是什么?”是体育哲学基础问题。“竞技”来源于人的实践改造活动,是人与自然对抗的本能武器,并通过后天的模仿、学习、训练和锻造,获得身体力量的充盈、技能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竞技”中体现出一种实践知识的特征。
5.1 技艺的知识
技艺作为一种制作、生成和创造的力量,是人在应对自然挑战的实践路途中,所总结出来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技艺”就是重要的概念,被运用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之中,“技艺”给予实践者(主体)以能动的权力和力量,在生活总体之上关怀人本身。“技艺”成为人主动性、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的始因,它不是无原则、无秩序的行动,而是实践理性所归纳的价值尺度。“技艺是在有所知的产-出的意义上的制造与建造”[16]。“技艺”其意义不是简单的技能、技术和艺术,而是一种“知”,是对存在事物有计划的安排、支配和把握的能力,它存在于较高的认识领域之中。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将“技艺”放置在经验与智慧之间的求知层次,为经验思考,为智慧实践。“技艺”作为一种普遍的概念,成为人行动的价值准则、道德标准和理论依托,规范着人的实践活动,成为探索自然、把握世界和理解存在的知识力量。
5.2 竞技的领域
“竞技”存在于人实践领域,是实践理性的知识范畴。它展现出一种生成的力量,从潜在到显在、模仿到持有、运用到创造,人身体的本原能力成为这种生成的独特解释。“竞技”规划着行动的能力,并通过技能、技术的经验形式给储存下来,成为规约人主体存在的生存方式,“竞技”中体现出实践知识的属性。1)生命起源的竞争,“竞技”中所固有的竞争性,就来源于物种之间的生存竞赛,对抗、竞争和比拼是基本的能力展示;2)原始自然的改造,人身体本原的能力是对抗自然的唯一武器,“竞技”就在实践改造之中应运而生;3)社会进程的炫耀,当战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时,“竞技”自然成为了第二选择,勇气、力量和肉身素质成为一种张扬的闪现;4)文明生活的保存,对抗静态文明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动态的“竞技”,人类种群的野化活动,“竞技”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以上表明,“竞技”是实践理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竞技”存在于实践知识的领域中。
5.3 竞技的本质
“竞技”不是随意性的玩耍、无目的性的游戏和怡然自得的休闲,它本质中体现出一种生成的能力,使人保有一种对抗的勇气、决斗的气质和进取的品格,是生命力所造就出独特的文化关怀。“竞技”是生命活动的必需,它归属于实践知识之中,是关乎行动的技艺。在知识普遍性的认识之中,“技艺成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认识标准,规范和引导着人类的现实生活和行动方向”[17]。技艺成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准确把握着实践知识的存在价值。“竞技”是后天的行为能力,是在实践训练中获得的技艺品行,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技能学习过程,是经验总结、实践累积和技巧演练的知识,它存在于技艺的知识架构之中。“竞技”普遍性的本质、知识的结构和存在的价值,都能够在技艺所属的范畴中得到彰显和证明,技艺使“竞技”获得了知识认可的存在空间。技艺规定着“竞技”的本质。
在寻找到“竞技”的属概念之后,需要进一步确定“竞技”概念之中的几个特定因素,以便获得临近的种差。在规定“竞技”意义中,“身体性”必须首先得到确认,这是行动的主体、实践的对象和存在的前提;“运动性”是世间万物普遍存在的规律,是“竞技”活动的动力来源,扮演着驱动者的角色,成为“竞技”存在的普遍形式;“竞争性”是差异性的体现,是获得超越的本质动因,于是,极限能力和最佳成绩才能获取,竞争使“竞技”意义突显。从中,身体是基础和前提,运动是动因和目的,竞争是价值和意义,技艺是本质和范畴,“竞技”获得概念形成中的思想根据。
综上可认为“竞技是人身体性运动竞争的技艺”。
“竞技”非此即彼。“竞技”是正经的工作和事业,在“游戏”和“技艺”的选择之间,“技艺”显然是“竞技”最合适的属概念。而“游戏论”则是一直困扰学术界根本问题,这一观点直接导致体育现象之间出现交错、繁杂、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正是因为“游戏性”的羁绊,在学校体育中,快乐体育思想是无法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益,导致学生素质30年来持续下滑;在竞技体育中,假球、黑哨和兴奋剂将体育沦为了一场场闹剧和表演;在群众体育中,与工作无关的随意使体育变成为退休体育、广场舞和饭后休闲。人们看待体育的视角出现了偏差,这很可能就是受游戏性思想干扰的结果。亚里士多德[18]认为:“幸福决不在游戏中。”“游戏”被认为是不正经、不务正业和低俗的象征,这直接导致神圣、纯洁和高尚的“竞技”精神,被认为是世俗、无用和低贱的玩意了。
“竞技”本质不在“游戏”或“玩耍”之中。“刘文”认为是“技艺与游戏”的本质之争,而“陈文”倡导的是“play和game”的地位之辩。“身体活动性游戏”到底是“play”、“game”、“play+game”,还是两者的综合物、交叉物,“陈文”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但是,没有人会将“竞技”这种艰苦训练、磨砺和锻造,认为是通向“游戏”精神的实践过程。“竞技”是“种”的能力,和“类”的品质,除非我们不需要“竞技”作为生命的保护,而另有“他者”能够替代这种社会功能,不需要“竞技”中的体求完善、寻求超越、追求卓越的精神。“竞技”是国家、民族和种类的事业,如果继续“游戏”下去,可怕的素质下滑、体质下降、体能衰减、体力不济,将会让“中国人”的勇力、气质和野性无迹可寻。
综上认为,“游戏”之内的“play和game”,是无法真正寻找到“竞技”的本质,“竞技”的本质不在“游戏”之中,“竞技”本质在于“技艺”所规定的知识系统之内,“竞技本质是技艺”。
参考文献:
[1] 陈璐,张强,陈帅. 此游戏论非彼游戏论——就《竞技本质非游戏论》与刘欣然老师商榷[J]. 体育学刊,2014,21(3):8-12.
[2] 刘欣然,余晓玲. 竞技本质非“游戏论”——就本质主义立场与军献兄商榷[J]. 体育学刊,2011,18(3):7-13.
[3] 克尔凯郭尔. 非此即彼:一个生命的残片(上)[M].京不特,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5.
[4] 张志扬. 偶在论的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
[5] 奥卡姆. 逻辑大全[M]. 王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9.
[6]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解释篇[M]. 方书春,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3-19.
[7] Harry Edwards. Sociology of sport[M]. Home-wood,Ⅰ11:Dorsey,1973:90.
[8] Roger Caillois. Man,play and games[M].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1:4.
[9] 约翰·胡伊青加. 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 成穷,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7.
[10]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4.
[11]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7.
[12] 刘欣然,李亮. 游戏的体育:胡伊青加文化游戏论的体育哲学线索[J]. 体育科学,2010,30(4):69-76.
[13] 希尔贝克,伊耶.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 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2.
[14] 塞莫斯·古里奥尼斯. 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沈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41.
[15] 刘欣然,张学衡. 基于游戏理论的体育哲学考察[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4):39-34.
[16]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
[17] 刘欣然. 生命行为的存在——体育哲学、历史与文化的线索[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306.
[18]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