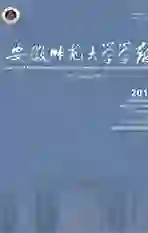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日占区问题再探
2015-10-17周峰
关键词: 抗日战争;受降;接收;新政治史
摘要: 受降与接收日占区是抗战胜利后的重大事件,也应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新政治史视角下,运用政治史、社会史等研究方法,可以看出:国民党接收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从根本上说是由组织制度的混乱所造成的,恰恰是其弱势独裁的表征;普通民众在胜利幻象中的不幸遭遇,激发了对国民党的失望和不满;由于国力微弱,国共的受降之争乃至战后中国的政治态势,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缘政治和强国政治斗争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5062209
受降与接收日占区是抗战胜利后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关系到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影响深远。由于受降与接收在时间上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间,因此并不为抗战研究或解放战争研究的重点。可以说,对受降与接收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称。①为此,史学界发出了“努力填补‘中国战区受降研究空白点”的呼吁。②
学者已注意到,与其将受降与接收纳入抗战史研究的终点与后续研究范畴,不如将其视为“内战的开始”③,进而从
政治而非军事的角度考察其对战后中国政治走向
的重要影响。从“终点”到“开始”,尽管这一
历史事件本身并无实质性变化,但却大大拓展了
研究者的视域和思路,我们有必要将这一“事件”置于更加宏阔复
杂的深层的长时段历史来考察。所谓“历史思
收稿日期: 20150603;修回日期: 20150811
作者简介: 周峰(1982),男,江苏溧阳人,博士生,讲师,编辑,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①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共的受降之争、国民党接收工作中的腐败及其对经济稳定造成的恶劣影响,研究内容之新意略显不足。汪朝光的《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也有少量的研究成果涉及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如张盛发的《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②路育松、吴楠:《努力填补“中国战区受降”研究空白点——“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胜利 69 周年专家学者座谈会”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2日。然而,这一呼吁仍是针对受降作为一个“事件”的历史研究而言的。
③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维”,绝不仅仅
是对过去的事实重建和简单叙述,而是基于历史并面向未来的思想重建。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战后受降和接收日占区为切入点和研究路径,通过“事件路径”的历史,试图挖掘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局势”和“结构”,从而实现“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
接收乱象:弱势独裁之表征
以往研究成果述及国民党接收乱象之缘由,皆由“腐败”一言蔽之。这一颇富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从其他角度深层探讨这一问题的路径,从而错失历史的细部真实和复杂面貌。9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六组。委员及各组负责人,均由各有关机关的代表担任。同时,各战区、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党政接收委员会,受中国陆军总司令及本地区受降主管之指挥监督。
为扭转这一局面,1945年10月,经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由此,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归“陆总”外,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划归行政院负责。各省市、地区亦相应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从12月起,原“陆总”下设的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及下属各省市和战区接收委员会相继撤销。行政院随即制定了《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各级机关接收职权范围及资产处理原则,其总的接收原则是分系统接收。这一制度设计理论上讲比较理想,然而,实际上却并未能按预定计划和规定予以实施。
在蒋介石8月份那个不具可操作性的“收复”命令之后,未及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成立,相关的军事部门和国民党派驻各地的机构和代表就已经开始接收了。等到“陆总”执行具体的接收任务,行政院主导的接收实际上已经是“第三轮”了。当时就有报刊对这一情况作出辛辣的讽刺:“当日本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中央还在措手不及没有派出各地接收大员的时候,上海已经出现了五颜十色的自动接收者。他们有的是战时潜伏在上海市的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战时伺候在上海四郊准备迎接盟军登陆配合盟军反攻的军事部队。他们既没有受过任何方面的接收派令,自然也用不着向任何方面报告接收账目,接收了的,就是‘我的。等到中央派出各地接收大员的时候,他们早就成了暴发户了。”
此外,按系统、分部门接收的弊端,也逐渐呈现。不光在党、政、军之间互相重叠交叉接收,就是在军队系统的接收中,也出现了各单位的重复接收,如在上海,“海军接收了农场,空军接收了科学研究院,陆军接收了轮船、工场,怪状百出……”“本来(按系统接收)也是一个适当办法,但是到底因为上海这个地方,物资太过丰盛,情形太过复杂,加以敌伪的混乱状态,头绪纷纭,虽然这样地分工做去,结果仍然是有隐匿、盗卖、侵吞、中饱的种种怪象,引起物议沸腾、人人失望”。有的地方接收了汽车,却没有汽油,因为油料又是另一个单位接收;甚至有的“接收车辆,疮疤遍体,零件全无”。在沈阳,“至接收已入混乱状态,初则竞争接收工业设施,继为房屋,近则进而为家具。素无人过问空楼大厦近均为某某接收大员派人驻入,甚有一军官接收数千间者,中国文化服务社亦居然自平津‘远征关外,本其一贯作风,接收日人印刷机器及书店,尝闻某机关以为捷足先登,却不料沈阳已十室九空,大失所望……”至于接收过程中中饱私囊、乱贴封条乃至兵戎相见的情况就更不足为奇了。民众形象地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收”:“若干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接收人员,大变其‘五子登科的戏法,使人民生活日艰,怨声载道,甚至使‘重庆人竟成为最讨厌而最可耻的名词”,人们谈到“接收工作”,就会联想到“贪赃枉法”,“接收人员”俨然成为“贪官污吏”的同义语。endprint
由于接收乱象不断见诸报端,加上接收系统内部由于分赃不均或职权不分而相互告状,更让蒋介石不安的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接收工作也相当不满。然而,为期近一年的清查,各地工作大同小异,除恶不能尽,最终不了了之,使民众感到了又一次的失望。当初预见的问题也不幸一一成为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其实也有民众提请国民政府从制度和体制的角度反思接收工作。如作者“石”撰文指出:“现在一般人都着眼在接收工作人员的‘贪污舞弊这点上,所以现在‘清查团正在鼓励人民‘密告等。但我们认为惩处贪污失职的重要接收大员固然重要,而立即纠正‘接收政策的错误实尤为重要!现在差不多大家都知道政府‘接收工作,使仓库内的物资霉烂,使工厂停闭,工人失业以及接收了东西只求标卖图利等事的不当了,(我们应知道是由于这些原定接收政策的不良,所以才更引起接收人员贪污舞弊的可能来的!)可是这些错误的接收政策却仍在继续!”也有人对接收工作缺乏预先谋划和整体实施亦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一切的措施显得完全无准备,无计划,沦陷区来的接收大员步调太缺乏整齐”。混乱的接收工作让民众在战时对胜利的憧憬顿时黯淡,刚开始时以为是“黑暗前的黎明”,继而以“暴雨后的燥热”聊以自慰,不曾想到竟“陷在黑暗的深渊”,且越陷越深。“我们胜利了吗?”这一疑问,贴切地反映了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与无奈。
综上,无论是国民党接收工作最初的筹划,还是接收体制和机构的混乱,乃至后来对接收的“清查”,都未能实现制度本身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民众对全国收复区总的观感是“货弃于地、人浮于事”,对于时局,也“由渴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声载道了”,政府在收复区所失去的人心,其损失远较接收到的物资价值为大。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由国民党军党体制衍生出来的弱势独裁之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蒋介石深受其利,更受其害。
胜利幻象:普通民众之观感
1945年上半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和苏联的对日作战行动和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大大加快了日本战败进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侵略者转为失败者。然而,在中国战场,“胜利究竟属于谁”这一原本毫无疑问的问题,在当时却不甚明了。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号召下,国共两党暂时放下争端,实现第二次合作,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抗战胜利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克服国民党种种限制和摩擦,以及自身兵员较弱、装备较差的困难,坚持抗战到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命令解放区军民原地驻防,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并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抵制中共军队受降。在国民党看来,胜利显然不属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军民。那么,收复区的民众观感又如何?何以发出“胜利在何处?胜利又属于谁?”的疑问?
一方面,这样的疑问源自收复区民众对改善生活之希望的破灭。日本投降之后,收复区民众对生活之改善满怀憧憬。然而,无情的现实却让民众“渐渐的沉重和悲痛起来”。
一是生活愈加困顿。除了前述重复接收过程中存在的对物资的破坏和任意侵占民众财产的行为之外,还有国民政府对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规定。由于政府在日占区不同货币区确定兑换政策的迟缓,给投机者带来了无限“商机”,其中不乏政府工作人员和“接收大员”。这种洗劫式的兑换,使得收复区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从前伪币十五万买一袋面粉,现在四十五万,从前三万四买一斤糖,现在十四万,从前四百块钱发一封信,现在要法币二十元,合伪币四千块了”。在南京,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害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提出警告,却未曾料到,民众由此“才恍然大悟,物价是这样涨起来的”!民众的凄惨生活和无奈愤慨,在当时创作的漫画中形象地反映出来。如董天墅作《仓库门外即景》:锈迹斑斑的仓库门上张贴了封条,门外则是一具饿殍;叶云作《如此接收》:一只写上“接收”二字的大手,握着一把剪刀,上剪书“高价工业品”,下剪书“低价农产品”,待宰之无辜民众却无能为力。
二是归乡遥遥无期。据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估计,抗战期间逃难至后方的人数约有两千五百万之多。归乡无疑是这些难民胜利之后最大的期望。正如当时流传十分广的歌曲《还乡行》(陈济洛作词,张定和作曲)写的那样:
好音从天降,欣喜若狂,尝够了流离滋味,准备回故乡;八年阔别,故乡该无恙?那小桥流水,那江南草长,那庭院绿荫,那田舍风光,那蔼然的父老,那慈祥的高堂,我曾苦忆了千遍万遍,如今快要见面了,怎不欣喜若狂?卷诗书,整行装,上征途,意气扬!江流似箭,关山退两旁,怎及我归心更急,恨不得插翅飞翔!行看重整家园,欢聚一堂,同建新中国,共乐安康。
这首描绘胜利归乡的歌曲刚一写出,就不胫而走,流行全国,因为它唱出了人们的心声。抗战胜利后,类似以“归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然而,现实中,大部分难民仍处于有家难归的境地,政府工作效率极缓,交通迟迟未见恢复。一名政府公务员感叹道:“长江航运全部统制,黑市票高达二十万元,决决不是我这个穷公务员敢去问津”,更何况一般民众。民众最初的欣喜与期待,于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殆尽,加上收复区物价飞涨、生活困顿,相形之下,接收大员却大发“胜利财”,民众对政府渐生绝望之情。所谓“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便是这一境况的真实写照。
三是遭遇身份歧视。战时在沦陷区,人们往往遭受多面的压迫,如时人所言“一面是敌兵,一面又是傀儡,同时还有困苦的生活逼得你去卖淫卖身,这真是千难万苦的境环”,然而,光复之后,却要面对接收人员和投机商人异样的眼光,“最可恨的是那些胜利面孔……不少人似乎有一个共同性,那便是在心理上对于沦陷区的人民的一种歧视”,以致沦陷区的民众“除了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苦之外,现在又加上一层无可告诉的精神上的压迫”,人们讽刺道:“重庆飞来的人,把收复区的小狗,也看作是奸狗,因为小狗会为敌伪守夜”。此外,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甄审”政策也引起了较为激烈的抵触情绪。1945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收复区各县市国民学校教员登记甄审训练办法》,规定“凡敌伪设立各级各类师范学校毕业之学生或曾在敌伪学校任教之教员,均应予以甄审并经短期训练考核认可后,方得分发国民学校任用”。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认为,正是国民政府这一不得人心的甄审政策,将青年人推向了共产党。直到1945年底,“大量日军仍然保持武装,并被国民党政府用来驻守政府军队尚不能到达的华北铁路沿线各据点”。曾经从事卖国行径的汉奸,此时也开始积极活动,向国民党官员行贿,试图以做地下工作的名义开释罪责。人们为此疑问“汉奸乎?‘地下工作人员乎?”对政府随意释放汉奸人员的行为提出质疑,抱怨那些“自己也认为死定了的恶徒们,却出乎意外的可以爬起来走动,甚至活跃!自己也认为逃不出法网的奸商们,在漏网中优游而出,在工厂复员声中,长袖善舞,发国难财后又发国庆财!”当时叶浅予的漫画《接收大员》就形象地刻画了如此场景:一个汉奸用钞票封住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接收大员的嘴巴!鉴于国民政府迟迟不愿审判汉奸,民众的愤懑之情也与日俱增。如在胜利八个月后的一篇文章写到:“我们最近很关怀这批逮捕已久,有名的大汉奸,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直到今天还是消息沉沉没有审判”“大家已是望穿秋水,希望当局从速把大汉奸审判一个下落。”对于汉奸们在狱中的优厚待遇,民众更是愤怒至极:“在得势时摧残人民的汉奸,即使在‘狱中也过悠哉游哉的生活;而抗战有功的军民,却遭着层层压迫与摧残”。眼看着昔日汉奸仍逍遥法外、若无其事,一位国民党老兵愤愤地感叹“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们的胜利?”一边是蒙难的同胞饱受胜利之苦,一边是战败的敌人仍旧嚣张得意。如此对比,可悲可叹。endprint
客观而言,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尽管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摩擦与反摩擦之争,但始终没有如同汪伪之流与侵略者合谋,因而也基本修复了在民众中的正面形象。抗战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声望都达到其巅峰状态,因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国民党来说,接收日占区都是一次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良机。然而,接收过程中,收复失土丢失人心的种种行为,使得国民党的政治资源消散殆尽,民众对国民党可谓失望至极。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的成败归根到底是由政治决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国民党从接收开始即埋下了内战败局之种子。这就是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
弱国外交:美苏争霸之产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外交原则,在战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度成为盟友的美苏两国,在战后迅速成为冷战的主要发动者,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加之战后满目疮痍、国力孱弱,也沦为大国的附庸和美苏争霸之牺牲品。反映在受降和接收上,原本是中国之内政,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国际”的烙印。作为最重要的两支抗日领导力量,国共两党在战后立即面临着如何受降的直接问题。尽管从法理上来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拥有合法的政治地位与身份,因而由其主导受降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缔造者和参与者,在抗击日军侵略中居功至伟,于情于理亦应参与受降。而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垄断受降权,完全将中共部队排除在外。
在美国看来,中华民国政府是“反对苏联在亚洲的扩张目标的唯一的统一的力量”。据美国方面统计,日军投降后,美国共运了40-50万国民党军队至新的阵地,派遣5万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党军在华北登陆,并占领北平、天津、平津以北的煤矿,以及该地区的重要铁道,由此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实现对该地区120万日军的装备及物资的受降任务;同时,继续施行在日军投降之前就已经确定的援建国民党空军和陆军的政策,表现为对中共主张受降权的反应较为冷淡甚至不支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并在日本投降前夕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诺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相比较而言,由于苏联的谨慎政策和毛泽东应邀参加重庆谈判,使得民众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颇有好感。为此就有舆论指责国民党,苏军在东北“不但撤兵,连条约上载明的铁路人员也撤退了,你们又有什么新制造的口实,还要坚持进行内战?”
远距离研判历史,固然有一目了然之快,然而,后人之见绝不如身处其中的当时人体会得更为真切。战后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然而,内中虚弱,时人更能有切肤之感。对于“强国”与“弱国”的理解,我们并不能比局中人体会得更真实。尽管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和战略地位,成为各方笼络与争夺之对象,而如真有人以此沾沾自喜,那就贻笑大方了。时人指出:“一个强国有他够称为强国的许多条件,并非靠他人几声称赞,亦非靠‘自己读之可以摇头晃脑的八股文。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人民之努力,尤须政治的清明。”这既是对当时苏联的称赞之言,亦是对即将到来之胜利的警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种种离心行为,使得民众失望至极。时人对中国“五强”之一的身份亦有讽刺之语。如在1945年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中国问题”列为重要议题之一,而“不得不劳‘三强费心顾问,这与原来自处于‘五强之一的地位岂非大有损伤……今其命运竟由它国支配,使吾人极感不安”,进而作者认为“中国之为大国,是理论上的存在,如何尽早把理论转化成为事实,端赖我们国人的自强”。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主的政体,命运终究会操于他国之手,国家沦为“棋子”、人民沦为“鱼肉”,更不要妄谈自强。“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也在于此。
余论:兼谈新政治史视野下的抗战史研究
传统政治史以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人们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相关重大问题贡献巨大。然而,随着时空变化,在过去毋庸置疑乃至成为常识的若干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却遭遇了重大挑战,“事件史”研究的困境与尴尬也随之而出。表现为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事件”所处的“局势”和“时段”,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得到更替,不可避免地使成为历史的“事件”走向孤立甚至被抛弃。这里的抛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研究对象,“事件”的说服力大大降低,而不断招致否定和怀疑;二是指作为研究方法,传统的“事件史”研究逐渐被边缘化。
这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将事件本身当作独立自足的研究对象,而不太在意事件背后的结构因素”,同时也是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兴起的一种响应。然而,无论是新政治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多视角切入,还是年鉴学派注重“中时段”“长时段”的研究,在布罗代尔看来,“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将它视为一个长时段”,借助它,“可以揭示出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所有重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是唯一一种能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的语言”。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之《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事件”作为构成历史现象、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终究是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领域。
那么,新政治史研究如何恢复政治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如何既关注“事件”,又关照其所处的“时段”?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或许能够成为一个突破口。简言之,“事件路径”的历史不仅将“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探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切入点,“关注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如传统的抗战史研究,以线性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宏大叙事的基础,往往是孤立的、静止的。改革开放之后,抗战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飞跃阶段,表现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地区(区域)研究的兴起、“中观”“微观”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其意义重点在于对传统意识形态框架的挣脱。例如,对国民党抗日战场的研究和著述实现了重大突破、把抗战史与中共党史区别开来,等等。然而,新世纪以来,在抗战史研究外延不断扩展的同时,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对新事件的关注,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一些原本已经得到深入阐释乃至得到公认的历史叙事又变得模糊起来,如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借此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这在手法上并不比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指责有多少高明之处——甚至断章取义地抽取一些本来富含整体endprint
历史感的语句,
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军事体制的素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为国共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关键看谁把握得更好,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谁的策略运用得更为得当。进言之,抗战的胜利,对于国民党来说,更是一次相当难得的机遇。然而,结果如何,历史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J].历史研究,2003,(4):144-153.
[2]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4]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M]∥文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11,(13):14-20.
[5]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行政院各部会署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J].交通公报,1945,(15):18.
[8]魏红运.民国史纪事本末·七[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9]国内时事:敌产接收经过与调查[J].见闻,1946,(4):18.
[10]小韶.上海的接收战[J].社会评论,1946,(32):11.
[11]民本.接收车辆之谜[J].金融汇报,1946,(7):11.
[12]孙洪.从“劫收”人员谈到官僚资本家[J].民间,1946,(5):2.
[13]本社社评.不要再让人民受胜利的灾难[J].古今谈,1945,(3):1-2.
[14]佚名.清查接收[J].读者文摘,1946,(3):5.
[15]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M]∥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16]君平.希望于清查团者[J].中立,1946,(4):10-11.
[17]石.向接收工作清查团进一言[J].经济周报,1946,(6):3.
[18]郭刚.我们胜利了吗[J].民众杂志,1946,(1):17-19.
[19]秋云.痛论接收[J].现代生活,1946,(1):17-18.
[20]酉星.胜利在那里?[J].时兆月报,1946,(8):8-9.
[21]慧年.胜利周年在南京[J].民主周刊,1946,(48).
[22]史思明.胜利面孔与妓女守节[J].平论,1945,(4):2-4.
[23]汪朝光.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J].抗日战争研究,2003,(2):1-28.
[24]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25]董天墅.仓库门外即景(漫画)[J].真话,1946,(1):11.
[26]叶云.如此接收(漫画)[J].民间,1946,(1):11.
[27]陈济洛.还乡行[J].广播周报,1946,(16):14.
[28]何冻尧.被裁之后有家难归[J].民众杂志,1946,(1):121-122.
[29]英士.寄自南京[J].平论,1945,(5):15.
[30]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修订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1]张琦翔.由“甄审”说到“奴化”[J].北大师大校友会刊,1945,(1):3.
[32]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33]张黑子.一月前的南京[J].自由导报周刊(上海),1945,(3):15-16.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马歇尔使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5]温锐.中国政治通史:第11卷[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3.
[36]廖耀湘.美蒋在南京受降前后与日寇的勾结[M]∥文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2011,(50):482-486.
[37]棻.汉奸乎?“地下工作人员”乎?[J].学习知识,1946,(1).
[38]山风.胜利以后[J].平论,1945,(7):15-16.
[39]叶浅予.接收大员(漫画)[J].愿望,1946,(12):183.
[40]假话室主.大汉奸的下落?[J].真话周刊,1946,(7):8.
[41]棻.汉奸肥,人民瘦[J].学习知识,1946,(3-4):163.
[42]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报告[M]∥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43]陶文钊.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六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5]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46]邱维达,刘措宜.国民党受降和何应钦的“精囊妙计”[M]∥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5):227-228.
[47]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48]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J].世界历史,1999,(6):19-31.
[49]梁纯夫.胜利一年来的美苏关系[J].中华论坛,1946,(2):14-15.
[50]北山.抢救国内和平[J].民间,1946,(5):2.
[51]林兴育.苏联复兴战区之努力与成就[J].新经济,1944,(1):14-18.
[52]陈循.中国问题:以莫斯科会议谈起[J].真话,1946,(1):12-13.
[53]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80-88.
[54]周一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史研究述评[J].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S1):176-180.
[55]章百家.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两点想法[J].党的文献,2005,(5):35-37.
责任编辑:汪效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