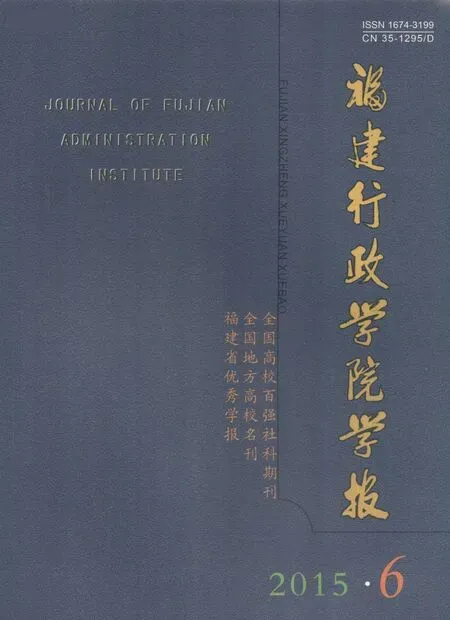晋升锦标赛下省际边界区的发展困境与突围
2015-10-16钟昌标肖庆文
钟昌标,肖庆文
(1.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315211;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经济管理科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3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十多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努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中部经济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占我国省际陆路边界线连接的县(市)级行政区面积1/3的特殊区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洼地”,进入一种“低水平发展的循环陷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成片的贫困区集中在省际边界区,2015年全国大约7 017万贫困人口的55%左右、561个贫困县的259个位于省际边界区。省际边界区与所属省域中心地带的差距越来越大,远远超过沿海与内地、东中西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关研究对我国大陆22个省各省会城市所在地与该省人均GDP 最低的地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的平均差距为3.45倍,其中甘肃省高达6.38倍。由此可见,我国区域经济最大的差距并不是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而是省域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以省会为中心,由近及远,经济发展水平随距离而递减,经济发展差距随距离而递增,省区交界地带绝大部分为欠发达地区。[1]这种“中心-外围”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显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果没有省际边界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这一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目标将难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关心这些区域相对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即使有也是从资源匮乏和文化滞后等视角进行解释。的确,省际边界区往往存在自然障碍阻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之处,甚至少数地区的自然条件很恶劣,文化相对闭塞。但为什么像江苏徐州这样所处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地理条件较好,秦汉时期经济比较发达,现在却不如胶东半岛和苏南地区?又比如晋冀鲁豫交界地区大部分为平原,经济发展也相对缓慢。更何况不少边界地区森林资源得天独厚,农副产品丰富,并且有相当数量的能源及矿产资源。据不完全统计,省域边界地区煤炭储量至少有3 000亿吨,占全国煤炭资源总储量40%以上。所以,省际边界地区的贫困化并不能从资源文化中得到解释,核心问题在于行政区经济模式下晋升锦标赛的制度环境。
二、晋升锦标赛下省际边界区的发展困境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分级管理是不得已的选择。这必然导致多个利益主体的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难免在利益上产生矛盾与摩擦。事实上,横穿五千年的中国史就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协调区际关系一直是我国的历史特征之一。作为一个大国特征的经济体,其引人注目的资源优势及巨大的国内市场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可以组织力量完成小国难以期冀的大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几乎所有产业的规模经济,可以抵御较大的各种灾害,等等。但是,大国经济由于区位、地理、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区域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必然存在差距,这在大国经济的发展初期尤为突出,是大国经济的“一根软肋”。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出现省际行政区边缘地带经济凹陷是多种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和经济体制高度分权的制度安排下,“由于中国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地方官员入手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乃至经济差距的源泉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2-3]。有学者将在这种特殊制度安排下,官员不断晋升的过程看作一种锦标赛。[4-5]本文从晋升锦标赛视角分析省际边界区的发展困境。
(一)省际边界区在本省处于政策弱势
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让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强势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区域经济事实上成为行政区经济。在晋升锦标赛中,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利益目标。地方政府基本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代言人,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彼此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总是想方设法将资源投入到周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产业和地区。每个省的中心城市或者副中心城市往往是政府职能部门施政与建设的重点,因为符合周期短、见效快的要求,大量的有限资源通常投入到这些地区,加快了其开发建设的速度。省级政府对边界区域一般不重视,甚至限制地方财政投入到边界区域,边界区域事实上充当了“献血者”角色。这些城市往往利用政策优势先发展,成为“要素海绵”,对外围地区的发展要素产生极强的“虹吸效应”,边缘地区的青壮年大都被吸附在省会或者副中心便是最好例证,增长要素的流出致使省际边界区域长期处于发展边缘,如北京周围的河北辖区基本都是贫困县。从市场作用的角度看,生产要素总是自发地从低收益地区向高受益地区流动,边界地区的发展弱势加速了这种流动,而这种流动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了同省际边界区的发展,形成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也就是说,在晋升锦赛中,省级政府对省际边界区政策支持不足,使得政府无形中加大了市场机制作用下的“马太效应”,使得边界区域发展越来越滞后于中心区域的发展水平。
(二)省际边界区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被边缘化
不仅这类地区处于政策弱势,难得有政策阳光聚焦,在此任职的官员同样处于边缘化地位。省会中心城市党委书记、重点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进入相应常委班子的可能性大,而几乎没有省际边界区的主要领导进上一级班子常委的。我国是强势政府,政府手中的资源配置力量雄厚,中心地区晋升的官员,将获得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也更有可能将资源向以前就职的地方倾斜,而对边界地区却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限制其发展。这一点,不仅从项目审批、财政资金投入等方面可以看出,甚至从官员的配置上也可以观察到。能力强的官员往往被配置到中心城市委以重任,而那些能力平平的官员甚至庸官被派遣到边界地区。一些感觉被“发配”至边界的地方官员因为晋升无望,干脆退出晋升锦标赛。更有甚者变“援助之手”为“掠夺之手”,进一步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三)与周边“难兄难弟”竞争同构化
晋升锦标赛的竞争规则使得地方政府仅考虑本辖区的经济利益,造成各地经济发展的分散碎片化,割裂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是对市场经济的阉割。省际边界区域不仅难以依托本省核心城市(如省会城市)的辐射,与比邻的外省邻居也难以协同发展。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前提在于交换稀缺资源,但行政边界两侧区域资源禀赋相近,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条件极为相似,又缺乏外生的生产要素投入,导致边界区域产业结构同构现象突出,加剧与相邻地区的竞争。没有统一的区域大市场,各地产业结构难以在更广的范围调整,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向落后地区转移,各地只能自成体系,产业结构雷同,整体发展效益不高,行政区之间的差距一旦形成便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地域相邻、资源同质,本来构成了区域统筹发展的天然基础,但各自所处的非均等的战略区位及区域政策导向,阻碍了边界区域的协同发展,重复建设、产业雷同等现象就不可避免。
(四)要素流动和信息传导被行政区边界阻隔
经典经济理论都是假定在一国范围内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只有国际之间才存在流动壁垒。由于自然、社会历史基础的差异,以及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势,在晋升锦标赛中政府官员同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竞争,加剧了区域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非合作倾向。地方政府往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地方保护主义或明或暗地长期存在,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原材料大战”和90年代的“市场封锁”,还是近年来政府采购对本地产品的优先,都充分显示出国内要素流动不充分,以及市场的分割。这种类似零和博弈的经济竞争模式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并在省际边界区表现特别突出,如:“原材料大战”时期跨省边界区往往关卡林立,国内要素流动的困难甚至超过欧盟内部。常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一大现象是,在两省边界跨出一步,手机要加漫游费,省际之间的“断头路”大量存在。在行政区交界地带,具有不同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这种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政策,使省际边界区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压制。
(五)公共品“外部性”特征导致边界区公共产品短缺
公共品的“外部性”特征使各地方政府不愿提供跨地区性公共物品,在没有合作契约约束的情况下,各地政府都想搭乘对方的“便车”享受正的外部性,并力图将负的外部性转嫁到相邻区域,让相邻地方政府承担。在没有更上一层政府介入的情况下,类似“断头路”这样的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空气污染这样的跨地区环境治理要推进就非常艰难,更有甚者,还出现有的地方政府将当地流浪人群强行用车运到偏僻邻近行政区域抛弃的事件。这种现象表明,和中心区域相比,省际边界区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极度缺失,跨地区的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由于各省中心区域经济发达,居民环境意识和健康保护意识强烈,一些具有较强负外部效应的项目,由于受到人口集中的中心区域居民的反对,政府不愿意放弃项目又要减轻压力,有关部门在项目布局上往往倾向于向行政区边缘布局,产生效益在本行政区域内,但负外部效果却由跨行政区域附近的居民来承担,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在我国省际边界两侧更加典型,进一步影响了边界区域的公共设施建设。
(六)边界区域地方治理难度大
利益主体越是多元,社会就变得越复杂,内生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就会越大,就越有可能危害整体的发展。相比省级区域的其他地方,省际边界区域的地方利益主体的跨界性导致治理的复杂性。治理主体涉及跨行政区域政府,且地方政府财力本身较弱,人力、设备等跟不上,导致各类犯罪、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反而较高,正所谓“三不管地带”容易出现“屋漏偏逢连夜雨”效应。此外,由于省际边界区与各自省会城市的空间距离往往较远,联系成本远远高于中心区域,这又导致治理成本偏高。作为经济理性的省级政府,在治理改革时往往选择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进行试点,以获得更多的改革红利,而省际边界区则很少获得机会。如“从省管县改革的实践看,绝大多数省份在试点时都优先选择经济强县,而经济基础薄弱县则大多被排除在外或被延后。”[6]
三、省际边界区发展困境的突围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协调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省际边界区发展的困境提供了战略指导。具体而言,需要从整体的协调机制和管理体系上寻找突破。
(一)建立合理的区域政策体系
我国地区问题由来已久,为加强地区协作和政府宏观调控,在不同时期为某些特定目的制定了不少政策。为避免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问题,充分发挥这些政策的作用,必须对出台的区域财政政策、区域税收政策、区域金融政策等进行体系化梳理,加强这些政策的协调,做好政策体系的无缝对接,努力勾勒出一套既各具特色又有机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所提出的,在“十三五”期间,“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加大区域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快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区域税收政策要及时完善,改变长期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立足税收中性原则,加大跨省际边缘区的税收支持力度;区域金融政策要纠正“市场失灵”,改变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边缘区不断被“抽血”失去自我发展能力的“马太效应”。金融机构要适当放松对欠发达区域的贷款条件,国债基金要向此类地区适当倾斜。
(二)通过制度安排降低省际边界区的交易成本
不同的制度设计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不一样。世界各地的实践表明,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必须切实转变政府的自身职能,恰当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弱化“行政区经济”,政府不能“一方面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参赛运动员,同时又是辖区内市场竞争的裁判员”[7],直到行政区经济逐步消失。省际边缘区的市场化改革启动的时间相对较迟缓,市场化程度远不能与东部沿海和所属省域中心地区相比。因此,作为省际边界区政府,除了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监督落实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构建良好的法制环境外,还要努力培育当地的市场主体,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省级政府,一方面,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制度必须跟进,“不仅要考核领导干部对本地区内的业绩贡献,还要综合考虑由于本地区发展而对相邻地区带来的外部性”[8];另一方面,省际边界区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更需要派出一批政治清廉、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官员去执政,改变当地长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构建新型政治生态。此外,绝大多数省际边界区域,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面积比重较大,应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补偿落后地区在市场开发中的损失。
(三)创建可行的省际边界区域协调组织
增加省级行政区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省际边界区的贫困化问题,比如设立重庆直辖市对解决原来四川东部的集中贫困区成效显著。但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并不能改变“行政区经济”的现实,且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防、民族等各种考量,并非现实的选项,而成立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协调组织却简单易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跨省际的区域协调机构,但运作比较成功的是长三角经济区成立的协调机构,其成功的一大因素在于上海的“火车头”地位其他省无从取代,其他省甘愿当配角,并且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较高。而在经济欠发达的省际边界区成立协调机构,这种制度创新产生的直接经济收益并不高,更多的体现为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这就导致各省参与的动力不那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参与就显得必要。中央政府可以出台政策鼓励设置省际边界区协调机构,比如解决协调机构行政级别、给予协调区域更多的优惠政策,有时还可以充当指导和协调的角色。此外,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富有成效的跨区域协调组织不能仅由政府唱“独脚戏”,还需要吸纳企业、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从而由原来的“区域管理”模式走向“区域治理”模式。
(四)创新省际边界区域协调政策
有学者在研究欧盟的区域政策后提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9]中国的区域政策之所以为人诟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一套完善的运行与管理体制。我国现行分散于各个部委的区域政策,往往以行政区为单位,对于跨行政区域则往往被忽视。特别是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类似跨省际的“断头路”现象存在多年也没有解决。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在使用时无排他性,如果没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跨边界的两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对方承担公共品供给的责任而自己“搭便车”,于是就会出现公共品供给不足或推迟的现象。因此,对于“外部效应覆盖全国或者多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公共品供给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外部效应覆盖范围仅限于省级行政区域内部的公共品供给则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10]。换言之,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事权必须清晰,辖区内的公共品供给主要由当地政府承担,而对于跨行政区域的公共品供给需要由上一级政府负责。只有这样,各个区域之间才能形成无缝隙对接,才会有真正的区域政策。由于省际边界区公共品的外部性覆盖一个以上省级行政区域,因此,相当一部分公共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省际边界区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需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区域协调政策也必须通过创新来保证精准到位。
四、结 语
“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在行政区交界地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行政区边缘经济”[11]。处于行政经济区边界地带的省际边界区,一直是我国区域政策忽视的区域。由于处于区位、自然禀赋、文化等方面的劣势,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与各省中心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本应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不但未能扭转这种差距,反而在晋升锦标赛中助升了这种差距。省际边界区要走出发展困境,必须从整体的协调机制和管理体系上寻求突破。由于省际边界区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扶贫攻坚重点,本研究对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肖金成.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C].北京: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3]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8(3).
[4]Li Hongbin,Li An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
[5]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J].经济科学,2010(6).
[6]肖庆文.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政府行为差异与推进策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11(9).
[7][10]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8-169.
[8][11]安树伟,母爱英.省级“行政区边缘经济”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5(6).
[9]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基础与欧盟国家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