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对不齐的纸
2015-10-06王刊
王 刊
两张对不齐的纸
王 刊
1
张妍站在门口时,我正埋头整理一束“甜言蜜语”。9枝顶级红玫瑰,加拿大黄莺、满天星适量间插,外加咖啡色英文包装纸单面扇形包装,便构成了这束小情人们喜欢的鲜花。女儿哪天也会捧回一束,嘻嘻。
彭姐,在忙呢?张妍一身灰色运动套装,胸部以上衬着紫,卷发垂肩。
没呢?今天冷清得很。张妍经营着一家内衣店,今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这个女孩好妖媚。顺着张妍的目光,一个女孩正要走过门口。黑色的高筒靴,嫩黄色天鹅绒齐膝裙,粉紫超短款披肩,带着耳麦,似乎沉静在音乐里。女孩遇到了我们热辣辣的目光,像被烫了一下,赶紧收了回去。
彭姐,你说这还是不是个女孩?张妍常常从走路的姿势里鉴别一个女孩。她曾夸口说,彭姐,不是吹,我一看一个准。
是吧。齐膝裙紧紧地裹着女孩的臀,显出饱满的曲线。
我看不见得,我们可以打赌。关于是不是女孩,张妍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整套理论,从头到臀,从远观到近看,呵呵,真是有趣。她当我说那天,我差点笑得岔了气,我跟她开玩笑说,用你的观点,我看你还是个女孩。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女儿的不幸。我笑了笑,门前的一排羊蹄甲,还没怒放,零零星星的,绿绿的叶子中间衬着淡淡的紫。
那是那是,她个死女子敢,看我不打死她。哎,女大不由人呐,都28岁了,还没耍朋友,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也急人啦。有没有合适的,你这个当阿姨的要介绍一下哈。
我手头哪有这个资源哦,有的话我就不开花店了。你看《非诚勿扰》好红火嘛。诶,对呀,你喊她上《非诚勿扰》嘛。
她哪里都不去。喊她去相亲就像要割她的肉,成天窝在屋头。恼火,这个死女子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还是羡慕你呀,你家妹妹是个美人胚子,又懂事,文文静静的,学历又高,将来一定带个好女婿回来。
你都说了女大不由人,我们家妹妹还是没谈恋爱,本科时就说要考研究生,不能分心吧。这次回来要好好跟她谈谈了。
你担心什么嘛,住在我们石油苑的哪个不羡慕你,养个女儿从小到大不操心。你家妹妹是不是回来了?张妍朝后拢了拢耳边的头发。
眼见着女儿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挺拔、丰满,还有男生喜欢的甜美,当我们手挽着手走过商场或者外出散步时,总有各样的目光射过来,做母亲的我像捧着一束玫瑰在走。
是。你看,旅行箱还在这呢。一回来就被同学拉出去了。一只红色的旅行箱立在“甜言蜜语”的旁边,笑盈盈的。
两个姑娘手挽手走进了内衣店,张妍起身离开。我们常常这样,说着说着,撂下一句未完的话,就去打理各自的生意。我也起身,按开旅行箱,把妹妹换洗的衣服拎出来。衣服里仍然散发着那股熟悉的味道,闻着让人微熏。
我的手插进白色连衣裙的衣兜,有软软的东西碰到了指尖。一看,我不禁傻了眼:试孕纸。
2
我之所以要回来,不是想家,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呆在异地。长长的国庆,同学还并不熟悉,大学的好友都独杖走天涯,留下我独自守着这个空城。要说,蓉城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住着住着就有了依赖。但一个人的7天,是怎么也无法打发的。倘若要在往常,他会匀出时间给我。可就在前几天,他添了第二个孩子。这无疑给了我当头一棒,原以为我才是他的中心,多么坚实的愿望在现实面前却薄如蝉翼。
我是从他微信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似乎还看见了他的表情和动作——微微笑着,手指翻飞地摁动着键盘,在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还在微颤的空气里打了一个响指——产女一枚。儿女双全。文字下配着几张在襁褓着的照片——一个血淋淋的讽刺。
我立即拨通了电话。电话被无情地挂了。我再次拨过去,这次挂得更为迅速。随后就关机了。我狠狠地将iPhone扔在床上,捂着被子欲哭无泪。天花板上,水渍印出了一个美女的轮廓,真想一脚踹上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爱上他的,但我清晰地记得三年前的第一次见面。11月13日。那时候的栾树顶着暗黑色的花,准备迎接生命里的冬天,我踩着飘落的细叶,咯吱咯吱,向校门口走去。我要见的这个人,仅仅只是在QQ上聊过天,聊到很晚。他说哪天带我去飙车去西岭滑草去都江堰荡铁索桥,他说到洛带吃伤心凉粉双流吃狗肉温江啃鸭子,他还说要资助我,给我的比我父母给的还要多。
我怯怯地站在路边,深秋的凉气让我缩了缩脖子。我再次从下到上看看自己,一身ONLY:PU拼接打底裤,腿部修长,好的臀线,暗红色棒球外套,妩媚。但他喜不喜欢?9点,一辆黑色的奔驰,旋风般停在了身旁。跳下一个中等个子的大叔,风衣裹住了大半个身子。替我拉开车门。坐在副驾,我死死地盯着玻璃窗,头微微右倾,左边像是长满了刺,戳得人生疼。不讨厌,也不喜欢。这便是第一次的所有印象。
我又一次一次地拨电话,他的电话除了“对不起”还是“对不起”。见鬼。我颓丧地靠着墙,抓了一把头发,隐隐有些痛。
三年来,我和他都生活在角落,他不在我的朋友圈,我也不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不想,便可以有毫无顾忌的快乐。一想,就毛躁的不行。
电话终于来了。一个小时后打来的。你打那么多电话,什么事呢?他曾向我约定,电话之前先发短信,短信的内容是:李总,合同发到邮箱,请接收。或者,明天的会怎么安排?看完,他就删掉了。我的真名一次都没有出现在他的手机里。
但我顾得了这么多吗?难道你背着我生了孩子,还要我化作喜鹊为你唱歌?妈妈的。
你自己明白你做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看到这些是什么感受吗?这么多年我的付出就一分钱不值?你口口声声保证说你们之间没有感情,那小孩是哪里来的?我想起你跟着某些人做爱就恶心。有她没我,分手,不要再见了……
电话那头现出长久的沉默,是被大火燃烧后灰烬的沉寂。
你说话呀,哑啦?你做得出就说得出呀。
我发微信之前关闭了你收听,你是怎么看到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了这个野种我们断交。电话里传来久久的电流声。不说话我就挂了。
我不是说过吗?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语气仍然是淡定的,不疾不徐的。我讨厌这种淡定,像什么都胜券在握。一种被捏在掌心的感觉。
3
妹妹的恋爱始于大一下学期,当妹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正懒懒地躺在床上,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闭着眼,还想享受这个早晨——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闯进来,同时闯进来的还有鸟儿的歌声,以及早春大地苏醒的气息。
妈咪,告诉你一个消息哦,我们部长喜欢我哒,就是那个公关礼仪部的部长,给你说过的嘎。女儿的声音甜美得像一块巧克力糖,一口蹩脚的四川话,像唱歌。
关于那个男生我能知道的是,河北人,大二,胖乎乎的,父母为银行高管。妹妹曾在QQ空间里上传过一张两人的照片,我曾经问过妹妹,这个男生是不是喜欢你?妹妹的回答很肯定,妈咪,你在想什么呢?他是我们部长,家里有钱得很,才不会看上我这个灰姑娘呢。
那要恭喜我们家妹妹呀。好久办喜酒,我和你爸爸也来赶个礼呀?你和他发展到哪一步了?
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呀。
显然我说的哪一步,包含但不止于妹妹的回答。
妹妹,我要给你说个严肃的话题,女孩要懂得自重哈,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恋爱时女孩最容易受伤,你不能糊里糊涂的。我相信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好自为之。我走到床边,一把拉开窗帘,阳光便一头砸进来,刺得眼睛有些胀痛。梧桐的树冠刚好伸到窗口,此时正顶着毛茸茸的新叶,在晨光里呢喃。
嗯啦,妈咪,我是你的乖女儿,你还不放心吗?
我当然放心啦,我们家妹妹可是最懂事的。话虽这么说,可我能放心吗?我打开窗,风便扑进来,我裹了裹睡衣,乍暖还寒。
妈咪,我暑假要去他们家,他带我去北京,我还没去过北京呢。
这个这个,我要同你爸爸商量一下。
好嘛,我知道妈咪最好了。妈咪,花店的装修怎么样了?妹妹在身边读书时,我选择了做全职。妹妹爸爸在石油单位,常年在外。妹妹终于上了大学,我就在城市的一角,开了一个小小的花店。
花都摆上了啦。
挂掉电话,我打开电脑,进入女儿的空间,再仔细地看了看那张合影。小子无邪地笑着,有些憨,盯着妹妹的眼睛里满含着光彩。小孩的心事都写在脸上,一眼就看得出。20多年前,妹妹爸爸也曾经这样看着我,牵着我的手,梳着我的发,颤抖着解开我的衣扣……一转眼,20多年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发了一会呆,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妹妹的爸,照片下写着:你的女儿恋爱啦。
写完这行字,才发现敲击键盘的手指竟然有些颤抖。去花店的路上,阳光明晃晃的,像刀子。当年,和父母的裂痕就是从恋爱开始的,不就是妹妹爸是农村人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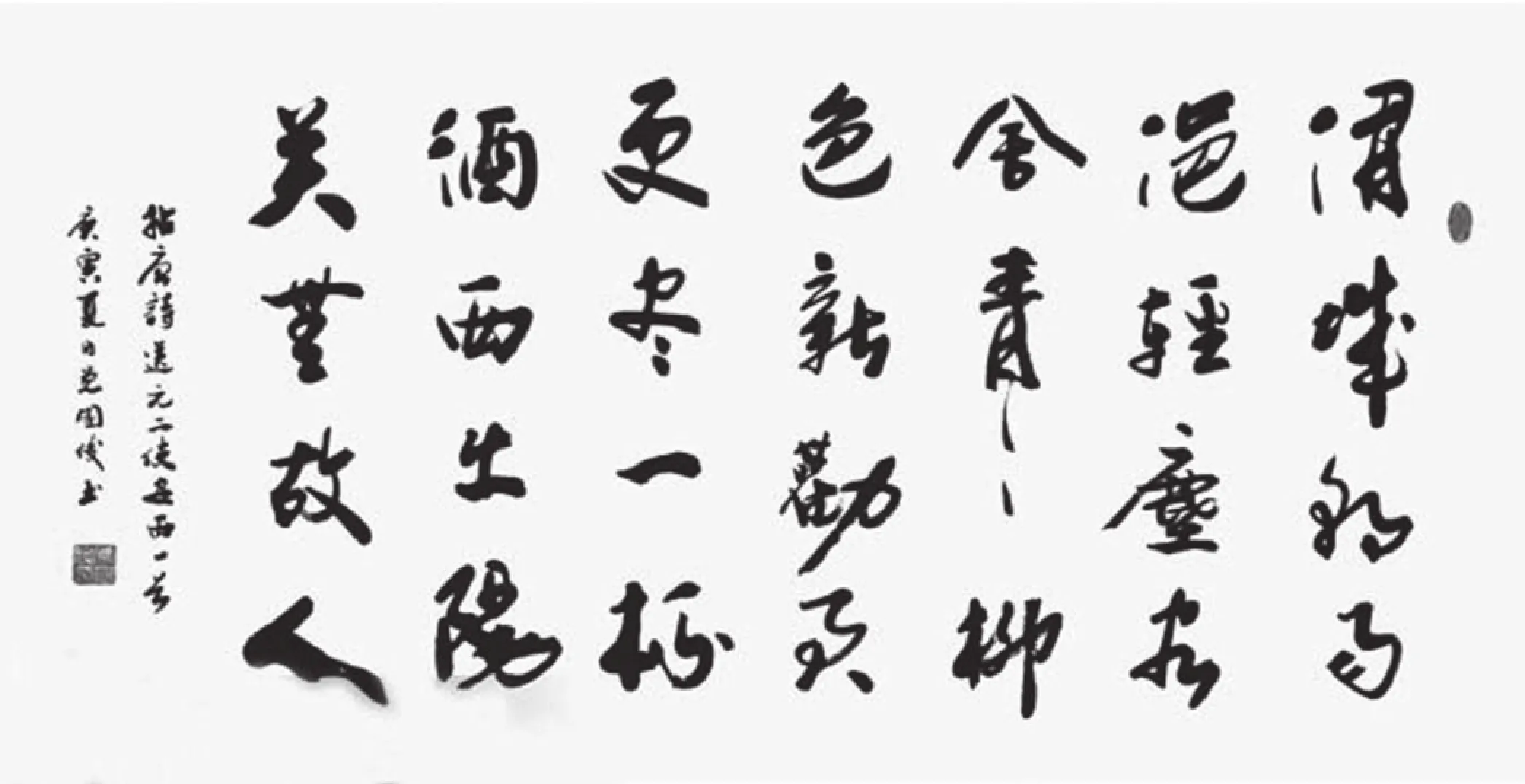
党国俊 书法《渭城曲》
妹妹暑假去北京前,我收拾着行李箱,妹妹站在一旁,嘻嘻哈哈地说笑。我看看她,欲言又止。作为妈妈,是应该嘱托些什么的。可是我又能怎么说呢?怎能说出口呢?
一年以后,妹妹分手时我连夜赶到了学校。妹妹看上去并没什么悲戚,或许是悲戚过了吧,或许是我担心得有些多余了吧。至于原因,妹妹说得很简单——性格不合,大男子主义,不懂得女孩的心。
当我问,你和他……我支支吾吾地没有下文,妹妹却坚定地说,妈咪,你想什么呢?你要相信你的女儿哈。
4
我的初恋在高三。现在想来,我爱上的除了他的阳光帅气,还有他那把吉他吧。
永远记得那天。学校停了电,放半天假。我们相约着去了网吧的一个小间,各打各的游戏。打着打着,身体就贴在了一起,我承认我全线溃退。后来,后来,我的裤子弄上了血迹。我将弄污的裤子装进黑色的塑料袋,转手扔进了街边的垃圾桶。又去妈妈常去的店买了一条相同的,才战战兢兢地骗过妈妈。
恍惚了几天,窃喜了几天,憧憬了几天,高考就到了。大学时,他去了云南,我撒到蓉城。渐渐感到电话里的他失去了真实,彼此的相爱到头来变成了单相思。不久,我们分了。
就遇到了刘涛。喊了一年多的涛哥,也分了。分手的原因,不说也知道,主要是他,那个被我喊为老爹的人。一个跟我小舅差不多大的人。
我们在QQ里聊得昏天黑地。我承认,这样一个男人有很多对付小女孩的武器,除了知识、阅历、那份沉稳,当然还有物质。
手机从床上摔下来,屏幕摔碎了。哭着打给涛哥,涛哥说,我不是叫你买个手机外壳么?你不买的嘛,这下惨了吧。哭什么呢?哭有用吗?我的哭声就更大了。打给老爹,老爹说,我很理解你,才买的手机,就摔了,哪个都心痛的。但是,小孩,屏幕坏了是小问题。我陪你去换。
万一机子也摔坏了呢?
万一是假设,我家的小孩不能提前预支焦虑呀。等到盖棺定论,你哭,我帮你递手帕,端个洗脸盆帮你接也行。那时,给你新买一个就行啦。我5分钟到楼下,出来吧。
我知道就这样把老爹和涛哥放在一起比较,是没有良心,但既然同时出现了,怎么就没个轻重之分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和他在一起就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安稳、踏实,一种类似父亲的亲切,一种想要侵入的欣喜。副驾上,明明知道有些动作是危险的,却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做——亲亲他的耳朵,亲亲他有些扎人的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你的心不知不觉沉下去,却让你的身体飘起来,舒张到极致去迎接他。
刘涛成了一根骨头,扔掉可惜,不扔却一点味道也没有,就连身体也一点一点地抗拒。
自然就有了一段奇怪的生活。明明跟涛哥在吃石锅拌饭,却跟老爹QQ聊天;明明坐在涛哥的自行车后,却不忍心挂掉老爹的电话……学会了撒谎,学会了敷衍,学会了心不在焉,直到,不想再戴着面具,不想再被撕裂,才终于提出了分手。
5
我按下了一串数字,就在即将拨通的瞬间,我果断地挂了。妹妹正在跟同学玩,在电话里一通臭骂怕是不好吧。一种虚空穿心而来,女儿还是原来的女儿吗?还有多少在欺骗呢?这个男生又是谁?刘涛?不对吧,他们不是分了2年多了吗?何况刘涛毕业时去了北京。难道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我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甜言蜜语”安静地立在身旁,咧着嘴嘲讽地笑。
那一次,妹妹与刘涛分手,我去看她,晚上坐在奶茶店,一个30多岁的人,挎着一个帆布包,进来买奶茶,朝我们望,目光一碰着就弹开了。从奶茶店出来,操场边,又见到那个男人。妹妹不冷不热地招呼,他也不冷不热地回应。真老。妹妹说这是一位读研的学长,也不至于这样一个年龄还在读书吧。难道是为他而准备的试孕纸?不可能,不可能,妹妹怎么会喜欢年龄这么大的人呢?
记得,就在这个暑假,妹妹问,《赤胆忠心》的老少恋,妈咪你接受吗?当然不接受,差了10来岁,能有什么交流呢?真是无法想象。妹妹当时似乎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难道是在为那人打埋伏?我的血液上涌,涨得脸有些红,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母女不相认的画面来。我有些哆嗦地拿起电话,熟悉的铃声刺得我的耳朵涨疼起来。铃声响了几遍,却并没人接。我狠狠地将手机砸在桌上,这个死女子,哼,太不像话了。手机滑出很远,啪地掉在了地上,后盖散开了,电池也弹出来。我慌忙捡起来,翻来覆去地瞧了瞧,心疼了半天。
一回家就疯疯癫癫跑出去了,说是个女生,谁知道是男是女?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要在以前,我会这样怀疑吗?我装好电池,盖上后盖,却怎么也盖不上。连电话也不接,越耍越野。
暑假时,一个男生的电话总是打过来,妹妹一接通就到了隔壁的工行。妹妹回来时,往往就失去了原本的活泼,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个男生是哪位?你好像很不开心?我一边修剪着花枝一边问。
是班长,今年又考起了同一所学校的研究生,在讨论入学的事情。我原本还想问怎么经常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情况,想了想,怕落得多疑的“骂名”,就继续做着自己的事。难道就是这个班长?怎么声音听起来有些苍老?
话又说回来,哪个小孩在这些问题上听父母的呢?想当年,爸爸说,你要跟妹妹爸结婚,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不就是因为妹妹爸是农村人吗?不就是怕以后农村亲戚多,麻烦吗?可是这些怎么能阻止我们呢?还不是悄悄地跟妹妹爸在出租屋里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谁管得了谁呢?到头来还不是当父母的做了妥协。那么大的人,还管她干什么?
但张妍万一看出点端倪,和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终归是不好呀。她会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当妈的身上。谁愿意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我愤愤然,手就不小心在玫瑰上划上了一道口,钻心地疼,血汩汩地冒出来。我撕开创可贴,缠上。
要不要给妹妹爸打电话?这个当爸爸的,真是做甩手掌柜的,孩子长这么大,他就几乎没有上心过。有一年,妹妹明明读5年级,同事问起时,却笃定地说成了4年级。
只是这件事,我怎么给他说?
彭姐,怎么呢,脸色有些不好呢。张妍走进来。
就是这些花嘛,把手扎了。我伸出贴着创可贴的中指。
好呀,彭姐,你还给我比中指。呵呵。张妍笑起来,她向我靠近些,手掩着半个嘴巴,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你猜,刚才两个女生什么关系?
呵呵,我怎么知道。朋友呗。张妍的气息是侵略性的,我本能地往后倾了倾。
拉拉。看不出来吧?现在的女孩真是看不出来。嚯嚯,彭姐,这是妹妹的衣服呀,好漂亮,怎么没见妹妹穿过呢?妹妹穿上,一定把全街的人都秒杀了。张妍从行李箱里抓起妹妹的衣服,晾在空中,左看看右看看。
这件衣服真的还不错,你看它的领子的做工,这里有一点红色一挑,就显得活泼了。我不慌不忙地抓过衣服,指着领子说。心头却一颤。
6
从来没有听我说起吧
我感到其实我很想你
总在每个孤寂的夜里
想着你却不敢告诉你
多么希望你和我一样
已经原谅昨天的遗憾
不想要再挣扎
在感情世界里怕寂寞
也怕你离开我
你如果爱我请对我说
说不让我寂寞
说不会离开我说不会后悔
只有你可以驱散我的寂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想着要跟他结婚。那天,捧着考研的资料,实在有些麻木,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他。又是3天没见面了,但看上去却似乎隔着远远的地老天荒。虽然刚刚例行公事地通了电话,我们的电话是一早一晚,他上班或者下班的路上。每天的这时候,我都掐着秒针等他。
是的,我多希望他能在教室里坐一坐,哪怕只是牵牵手,替我翻一翻书,那也是满足的。自从考研大战以来,我总是早出晚归,他也只是礼貌地问问累不累,我讨厌这种不咸不淡的距离。细细想来,这么多天他并没为我做过什么,更不曾牺牲过自己。天凉了,还是我自己去买暖宝宝,自己去买棉花鞋。喜欢吃的锅盔他似乎并不知道,很不喜欢去风里买早餐,却并不见他为我送过一份来。想到这些,我将资料狠狠地往课桌的肚子里一掼,攥着手机站在了走廊上。时针指向6点,突然想他陪着我吃晚饭。
电话被迅疾地挂断了。肯定回到家了,真烦人。一想到他正和另外的女人在一起,心里就涌起一阵呕吐感。我焦躁地在走廊上踱着步,刮得地板噌噌响。几位男生侧过头,诧异地盯着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你疯啦?打什么电话?叮,短信跳了出来。
想你陪我吃饭,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在家吃,都煮好啦,怎么好离开?
就说你有急事,你又不是没有撒过谎。
不行。
不来就再也不见了。
不见就不见。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败给他。只有他的这两年里,我也试图走近其他男生,可其他男生总不争气。像两根黄瓜,一根生,一根熟。一根让人食欲大振,一根还带着毛刺。
想起涛哥,那些年的豆汤饭、铁板烧,还有锅盔……人总是这么贱,失去了才懂得怀念。我曾多次安慰自己,涛哥即使在,也不是自己的菜,我跟老爹万一有未来呢?只是这个未来近乎于阿Q娶吴妈,近乎于南极眺望北极。但人总喜欢骗自己,我就是被一个谎言推向另一个谎言。坐在座位上,我把书翻得哗哗响,教室的温度降到了冰点。窗外正对着寝室,能够猜想,姐妹们此时正捂在被窝里,翻开笔记本,轻点鼠标,或者在手机里浏览人人网。热闹都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后天就考试了,输掉了考试,我还剩下什么?我想把自己按到书本中去,这时候的书本却像一堵厚重的墙,磕得脑袋生疼。
我颓丧地走向宿舍,就算这个晚上不曾来过,也或者今天复习的东西,三天后并不会考。踩着枯败的落叶,踢着虚无的光影。情侣们在暗影里相拥,用呼吸去呼吸对方的呼吸。这才是应该拥有的大学生活,我什么时候丢掉了它?我靠着一颗洋槐,洋槐粗粝的皮割得背生疼,这难道是生活的隐喻?肚子空空的,却全然没有胃口。
我在侧门老地方,出来吧。挂断电话,我匆匆地赶往侧门,考研的资料慌慌张张地掉到了地上。我承认,在他面前,我一步步无防可守。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就这么贱?就这样一个电话,抵消了先前的所有。
老爹,抱抱。高大的白杨伸出光秃的枝桠,路灯在枝桠间透出惨白的光。
老爹的脸少了往日的活泼,伸出手,微微探了探身,拍拍我的背,一下,两下,三下,浅尝辄止。
老爹,抱抱,你这不算。在暗淡的灯光里,老爹的脸上有陌生的气息,生硬得像块花岗石。
哎呀,不是抱了吗?老爹的声音里有烧焦的味道。
这么多天没见到你了,想你陪我吃饭,你都不干。你的时间才是时间?我的眼里立即汪出了眼泪,真没出息。我曾经一次次告诫自己,再也不为这样的男人流一滴眼泪。这样的决心,下了也就下了,终究算不得数。像飞蛾,明知道翅膀会烧焦,也还是一次次地绕灯飞行。
那你就打电话哇?老爹的脸有些变形。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受委屈?我想你的时候连电话都不能打?而别人什么都能做?我一想到你的身边有个女人就本能地反胃。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死死地咬着嘴唇,手指似乎要抠进座垫的套子里去。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不是早就说好了吗,叫你不要干涉我。我还想抓住什么,手里却空空如也。车子这小小的空间幽闭着我,像一个牢笼,我想捏着拳头砸碎这牢笼,可一点力气也没有,就连拳头也只是握成了拳头的形状,那力量是丝毫不曾有的。我抓起手提包,拉动门把手,我想在这冬夜的街头去奔跑,奔跑,让干冷的风刮得脸生疼,这样,眼泪就不会掉下来。可是,车门却重得怎么也打不开。
我们还是做爱了,那是一副解药。老爹曾经说,我的身体跟其他女人不一样,是安着喷泉和音乐的。在宾馆、在寝室、在教学楼的某个角落、在车上、在火车桥下、在良木缘、在帐篷、在荒野……我的音乐会低沉或者高亢地响起。曾经觉得日久生情这个词用于我真是太贴切了。
这一晚,我们掀动着车子,窗外的白杨和学生模样的人都跟着晃动起来,世界也一起陷落。我的泪再也忍不住,呐喊着或者在呐喊声里喷薄而出。
7
妈咪,饭好了呀?妹妹一进门就直奔厨房,抱住了我的腰。
哎呀,走开。我一挣,妹妹的手就被生硬地甩开了,妹妹怔怔地站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转过身,定定地看着她。妹妹被我的严肃吓着了。
妈妈,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了?妹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自己。一个女孩子要自尊自重,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我早就说过的。
我和妹妹都有裸睡的习惯,裹在被子里,我们总是拉些家常。这个暑假,妹妹总会有意无意地捂着乳房,或者趴着,只露出乳房的一个侧影。是不是她的身体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身体……妹妹嗫嚅着,我身体好好的呀。
妈咪今天怪兮兮的,怎么会对我说女孩要自尊自重的话呢?难道她知道了老爹的事?他们的见面仅仅只有奶茶店的那一次,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联系方式,怎么可能?
难道她知道了李然?她是见过李然的。一个高高的上海男,我的男闺蜜。毕业前,我们去了峨眉,在暗夜里,我们终于睡到了一张床上,不是什么都没做,那只是我敷衍老爹的话。我们浅尝辄止。是的,倘若说大学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话,恐怕就是和李然的分开了吧。但这件事,妈妈怎么可能知道呢?妈妈知道的是我跟着女生去的呢。
难道是刘涛,这么多年过去了,妈妈怎么会翻老账呢?刘涛也不可能再打电话来吧。难道是他托人搞的恶作剧?这个这个,不可能的啦。他这样有意思吗?
难道是妈妈挖出了我高中时的旧新闻?难道他知道网吧的事?想到这里我坚定地摇摇头,妈妈不是福尔摩斯。
但不管怎么,都得注意了,我要乖一点。帮妈妈做饭,帮妈妈料理花店,哦,还有,自己的衣服再不能麻烦妈妈洗了。
我拿出白色的连衣裙,衣兜里赫然地露出一张试孕纸来……
◎王刊,70后,生于四川广元,现居成都。先后在《黄河文学》《四川作家》《青年作家》等发表小说、散文若干。出版随笔集《孩子是父母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