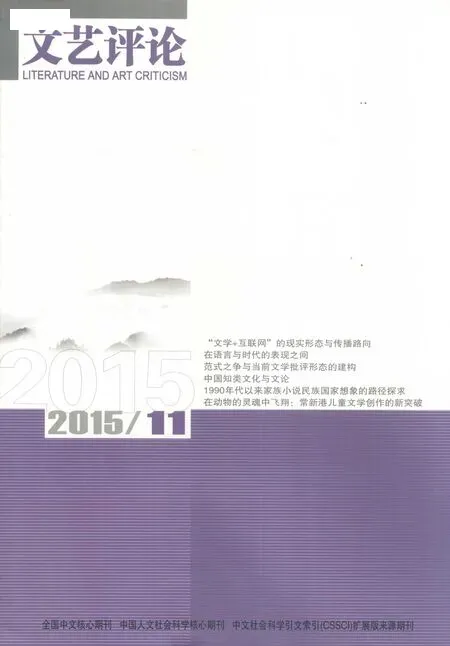迟子建小说中的“河流与女性”母题论
2015-09-29孙胜杰
○孙胜杰
迟子建小说中的“河流与女性”母题论
○孙胜杰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说:“意象经过作者的选择和组合,达到象与意互相蕴涵和整合的状态,它自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载体,一种人文精神的现象。”①文学是精神的创造,永不停息的河流与作家奔腾不息的灵感相遇合撞击,遂化为作品中具有灵性和生命感悟的审美意象,对河流热爱、关注和书写的心灵都是灵动而湿润的。地域空间特有的物质和文化精神与生存在其中的人的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地域空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会在文学创作中构成创作主体的“潜意识”。迟子建是黑龙江这个冰雪世界所孕育出的文学精灵,在东北的茂林江水中长大,涌动的河流是她最初的嬉戏之地,白山黑水的“原始风景”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作品中“像海洋和森林这样的自然物质的普遍形象反复出现在大量诗作中并不能看成是‘巧合’”②,海德格尔也曾说“返乡首先是从漫游者过渡到对家乡河流的诗意道说的地方开始的”③。所以,在怀旧的情绪中,故乡东北小镇中不通向城市文明,封闭的“河流”成了她长期漂泊与彷徨的休憩所和安放灵魂的乌托邦。对生长之地的无限回忆是迟子建文学梦想的起点,河流带给她童年最难忘的记忆,但迟子建在小说对河流的诠释,不仅是对于她童年记忆的简单复制,实际上,“河流”意象已经经过了她的加工处理,衍生出了丰富的内涵。
一、河流与女性
古代称原始生存空间为“州”,《说文解字》中对“州”的解释是“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④。可见,从远古造字伊始,就以河流的集体表象为依据,积淀在人类的意识深处。择河畔而居,不仅是生存背景的选择,更是河流孕育生命的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在人类的意识中,河流与女性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水的神话中,经常把河流与大母神崇拜联系起来。经过考古学家求证,在两万多年前有女神宗教,其中最让人崇拜的神是大母神,她创造了世间万物和人类,遍布于欧亚大陆的女神像是其结论的证明。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大地能生长出谷物,而就像女性的子宫的洞穴能涌出流水,哺育人类,河流便成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神圣交往的媒介,于是河流成为地母的象征,进而也被视为是女性的象征。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于想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⑤神话中对河流的叙述,也正是来源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整个精神性的遗传,注入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⑥。
《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大禹治水时,妻子涂山氏于滁河畔望穿秋水,不禁长叹吟咏出“候人兮猗”。这句发为心声的“候人兮猗”从此开启了痴情女子的心智,也成就了中国有史可稽的汉语爱情诗的篇章,随之“女性与河流”的一组文学形象自此肇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河流认识与对女性的认识是有很多相似处的。“在水一方”的“伊人”、“目渺渺兮”愁的湘夫人,“不禁暮暮朝朝”的巫山神女,“有泪洒湘竹,至今湘竹斑”的潇湘二妃,以及令曹植倾心爱慕的洛神,“河流与女性的共存共现,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原始先民时代即已固定并流传下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⑦,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河流带给人的空间想象是非常丰富的,涓涓小河“不舍昼夜”地奔流入海,既是生命过程的表达也是生命力的展现。“河流的象征涵义基本与流水有关,它象征自然与时间的创造力”,⑧河水的流动性与人生的起伏跌宕刚好契合。《无边水色》中,白雾笼罩伊水河畔留下了少女成长的足迹,也见证了这群女生的成长;《与水同行》中,苇河镇的流水充满了“我”所有的记忆,那些关于居住在海边的白佬族,关于早逝智慧的祖母……对世事的洞明皆源于河流,“祖母曾在这水畔顺着眼看世界,而我则睁大眼睛随着流水继续看视线早就看白了的世界”⑨。《逝川》中,在漠那小镇,之所以把“河流”视为女人,是因为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河流始终给村子带来丰富的鱼汛,能够在东北那漫长难捱的冬天,给漠那小镇上的人们提供食物。“漠那小镇的人们把这条江看得跟女人一样亲切。这条江在几十年前,可以很随意地用麻绳系起一张网,撒在江中,然后鱼就像爬满了篱笆的葫芦似的钻了一网。起网时鱼尾翻卷,鳞光闪烁,那真是让人百思不厌的美好时光。”⑩后来鱼汛的消失也被认为是“这条江就像女人过了青春期,再也生不出来孩子来了。江水不似往昔那般喧嚣,它平静而沉稳,就像个行将入土的人”(11)。旗旗大婶就像这条江一样,是“不曾开怀”的女人,这条河流对于她来说,在生命意义和情感上都非比寻常。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不幸没有让旗旗大婶丢掉生存的勇气,守江的执着、猎熊的坚韧以及用最宽容的胸怀接纳迷途归返的丈夫,这些都是旗旗大婶最闪光人性本色。
逝者如斯夫,女性对于韶华消逝残酷性要比男性的感受更为深刻,《逝川》中的吉喜,在最美的年龄敢爱敢恨,成为不依赖男人的生活强者。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这样的,母系制被父权制取代后,相应地父系文化取代母系文化,“男子在所有神话里都被看作是具有规范性的,而女性则是这一规范性的变异或离差。这就是说,男性是重要的,是物种之范,是‘标准’。而女性则是男性的变体”(12),漫长的男权社会发展中,女性没有话语权,是“第二性”,以“他者”的身份而存在。所以,吉喜所具有的智慧与才华不可能被当时的男权社会所容忍,她的挑战权威没有为女性争取到自由解放,反而被社会压抑,成为被所谓正常家庭抛弃的女人。逝川的奔流不息带走了守望在河边的吉喜的美丽,从男人心中的女神到只与孤独相伴的老渔妇,每年逝川中捕捉“泪鱼”成为她生活下去的动力。但生命的河流不会永远直线流淌,河流有岔路,生命亦如此。今年捕捉泪鱼的最重要的夜晚,那个曾经让吉喜一生唯一倾心过的男人的孙子求助她帮自己的妻子接生。捕捉泪鱼为自己赢得下一年的福气还是冒着遭遇灾难的危险去接生成为吉喜所要做的两难选择。其实吉喜并没有选择,只是归置了已经准备好的捕鱼工具,她放弃了捕捉泪鱼的机会。40岁长出人生第一根白发时的吉喜选择做了阿甲村的接生婆,在她手里诞生了无数新生命,她也用河女特有的宽容原谅了过往的背叛,她的生命之河包容了世间女性的悲欢与辛酸。
河流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成为孕育生命的核心环境意象,所以,无论是吉吉还是旗旗大婶,她们虽然没有像普通女性般真正生育过孩子,但她们都以河之女特有的方式孕育人类生命,河之女们用生命守望着河流歌唱,河流也让她对未来充满信心,用河流的宽容去拥抱生活,展现了河之女生命的坚韧。
二、“河之女”的死亡与救赎
荣格认为,“情结一般是由创伤造成的”(13),并且每种情结又都根源于一种原型。这也就是说,情结的形成有与生俱来的内因和后天经验提供的外因两个因素。也不是所有的创伤都源于外界,也可能产生于心灵的内在,是基于“人类终究无法成为完人的道德冲突”(14)所造成和触发的。“情结这东西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的情调或痛苦的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聚集物。”(15)有着挚爱与亲人逝世经历的迟子建对人世间的沧桑与生命的无常体会是非常深刻的,她通过死亡来认识人的现实处境,对历史进行反思,映射的是对现实的关怀。逝去的生命可以在现实活着的人的梦境和朴素的生活中反复出现(《遥渡相思》《重温草莓》),和鬼魂做伴旅行(《逆行精灵》《向着白夜旅行》),生命可以得到重生与延伸。无论生死,都笼罩着温情与爱意,带着人本来的温暖与浪漫的诗意。
河流是死亡事件频繁发生的地点,她是死亡确认者而且也隐喻了重生。《草地上的云朵》中的丑妞,本来如阳光下的小树一般健康,却在嬉戏中被河底的哑炮炸死……“丑妞的一只脚,几团粉红的碎肉,被炸死的鱼,炸弹的金属碎屑,连同刘守金的胳膊,都被装在小船里”(16)。死亡被作家用多种事物状态展示着,却没有死亡的恐怖气氛,有只的是为年轻而美丽的生命的逝去的痛惜和通过死亡展现的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天水和青杨想起了丑妞所描述的有关白鹤的情景……他们相信,丑妞已是天上的白云中的一朵了”(17)。《罗索河瘟疫》中的罗索河像“瘟疫”般吞噬了接生婆以及接生婆的儿子。当接生婆杀死自己杀人犯的酒鬼大儿子,这样的行为给读者所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生婆的职业对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会使人拥有一个“上善若水”的纯洁善良的灵魂,接生意味着未来的希望,可是接生婆看到自己的未来的希望却都是些“恶”,小儿子领条仁义却痴傻,“未来梦”的破灭让做为母亲的接生婆选择用彻底毁灭自己,以引来救赎,接生婆杀死了自己孩子别利后,最后也自杀罗索河,投身罗索河好像瘟疫一样飘散在接生婆的家中。之所以选择罗索河做为结束接生婆全家生命的地点,另一层意义也不无用河流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河流来源于自然,利用于人间,它涤去污垢,还世界洁净……河流与宗教中的洗礼仪式被作家用来表现作品主人公通过河流得到救赎,开始精神上的新生,河流是救赎的原型性象征”(18)。所以,选择河流作为死亡地,也是期待洗刷罪孽,求得人生的救赎。
现代人对周围世界的把握越来越艰难,命运瞬息变幻,人在这样的生存体验背后,感到的是生命的渺小和莫名的焦虑、恐慌,生命也会处于一种飘泊的状态。人们渴望的是从一些可以把握的日常生活故事中找寻可以慰藉的力量,有的时候,关注别人的命运,在别人的生命残缺中“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19)。迟子建的小说中,既有着对生命温暖的独特表达,也有着对生存痛感的真切感受。生存的痛感的体现最主要的就是对残缺、陨落生命的关注。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而承载着死亡的就是河流。河流与死尸都是静态的意象,但当死尸漂浮在河流之上而互相映衬时,就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动态效果。《岸上的美奴》中,初中学生的美奴在母亲陷入迷狂状态后,感到痛苦、寂寞,知道母亲与老师的交往后,又增添了道德上的罪恶感和压抑感,整个故事在美奴亲手把母亲推入江水时达到了悲剧的顶点;《沉睡的大固其固》中,温高娘平凡而受人尊敬的一生的重要环节是她生命的结束,这是一种生命责任感的呈现,个性生命形式的最终完成;《草地上的云朵》中对白鹤有着无限憧憬的丑妞被张无影放在江心的炸弹炸死了,一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的魔术师丈夫出了车祸,“我”内心无比痛苦,但是当“我”看到蒋百嫂把矿难中死去的丈夫亲自藏在冰柜中的悲痛时,听到深井画店老板陈绍纯的悲歌时,直到失去母亲的云领带“我”在三山湖放河灯的时候,所有这些在河流中发生的死亡者的灵魂彻底拯救了“我”。迟子建曾说:“也许是由于我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的缘故,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而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的。”(20)
死亡既是灿烂生命的终点,也是回忆的开始。生命的生动经历不会因为死亡而失去本来的鲜活色彩,恰好相反,它会成为一股强烈的力量参与生活,创造生活。迟子建小说关于死亡的描写中,没有情绪的宣泄,而是从主人公的身上发现的一种拯救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死亡”是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是精神的历练与拯救。可以用迟子建散文《冰灯》中的一句话,来对作者的生死观进行诠释:“冰是寒冷的产物,是柔弱的水为了展示自己透明心扉和细腻肌肤的一场壮丽的死亡。水死了,它诞生了冰,覆盖着北方苍凉的原野和河流。”(21)
三、“河流与女性”母题的生命文化之思
河水的流动形态启迪了迟子建的畅想天河之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明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为代价。迟子建在作品中对河流污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无思考。如果河流有生命,那她就是大地之神“盖娅”周身的血管,滋润着众神之母,是其生命的支撑和价值体现,亦是自然界最神秘最脆弱的核心主体。文明的崛起,河流被污染枯萎,这是全球生态的危机的预言,作为一个具有浓烈人文情怀的女作家,她对河流的文化生命更为关注。在《关于原始家园的浪漫追踪》中,迟子建写道:“城市是地球最大的罪孽……平衡失落了,世界就一直倾斜着,尽管我们驻守家园,可我们却在滋生和发展着那些敌意、困惑和迷。”(22)伴随着城市文明的发展,自然环境受到破坏,作家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使她的笔触伸向那些枯竭的河流、不断扩大的荒漠、濒临灭绝的动植物,这不仅是自然的危机,更是威胁到了人类的精神家园。迟子建在作品中旨在写出自然生态的失衡和社会伦理的偏离,“河流”意象具有了宣扬生态观念的新的精神意义和指向。迟子建用诗化的语言赋予河流以生命,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讲述生态变化和人的精神危机。
传统观念中对河流的礼赞和河水泛滥的肆虐在现今关注生态的作家笔下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流动的活水变成死水,作品中尽是枯竭的河流和岸上精神颓废的人们。流动的河水所彰显的鲜活生命力与顽强精神渐渐隐退;邻水而居,被河流滋养的人们在精神上也断了源流,滑向天平倾斜的另一端。迟子建在作品中写出了自然生态的失衡和社会伦理的偏离,“河流”原型具有了宣扬生态观念的新的精神意义和文化指向。迟子建作品中出现过的很多河流,如额尔古纳河、罗索河、黑龙江、逝川等等,它们如今或在继续流淌,或已经冰封,她用诗化的语言赋予河流以生命,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讲述生态变化和人的精神危机。小说《鸭如花》中,她借徐五婆的口谈了对河流的看法,认为给河流安上堤坝就好比给河流做一次绝育手术,从生态观念上说,这是对河流的束缚,也是对河流生命力的遏制。很早以前,西方一些倡导保护生态的人士就曾提出“让河流尽情流淌”的口号,并不是不接纳新兴事物,而是修建堤坝是以迁移居民、淹没古迹为代价,并且会产生一系列生态问题,修建埃及阿斯旺高坝就是很好的警示例子。农村妇女徐五婆在她所能思考的范围内,表达了自己对于生态环境的担忧。
《雪坝上的新娘》中一条蜿蜒的被白雪覆盖的小河给在现实生活中受尽凌辱的“傻子”带来无限温暖,让他重燃生活的勇气与力量,河流用她的活力给人带来永恒的慰藉。江河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它在提醒现代人,作为自然之子,受其恩惠之时,也要懂得反哺自然。《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在鄂温克人的心目中,额尔古纳河既是生命延续、种族繁衍的孕育之河,也是灵魂栖息之河。神秘的河流令鄂温克人尊崇、敬畏,在尊崇敬畏中饱含着对精神家园的企盼,温婉的额尔古纳河是条“母亲河”,缓缓流淌中诉说着鄂温克民族古老的神话,河流在小说中,不仅是“起情动意的物象、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还是连接岁月变迁、追溯生命源头的媒介”(23),额尔古纳河与一个部落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河流不仅是家园的象征,更是一种幸福、温暖、和谐的理想生存状态。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篇中这样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24)这句话鲜明地指出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个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世界,小说通过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之口,讲述了一个古老部落民族的百年史,家园从聚到散,由盛而衰的故事。在凄美而又不乏温情诗意的讲述中,表达了作者对衰竭的古老文明的追问。一个民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顽强、坚韧地生存着,当社会进入经济文化转型期,古老民族最终走下山,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被迫融入现代文明。迟子建在对河流的追忆中,探寻着一个古老民族部落的历史,同时也为这个与自然共存的游牧民族唱着一首深情而无奈的挽歌。
迟子建从小就与大自然亲近,有着万物有灵的信仰,面对人类的软弱与无奈,她意识到大概也只有萨满的神鼓之声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油然而生,这一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明显的表现。萨满最令人震撼的是跳神时的激情投入,迷狂与陶醉让死亡的恐惧退却,自我牺牲精神更是萨满的生命之舞。在现代文明侵袭之前,妮浩继承了尼都萨满的衣钵,成为保护氏族延续的部落新萨满,妮浩也把萨满使命当作自己人生的理想。身为萨满,每救一个氏族成员的性命都要牺牲自己的一个孩子,在亲情与族情的选择间,她每次都选择了舍弃自己的孩子去救族人。神人的大爱与凡人的牺牲都被她全力倾注到神秘的仪式中,萨满的迷狂与陶醉是对死亡的抗争。为了氏族的责任,为了信仰,她忍受着亲人离去的巨大痛苦,最后在一场大雨降临时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萨满是神与亡灵的信使,妮浩萨满靠着信仰的力量超越了死亡,在她身上有着一种崇高的大爱精神,对生命价值的追寻。
伊莲娜是鄂温克民族中唯一一个受到现代教育的孩子,最终却也在现代文明与氏族文明的选择中迷失,死在冰冷的河水中。通过氏族人一批批的死亡,迟子建表达了她的担忧,那些被现代文明和所谓全球化戕害的弱小民族,最终会消逝。萨满的生命之舞为现代人敲响了警钟,宇宙间的一切生灵不分贵贱,如果一味掠夺和破坏,人类最终会失去生存的家园。作为一个作家,迟子建只能用手中的笔来给肆意蔓延的现代文明以警示。“如果说一种民族文化的消失也是一种死亡的话,那么迟子建以现代寓言的方式喻示出现代人精神的荒芜,死亡将作为生命的图腾来纪念正在消逝的人类曾经拥有过的优美的文化。”(25)“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代价的……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26)。“让生命浸润在每一片日光、每一株草木、每一丝微风之中,在与自然的肌肤相亲、心领神会的交流中,切实触摸自我生存的依据,探寻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捕捉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深层体认”(27),这是迟子建在小说中试图为我们建构起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家园。
四、结语
迟子建作品中的河流与女性母题已经成为作家生命和创作的某种情结。与新时期以来很多作家相比,迟子建的创作并不是善变型的。她不紧追文学潮流和写作技巧的花样翻新,甚至有时还有与之滞后的隔膜,但这些都不影响她作品内容的丰富与深刻。她通过河流与女性这组意象构建起的独特的东北小镇文学,表达着作者对存在、生命、死亡、文明的诗性思考,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形成了鲜明的“迟子建风格”。
2015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中河流的地域文化想象”]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东方学院)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②弗莱《作为原型的象征》[A],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③海德格尔《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臧克和《说文解字新订》[M],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5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⑥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⑦王莹《〈诗经·国风〉女性形象与水文化意象关系之探微》[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76-80页。
⑧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菲利普·威尔金森《符号与象征》[M],周继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3页。
⑨迟子建《与水同行,亲亲土豆·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卷(1992-199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⑩(11)(16)(17)迟子建《迟子建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2)[美]珍尼特·希伯雷·海登,B·G·罗森伯格《妇女心理学》[M],范志强,周晓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13)Murray Stein《荣格心灵地图》[M],朱侃如译,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61页。
(14)Stein M.Jung's Map of the Soul.Open Court,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1998年版,第54页。
(15)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成穷,王作虹,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8)孙胜杰《原型批评视角下文学作品中“河流”的救赎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06-110页。
(19)本雅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0)《秧歌·自序》,《迟子建文集·卷二》[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21)迟子建《冰灯·我的世界下雪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2)迟子建《关于原始家园的浪漫追踪,北国一片苍茫·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卷(1985-199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23)朱育颖《与水同行——当代女性小说中的河流意象探析》[J],合肥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第77-81页。
(2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5)郭力《迟子建:给世界温暖与爱意》[J],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
(26)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J],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第34-35页。
(27)刘传霞《论作家迟子建的自然观》[J],理论学刊,2002年第1期,第120-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