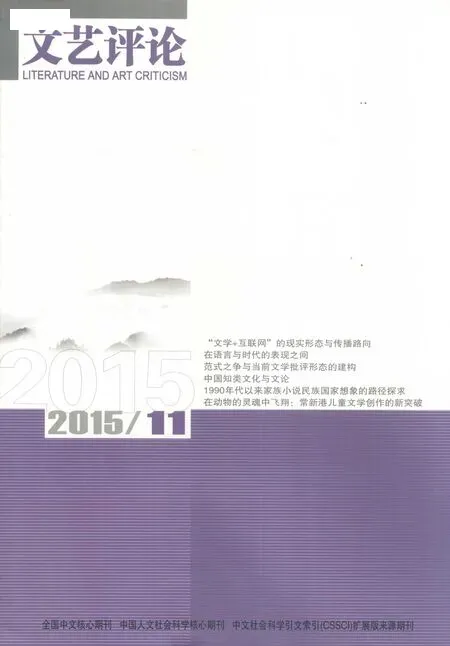西部文学的自我 ——韩子勇文艺思想述评
2015-09-29○王敏
○王 敏
韩子勇先生的著作自1998年《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出版以来,陆续著有《当代的耐心》(1998)、《边疆的目光》(2001)、《文学的风土》(2004)、《木卡姆:巨灵如风吹过》(2006)、《木卡姆》(2008)、《深处的人群》(2009)、《鄯善之书》(2008)、《浓颜的新疆》(2008)、《大声说话》(2013)等,他的研究,似以2004年为分界,由文学理论研究倏尔转向大文化批评,自此换了一番研究的天地。然而,在韩先生的诸多著述中,我读的最多,对我影响最深的仍是他的这本《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就西部文学研究这一“偏僻领域”而言,韩先生的工作,比之拓荒者,更像是一位“荒野筑居者”,再其后,所有有关中国西部文学研究的探讨,都绕不开它。
西部的自我
韩先生主张西部作家值得肯定的写作面向,应该是一种立足偏远却又能超越偏远地域经验的写作态度。在韩先生的文艺观念中,西部文学内部一直存在着艺术规范与人文内核上的创作张力,这种张力或者来自市场经济之下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压力,或者来自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价值观的趋同化、平面化对西部多样生活经验的话语压力。就这方面而言,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汉族作家体会更深一些,这就像是自家从小一起生活的堂兄弟、表姐妹们一夕间都住上了洋房,开起了小车,自己却还住在那个幼时合家欢聚的贫穷小屋里,能够共同言说的话题渐渐变少,可以提供的“有用”越来越捉襟见肘。这种“捉襟见肘”的场景与心理况味,颇有些像我在接受京畿地区、上海地区以及南方诸省的评论人同行们陆续送给我他们装帧精美的著作后,却始终“不好意思”将自己那些在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包装简陋、设计粗糙的书一一回赠一样。对此,韩先生概括得好,认为这种“捉襟见肘”促成了西部乡村叙事、底层叙事的文化基因,并与西部的自然物候,复杂地杂糅一处,成为一种地方文学的叙事传统。“西部文学的创作者也的确有更多的‘乡村意识’或‘底层意识’,这一点不仅与京畿文人的优越感相区别(即使是略嫌土味的京味小说或王朔式的调侃),也与沪上文人的市井形态不同,甚至于江南水乡的情调性叙唱也拉开距离。在这里,‘底层意识’包括着‘弃’的观念,一个‘弃’字远不是‘偏僻’、‘落后’和‘愚昧’所能概括的。这个‘弃’是形态上的凋残感、畸零感,是胸臆上‘无所谓’、‘不自觉’或者人所共言的什么‘旷达’之类,在生存本象上,更近于‘无’、‘消失’和‘临时的记忆’”。①本质来看,事实上,希冀凸显“自我标识”的西部文学、新疆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所面临的叙事压力是如何基于“交往礼节”、个体尊严的需要,对主流通行的现代价值进行反向定义的审美命题。
这种“反向定义”所采取的策略,首先处理的是有关创作主体以及故事角色的“时间的体验”。比如新疆文学中的新疆时间,容易让人们滑入一种无时间的状态,似乎所有的度量一时都消失不见,时间没有形状,却又既来自于当地的自然物候,又植根于当地更深的生活经验,但这种失去度量的状态又是在一个普遍单一的自我内部发生的,这使得作家们在证明共有时间的“稀有性”与调和时间的“通用性”间犯了难。刘亮程、李娟的写作便是个中典型,对于内地读者而言,将缓慢懒散、刻意拨慢的时间视作自然,并将其看作普通人生存于其间的隐喻,着实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就大多数内地读者而言,早已视不参与自然进程、疏远四季更迭的特性为理所当然。这使得西部文学、新疆文学急欲摆脱遮蔽、证明“有用”的“自我”表白,寻获存在的“稀有价值”,变得那么迫切,那么难以忍受。韩先生分析,这种表白的迫切性,使得西部文学、新疆文学总是勉力突出叙事行为本身的效果,为这种“缓慢时间”的品格、“稀有价值”的合法进行正名,他们或是强调荒原历史的创世性,或是强调叙事行为本身的奇异,又或是描述叙事对象的灾异,“文本自身的这种‘自我强调’,与西部文本的稀缺、叙事的严重不足有关,因而总是暗示自身的重要”②。与此同时,时间的相对停滞,多少也作用于西部文学整体的文艺观念与文学行动,较之东部省份、中心城市文学现场各种文艺思潮的潮涨潮落,西部文学似乎多年如一日地在自身的叙事轨道上运转,因而显得寥落、孤寂,呈现出一个单一、缓慢而涣散的文学叙述单元。
西部文学的“自我”当然还体现在“根”与“翅”的关系之中,韩先生在书中形容这种西部文学、新疆文学的“自我”更像是“根”与“家园”施予边疆文学表述的文化压力。的确,如韩先生所言,边疆文学偏离宗族、血脉、宗法,以至于“故乡在远方”,“在路上”成为其文学书写最重要的母题形式。内地小说家的作品总是建立在一种具有持续文化传统与鲜明地方经验的文本背景之中,而西部的文学文本、新疆的文学文本却立足一种虚空,突然而至,又杳然而去。“根”(通向原乡的血脉相连)与“翅”(指向远离原乡客居他地的经验)相亲相离,“这是一个相反的命题,是因为‘缺乏’而‘强调’的命题,正因为汉文化在这里的分布更漂移、更破碎、更缺乏稳定性和持久力,但又源远流长不绝如缕,‘根’或‘家园’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些”③。也因此西部、新疆的汉语文学创作,本身内含一种自我撕扯的意识形态因素,它们总建立在一种不时渴望和拒绝迁移的基础之上,这种因素当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文化的乡愁”,而是一种介乎国家主义与区域主义之间的“认同焦虑”。
“边疆是‘混杂’、‘混淆’、‘混乱’的,它因远离‘中心’而处于不断解魅的状态。同时,它又与‘忽视’、‘遗忘’和‘不惹人注意’相同义,与‘规范’、‘规律’、‘规整’方向相反,处在‘理性’的侧面,处在‘异质’、‘陌生’和‘边远’的控制里。而所谓‘神秘’、‘原始’、‘野性’等等之类印象式判断,更是‘主流文化’的居高临下的优越心理的表露。”④你几乎分不清是中心城市文学与边疆文学文化话语间的不对称给边疆文学创作构成的压力大,还是边疆文学在现实社会里不断被肯定和高估的价值与它在文学史或文学市场既有地位中“籍籍无名”间的悖谬反差,给边疆文学创作的伤害大。在有关新疆文学、西部文学、边疆文学的想象之中,梦想与现实的反差如此强烈,强烈到西部作家、新疆作家这么多年不得不反复思考与证明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主流文学,在为其提供“养分”的同时,又不至于那么“捉襟见肘”?
此外,西部文学的“自我”,还要面对多民族母语书写与国家通用语书写间的关系问题。西部以西的新疆,既是边疆又是多民族、多种生活方式同时并置之地。即便在首府乌鲁木齐,你也能在一个时空甚至同一个人身上看见农耕、游牧、城市生活方式的并置,这使得新疆作家们不得不在寻找一个新疆人真正共有的“区域身份”与“多族群”各族身份间保持平衡。这便是沈苇诗歌中那句“混血的城”与“综合的上帝”所表达的初衷。然而,现实地看,共有的“新疆身份”与“西部身份”仍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建构的过程,在保证各民族仍然能够充分发展各自身份特征的同时,通过频繁有效的文化接触与交际,或许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更为综合的“新疆人”或者“西部人”,他们将能够洞悉其他各个民族所有的观点与诉求,成为一种“新人”,反映这种“新人”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处世经验的作品能够对建构文学上真正有效的“新疆身份”与“西部身份”有所帮助。帕蒂古丽的作品《百年血脉》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这种面向“未来身份”的写作努力。对此问题,韩先生也不无感慨地形容:“母语问题的提出,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控制性背景,这就是文化的开放与交流、比较文学的兴盛和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讨论。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开放环境中的定位问题。对写作的定位首先从语种开始,从定位的不同文化标准开始,从主流与民间、中心与边缘、自者与他者开始。也因此,母语、母语写作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个文化的接触与影响的问题。”⑤
综合韩先生在书中对“西部的自我”所思考的轨迹,可以看出他先结合自身在疆生活的经验,从大量文学文本的细节出发,指出为何西部文学有“自我”表述的焦虑,接着又抽丝剥茧地论述了西部文学体现自我的叙事策略、方法与路径,最后评价了西部文学表达“自我”的利弊,他认为这种“自我”表述一方面属于区域文学较量的必要战术,另一方面,这种“自我表述”需要“自我超越”:“如果说那时关于‘西部文学’的提法,更多地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是文学的‘边疆政策’,是对京畿的文学的中心地位提出一种挑战,从而获得某种格外关注,那么应该说,作为文学策略它是成功的。无论如何,啸聚山林的‘西部文学’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格局造成某种拉动、构现热闹的一景,它的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颓而不败,败而不死,死而不僵。”⑥但是韩先生更不无辩证地指出,这种文学策略在“策略层面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造成很难消除的后果,就是一种文学倡导变成审美强制,使一大批有才分无才分的写家不由自主地‘尽入此瓮’”⑦。他尤其指出,今天的西部文学若要概念成立,一定要超越地理的西部特征、奇异的自然景观以及某种简单直白的“西部精神”的口号,必须直面西部文化尚未得以梳理、朦胧却显豁的精神欲象,探究这片土地内部的人文精神向度。无论在他的著述中,还是在日常的读书讨论中,他都反复指出:“西部文学才不是一个狭隘的、守旧的、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的文学观念。我不是反对‘西部’,我是反对仅仅匍匐于此,把‘西部’当成‘文学特产’中的一种来兜售。”⑧他主张拒绝标签化,浅表的符号化,拒绝这种不证自明的姿态或曰主题先行的盲目自信,提出西部文学作为一种“有方向的写作”,西部的自然精神是它必须面对的书写与扎根对象。
不难发现,韩先生对西部文学的“自我”表述一方面有着充满情感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又不乏理性的反思,他认为偏远省份的文学创作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正来自于把“‘地域特色’和‘文学价值’生拉硬扯,用文学的鸵鸟政策来掩饰日趋陈旧的危机,获得小国寡民式的自高自大和沾沾自喜……它缺乏统一的尺度,就自立一些别人所稀缺的东西为尺度,它获得承认的机会相对较少,就把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转化为另一种不公平的自我想象的成功,用别人不懂不会的‘地方项目’来对付另一种普遍的流行的‘花拳绣腿’,用‘地域册封’的局部有效性来偷换为超地域册封的良好感觉”⑨。我以为,他的态度里包含一种世界眼光,总认为证明一种文学叙述比另一种文学叙述更好,浪费精力,“动机不纯”,意义不大。写作者的对手永远是他自己,自己多和自己比,不要太在意其他人。
人际间的简单道理,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城际之间、族际之间乃至区际之间。中心城市与西部文学、新疆文学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土地与乡野叙事孰重孰轻的区别,土地是玉米、沟壑……在中心城市更多是按揭房产的栖身之所。乡野则是土地流放而出的特殊空间,在其中,土壤、旷野、生物、气候能够和谐一气,没有没完没了的按揭,没有名字按笔画排序、桌签总在更新的各种机构。当然,历史地看,我们要承认,边疆文学之于内地文学的作用,历代以来便由于其所提供的“边疆养分”、“异域教诲”而难以小视,在现代化语境中,边疆地区作家的任务或许在于如何从历史中激活它们对当今时代的引导意义与价值影响,而非一味在意与中心城市文学群落的“意气之争”罢。那位仍然住在辽阔荒野中贫穷屋子里的姐妹、兄弟或许也能给住在豪宅里吃惯山珍海味的姐妹兄弟,做一顿取自自然的农家小菜。
独处的剩余
独处不仅是一种行为状态,更是一种西部人文精神的象征:“相对封闭的环境更有利于沉思而不利于对话。”⑩韩先生十分强调“独处”,认为“独处”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思考状态,也是描述西部人文精神准确的空间表征,他在《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一书中认为:“‘独处’是西部文化与西部文学的一个带有很强体验色彩的字眼,‘独处’处在‘出现’与‘消失’的边缘,处在临界的状态。‘独处’是西部文学特有的描写单元,‘独处’当然是漂泊和荒野恐惧双重交织的产物,同时它也有很强的文化特点,也可以认为是西部多元的文化存在的一个表征。”⑪“独处”就像那句时髦的表述“我想一个人静静”,也像那句俗谚所形容的“如果你想要尊严,便一个人呆在家里,穿戴整齐”,“独处”是思考的理想状态,也是对个体尊严的一种吁求与回护。
韩先生对于他所肯定的文学写作,也认为是因为其以强有力的艺术形式书写了有关独处的美学,譬如他以周涛为例,谈及周涛的写作在消费主义相对薄弱的西北和新疆,他的写作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充满着独处的剩余价值,“孤立、决绝、不为所动。诗的激情(行动)消退了,虚拟故事的繁殖消退了,剩下沉思的随笔和散文,如同时间的滤纸留住最后的积存,艺术为它的强度找到了‘适当的表达形式’”⑫。
个人独处的寂寥空间,留下了时间灰烬里珍贵的剩余之物。这种“剩余”给予韩先生文学批评一种智慧的温度,思考的喧哗以及批评的力度。这是属于他的“太初有余”。“独处的剩余”里有他对西部文学整个符号体系的思考,“独处”自身也是他所归纳的西部文学中的一个符码。“其实,通过对西部土路边的小规模的废墟、独立房子、独处、旅途、行人、歌与沙、果与舞、残缺与边余、荒野、性感的牛羊肉食物、热烈的服饰、刀子、单元性的街市、动物、陌路人相遇时的关系与态度等细节的分析,也不难找到一个西部的符码与表征系统,找到一种文学写作的叙述出路,找到关于‘剩余’和‘不足’的话题。”⑬
在这些独处的剩余时空里,他思考了有关西部文学研究将会涉及到的几乎所有主要观点、文学主题、价值、意识模式的话语与关键概念。譬如对文学价值、纯文学理想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反思,在这种反思里,他观点鲜明地主张对作者与世界关系之间、文本与意识形态话语间的肯定。“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当然不像某些哲学教员宣扬的那样,硬要从喜马拉雅山的一块石头‘普遍联系’到长江下游的某一朵浪花。但他们的确生活在这个星球转动中的某个瞬间,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关于生活的判断,他们非常独特,甚至怪异,超出常人,但他们仍不可能在写作时变成另一种好像是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的‘外星人’。”⑭在作家与作品、读者以及世界的关系之中,他格外强调与世界间的联系,认为在作家与世界的联系里其实早已包含作家与作品、读者间的关系。一味强调纯文学创作,维护文本主义的写作立场,不仅是一种不现实的写作理想,在某些时候还暗含自相矛盾、自我消解的危机:“一种普遍的情况是,一些作家以某种可疑的‘清高’姿态反复传达这样一种意思:我和我的写作是超制度、超党派、超意识形态、超民族的,我不接受任何‘敲诈’,相反,我尽可能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唱对台戏,来表明我的‘勇气’和‘行动能力’。但是,不要忘记同样的人,在涉及机构、荣誉、晋升机会、工资、社会待遇、权力和一大堆具体的物质利益时,就忘记了他的超制度、超意识形态的清高承诺,而变得很积极、寸土必争、斤斤计较了。他变成一个‘很合作’、‘很实际’、‘很世俗化’的人。”⑮
再比如对现代性的反思,韩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文化观念上主张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在文学的主题学观念上则认为是一种无需讨论的命题。“也许一方将要丢弃的东西正是另一方追求不得的东西,丢弃者以为追求者为‘现代性’,而追求者却把实际的牙慧当作梦中的宝贝呢?文学的现代性,干脆是一个不要讨论的话题,这里面存有太多的歧义和误解,认识一种立场只有在你真实地从存在上拥有它时才可以理解——理解失去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的关系”⑯。
《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一书中,也有对批评家自身的反思,包括对文学评论话语以及价值评估的反思,尤其在衡量昌耀的诗的文学地位与意义时,韩先生批评评论界失去了统一的判断,认为昌耀的诗之所以没有得到即时应有的肯定,原因在于中国诗学和批评出现了判断力上的毛病,“看不清创造”⑰。
当然,“独处”也未必总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精神面向,它或许有利于思考,能够产生智慧,但却也容易培养伤感,滋生偏执,特别当这种“独处”不被认可的时候,更会产生焦虑。韩先生不无辩证地看到“独处”对西部作家、新疆作家文化身份的影响,就像西部文学“文化身份”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样,一方面来自被豢养却又频繁失落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来自市场经济主导下自诩优越却又并不优越的社会地位,在书中,他对这种现状有一番精彩的评论:“在银河系的中心之外,密密麻麻地对垒着数不清的沉闷忧郁中的石头。他们也如那些星光闪耀的人物一样,在稠人广众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埋头于孤独中的写作、思考,观察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的变化,如同那个背运过时的手艺匠人,看着货柜里琳琅满目的时髦商品而为自己后院里堆积如山的手工艺品心酸发愁。他们对世俗的前程已不存指望,他们越来越陈旧,也越来越勤奋,他们对缪斯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忠诚,他们没有别的技艺和出路,准备就这样过下去,真正应了那句老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孤寂写作中离世界越来越远,他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成了这个环境中的陌生人,他们也无法左右自己在写作中的位置,在这一日益冷落的行当之中,仍然有新手不断加入,而且出手就不错,就赢得了他们一生才得到的掌声。”⑱
这种写作像是动荡时期内“停滞的写作”,在这本书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他特别分析了刘亮程的写作,认为他读书不多,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和文学训练,他的文学创作保持着一种直接书写的特点,他写作的初衷那样简单,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生活类型告诉大家。并以此为例推及、演绎、概括出大部分偏远地域的写作者、底层写作者的“孤独命运”,“他们因重重的遮蔽始终深陷在无法自拔、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境,而没有为更为广大的人群所了解。对他们而言,这种缺乏联系、仿佛是孤立、自在的环境是要命的。”⑲
当“独处的剩余”最终变成一片“寂静的风景”,“过度的孤寂”反而会毒害这种“一厢情愿”的写作,以至写作形象之刻板难以渗入另外的质素。而如果写作的职业热情、理想希冀与孤独处境的热烈程度同样的旗鼓相当,便多少需要一些自况为“个人英雄”的自我解嘲了,像那首民歌唱的:“世界在我眼中一如废墟,我的左脸已被情火烧伤,右脸仍将情歌唱。”
个体自身的“哑存在”
俗谚云,人情练达即文章。好的文字有粘性,像懂事的人,挣不脱,离久了,会惦记。对此,韩先生也说过,人生一切的失败都是语词的失败,就像韩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哑存在”,语词不过关,譬如行文不动脑,譬如办事不走心,你便是你自身的“哑存在”,你是你自身命运的结果。
由此联想,边疆的文学,尤其是新疆文学既是其自身庞大文化显影的遮蔽之物,又是创作主体失语之后的“哑存在”。历代至今,那么多文学家向西而行,一群人被另一群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赶向一片荒野包围的绿洲之上,在诸种关于西部的想象中,这群人中有的人怀着强烈的自我或者个体意识来到西部,来到新疆,认为自身的独立性大于集体性,认为自己的这个“我”,是一个有历史责任、忧患意识、理想情怀、自由意志的“我”;是一个懂得牺牲、善良正直的“好我”;是一个向往自由、坚持信念的“理想的我”。毕竟这些个“我”会比城镇人口密集的原乡拥有更多空间,一望无垠的荒野,一片混杂文化的天地,就像周涛可能会说,我也许没有你那么富有,但“我”一个人拥有一段边塞历史;就像董立勃会说,我也许没有你那么富有,但“我”一个人拥有一个拓荒者的乐园;就像刘亮程可能会说,我也许没有你那么富有,但“我”一个人拥有一座村庄;就像沈苇可能会说,我也许没有我在浙江的亲戚们那么富有,但“我”一个人拥有一座混血的城。梭罗怎么说的,“东行乃不得已而为之,往西则能得到自由”。
他们勤奋地写作,努力为今天输送西部的精神、“自然的自我”、“异域的教诲”,然而从韩先生写下《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至今,市面上的确未能有一本书,网络上的确未能有一部影像作品,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他们在西部、在新疆无论是祖辈支援边疆、开疆辟土轰轰烈烈的生活方式还是他们目前平淡简约的生活方式,能够在社会总体生活目标中有任何地位,书本中宣传的,各种媒体尤其是影视作品中鼓吹的,无一例外不是东部、日韩或者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生活方式为标准。董立勃的写作特别集中地反映出西部精神的某种无能为力。他在新写的短篇小说《杀瓜》中,塑造了一个被时代抛却的、“过时的人”陈草那么窝囊、憋屈、自我伤害、偃旗息鼓的一种“造反”。李娟的系列散文也只是向厌倦了城镇生活的文艺青年们证明了一种西部以西新疆地区的“小众”生活方式其背后的“怡然自得”。西部、新疆、边疆、底层的作家们在超越了一切“强媒体”与“强文字”记录的地方默默无闻、哑然失色地写作。因此,张承志、阿来的文学写作开始变得不那么“静谧”了,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在“无用”的文学修辞以外,“有用”的文化处境里发出声音,试图引导人们相信:“我们固然生活在被全球市场控制的世界中……但也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那就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物质文化往往能够抵抗征服性的、同一化的经济势力的冲击而生存下来。”⑳这种情形就是韩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文学地位与文化处境的反差,并且愈来愈大。“……消费文化怎样和宗教精神同时发达起来,震惊和失语相同步,难言的感受日益尖锐也日益孤独。每个人都只与自己心智相当的朋友议论它,但又似乎不愿诉诸文字,就这样暗守着一个内心的轩然大波。”㉑
西部、新疆或者说边疆所提供给个体的理想在于生活在自然之中,东部地区发达城镇提供给个体的理想则是与高科技、工业化的机器为伴。我们尊重西部,因为自然造就了我们,我们肯定东部,因为技术让我们趋于“完美”。“西部的危机”或者说西部文学“哑存在”的困境当然也来自于现代化以及高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个体理想的裂变——自然理想的“哑存在”使然,西部文学、新疆文学的困境在于作家没法在“顺应自然”与“追求技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梦想中保持同样强烈的渴求而不至自我分裂,这就像读者对西部生活、新疆生活的想象也很不一致一样,他们不得不时刻在两种理想认同中做出选择。起初那些主动选择向西出发,涌向自由自然荒野的“我们”不得不向“我们”所逃离或者被驱逐的“城市文化”表示“认可”,这意味着这些个“我”必须既前进又后退,后退似乎会被“文化消费”,前进又会认可自身长期的“哑存在”,既怀念过去又向往未来,在进退维谷中重新“自我殖民”。
然而,现代化语境中,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无论前进还是后退,“贫困”都不会是一幅诱人的图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我们成长的履历、我们获得社会身份的评估体系都在铿锵有力地否定“贫困”,都在指向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实际与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份可以活命的工作,一个家,一次缓解压力的出轨,一次工作之余的旅行。“自然”与“自由”似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就,在既有的教育、阅读、交往与评估体系中,似乎难以被清晰地加以辨识。在近年来几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动荡之后,西部人、新疆人似乎也比过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更加矛盾、痛切而别扭地,却又不得不逼迫自己承认这种“哑存在”
韩先生对边疆文学文化身份的反思极其深刻,他比喻西部作家不得不成为自我观念的“殖民者”,并打比方认为偏僻省份的写作者作为次子,难以继承大统,就像是一个在台下永远看着话筒发言的人,“你是一种有待证实、填充和肯定的假设,你不可能像了解人家那样要去人家也同样了解你,你只有踮起脚尖才能理解一个祖宗八辈居住在京畿之地的文坛阔少。不是这样吗?你是这里的一流似乎只能是这里的一流,而他即使是三流那也是全国的三流,也有理由在你房间里颐指气使。在这里,优先权是丧失后的再度丧失,不存在什么共享性的原则。”㉒“在一个大国的文学里,有了一片这样的夜景:在中心区域和沿海地区,文学的星空如同无数星辰组成旋转燃烧的银河系,群星璀璨、相互辉映,炽热的光源和良好的反射能力,使得那里如同白昼。而在这个庞大的银河系外,在更为广阔、神秘的夜幕里,那些流落偏远的星子稀稀拉拉地点缀着,显得有些冷清。其实在这广阔的夜幕中,可能有更多的石头和火焰在运行,如果说在数量上不是更多的话,那也决不会更少,但他们是一群‘哑存在’,是一群处在遗忘和隐匿中的倒霉蛋。”㉓
他在分析昌耀的诗歌时,尤其痛切地指出,昌耀的诗歌创作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哑存在”,“昌耀这个居于偏僻之地的倒霉鬼只能自己救自己”㉔,“难以理解的不是偏僻,而是对偏僻的无形的轻视和歧视”㉕。这让西部作家、新疆作家或者说边疆作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写作现实,倘若“我们”并不能接受多年以来“哑存在”的文化身份,便不得不承认:与我们过去所塑造的西部、边疆作为躲避竞争、逃离快速进步的“荒野”、自由“飞地”的文化身份截然相反的是,它恰恰处在现代化进程、城市大开发最“激动人心”的阵地前沿,处在一切变动发展最为迅疾而难以下断言的地带,它无法一再怀念它过去所拥有的纯真、偏僻、简陋与质朴的本质,而是接受它逐渐成为荒野上那个贫困小屋,将被改造成城镇洋房中后进的、并不完美的一员,那位在荒野小屋中外表贫弱的姐妹、兄弟不得不接受他/她那些富有表亲们来到家里“颐指气使”的炫耀。
但是,就像韩先生在书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区域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历史塑形、边地想象,突然间要改变装扮,哪有那么容易,这就好比一个经历过青春期的个体很难真正重新激情一把,一个超越“哑存在”的全新文化身份的塑造,或许将不得不使西部、新疆的作家个体暂别过去,成为他们自身的外乡人。“一个人20岁以后就难有朋友了……你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如同一个热铁块从橘黄色变得暗红再变得冰冷灰暗,再也渗不进一点东西。你的过程就在此时似乎已经中断了,你的内部已经塞满了无法理清的各种东西,环境再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你,之后的一切作用只能使你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现在的生活性质的迅速变化,已经使‘过去’有世纪之遥,好像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我们已经中断了和记忆、经验及经历的联系。这使我们看起来像自己的‘外乡人’”。
如果,作为对个体“哑存在”的抗争,能够在坚持自我的前提下发生,即西部、新疆的作家们能够“自我安慰”地说西部、新疆、边疆、底层的文学权力只是暂时被低估了,能够忍受自己“一时谦虚”地将自己打扮成文学史中的配角,或者忍受自己“一时委屈”地扮演成联欢舞会上那位唱歌跳舞的小姑娘,他们仍然像多年前韩先生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只管耕耘,不计较收获,既不天真浪漫地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加以分离,又不一味自大地视自我存在的价值为理所当然,把“过去”当作“未来”,继续更加努力地发掘或者说重新赋予西部、新疆、边疆文学在当代社会总体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履行长期以来西部文学、新疆文学、边疆文学、底层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承诺,使其能够真正赋予当下生活中的普通个体以精神力量,它是否才能真的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自我反思,更加懂得人文精神?并在它辽阔的地图空白之处收容进这些看似无用的“荒地”、“旷野”、“边界线”与“牧场”,并不会因为大部分中心城镇生活的人们无法到达那里,而否定它们的价值?
这些疑惑,韩先生的书中没有给出答案,作为生在成都,长在新疆的我,突然有一瞬,就在写文的此刻,不那么执着于听到答案了。我想起他在《大声说话》后记中所整理的启程心情:“我感觉,这样下去,我的生活会越来越被动,我的生命会越来越老旧,我在重复、停滞,像个破旧的放录机,老要倒带才能快进,缺乏挑战和刺激。我已经开始老了,但还能动,我得挪挪窝、换换地”。韩先生他来自祖国边疆辽阔的“荒野”,却突然有一天感到无法从中汲取到力量,于是他决定重新启程,向东逆向,荒野上仍然有他留下的小屋,收容西部文学中的行旅之人。
无论在东在西,也无所谓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韩先生都说:“我的新疆之爱——纵到底、横到边。”这位荒野筑居者,他心中的小屋,筑基于荒野,却不依赖任何事物,总能对出现在他小屋门阶上的任何人迹或声响做出回应。
不信,行旅在西部文学无边旷野中的朋友们,当你孤单时,敲一敲韩先生建筑在荒野上的小屋,茫茫原野之上,必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