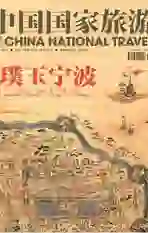远洋古道,另一场传奇漂流
2015-09-10麦克·山下
笼罩在郑和身上的神秘色彩使我着迷。沿着他的足迹,我踏上连通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个向全世界讲述这位伟大探险家的机会,他的很多故事不为人知,也从来没有人用照片去讲述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史诗般的冒险历程。
作为一个专门拍摄远东地区的摄影师,我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亚洲,总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关于亚洲的各种信息,我为此感到骄傲。尽管如此,当我第一次听说“郑和”这个名字时,还是感到完全陌生。
郑和是亚洲最伟大的探险家,他指挥着船队探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那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有多达300艘船只,其中有些长达400英尺(约122米),配备士兵30000人。

郑和身形伟岸,身高将近两米,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时代到来之前,他领导了7次大规模的世界远航,足以使其他任何一个我所了解的探险家相形见绌。他7次出海造访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旅程最远到达中东和非洲沿岸,比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早了90年。
追随这位杰出的中国探险家的足迹,我踏上了重走郑和远洋古道的旅程。在这条连通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有过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在内的很多航海探险者的足迹。
在郑和的时代,风力主导并引领着航海者的方向。11、12月的东北季风,使船只从中国沿海顺风南下至越南、婆罗洲、马来半岛,最后到达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在那里,船队要等待5个月,然后借东南季风从马六甲海峡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当风向再次变化时,船队从阿拉伯半岛顺风南下,到达非洲沿岸诸国——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那里,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非常繁荣的贸易。
我梦想着可以乘船完成大部分航行——最好是中式帆船和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遗憾的是,中国的渔船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目前大多数船只都是用玻璃纤维或钢铁建造的。寻找阿拉伯帆船的愿望也落空了。阿曼是我进入阿拉伯半岛的第一站,它已经成为中东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老城和要塞已经重建过,15世纪时的历史痕迹,消失在那些超级现代的露天剧场里。
为了展现郑和曾经走过的海上古丝路,我要前往他到访过的超过37个国家的停靠港,寻找他曾经进行过贸易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的物品,体验他所经历过的陌生的习俗与文化,重现15世纪亚洲的航海世界。
实际上,今天能证明郑和令人惊叹的7次航海的证据少之又少。随着15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闭关,政策转向保守,关于郑和的大量记载和航海日志,在他最后一次返航后被有意销毁,只有时任郑和船上的两名通事——穆斯林学者马欢和费信的记载得以保留。他们对航海生活的描述,以及对登岸后的观察见闻,成为今天揭示郑和之谜、了解他足迹所至之地的主要资料来源。
我从故纸堆里找到了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以摄影师的视角规划着我希望拍摄的画面。
郑和船队的海外第一站是越南,目的是寻找珍贵的木材、朝天犀牛角、象牙、热带水果和槟榔。

在越南寻找600多年前郑和可能见证过的场景并不难,湄公河沿岸的生活节奏依然故我,渔民们依旧靠人工拉网,头戴圆锥形帽子的妇女依然在辛苦忙碌。
郑和的船队从越南前往泰国(暹罗),这个国家给船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船员通事记载:“如果已婚妇女和来自我们船队的人非常亲密,他们就喝酒,吃东西,举止亲密,而她们的丈夫对此很平静,不会反对。”
我选择了拍摄大城府阿玉托纳(Ayuthaya),1407年郑和抵达时,它是暹罗的首都。让我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在建于14世纪的帕楠称寺,郑和被当地人称作三宝公,并被奉为财神来膜拜。人们为他修建了21米高的黄金坐像,崇拜者们将橙黄色的丝织品抛向雕像,丝巾的另一端盖住自己的头,几百名僧人在旁边的房间齐声诵经。从庙宇的宏伟程度及装饰过的地面来看,郑和应该是满足了许多祈祷者关于财富的诉求。
马六甲曾是南中国海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郑和将这里作为重要的中国海外移民地,他在马六甲建立粮仓和货栈,方便船队储藏物品和获得新鲜补给,以便继续北上或者南下。
我到达马六甲时,正值印度教最重要的节日datak chachar,信徒们为了向神明表达感谢,会用针刺进自己的身体,用鱼钩穿进体内,这些都是在一种恍惚状态下完成的,没有流血,似乎也没有疼痛。

黎明时分,我到达旧城中最古老的庙宇——兴都印度庙,朝圣者聚集在这里,准备接受严酷考验。他们大多数是华人,是最早一批中国移民的后代,有些人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郑和时代。郑和的船队走到哪儿,中国的移民就散播到哪儿。大批中国人移居到东南亚,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在马六甲海峡,华人文化和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海外华人的后代开始信奉印度教,有些人甚至近乎狂热。
郑和6个世纪前的7次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麦克·山下搜集了每一段关于郑和航行的记载,重访了这30多个地标,追随着这位“被遗忘的船长”,穿越了整条古老的航海路线:
中国—越南—文莱—印尼—爪哇—日惹—巴厘岛—柬埔寨—吴哥—泰国—大城府—马来西亚—马六甲—斯里兰卡—印度—卡利卡特—科泽科德—喀拉拉邦—古吉拉特邦—卡拉里—阿曼—穆桑达姆半岛—苏尔—阿联酋—也门—萨那—吉布拉—肯尼亚—马林迪—拉姆群岛—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了解更多麦克·山下寻访郑和远洋路线的故事,可关注《镜头下的航海史诗》一书。
1371年,郑和出生在云南一个穆斯林家庭。11岁那年,他在战乱中遭受宫刑,被押送到南京服侍宫廷,后来成为太子朱棣的亲信。朱棣称帝后,派郑和率大型船队出使南海,郑和身担外交、贸易、探险的重任,他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带到海外,换取种子、珠宝、珍贵木材、药材、纺织品和矿产。1405-1433年,郑和的7次航行为中国带回大量财富,奠定了明王朝世界超级强国的地位,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为一个专门拍摄远东地区的摄影师,我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亚洲,总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关于亚洲的各种信息,我为此感到骄傲。尽管如此,当我第一次听说“郑和”这个名字时,还是感到完全陌生。
郑和是亚洲最伟大的探险家,他指挥着船队探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那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有多达300艘船只,其中有些长达400英尺(约122米),配备士兵30000人。
郑和身形伟岸,身高将近两米,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时代到来之前,他领导了7次大规模的世界远航,足以使其他任何一个我所了解的探险家相形见绌。他7次出海造访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旅程最远到达中东和非洲沿岸,比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早了90年。
追随这位杰出的中国探险家的足迹,我踏上了重走郑和远洋古道的旅程。在这条连通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有过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在内的很多航海探险者的足迹。
在郑和的时代,风力主导并引领着航海者的方向。11、12月的东北季风,使船只从中国沿海顺风南下至越南、婆罗洲、马来半岛,最后到达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在那里,船队要等待5个月,然后借东南季风从马六甲海峡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当风向再次变化时,船队从阿拉伯半岛顺风南下,到达非洲沿岸诸国——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那里,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非常繁荣的贸易。
我梦想着可以乘船完成大部分航行——最好是中式帆船和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遗憾的是,中国的渔船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目前大多数船只都是用玻璃纤维或钢铁建造的。寻找阿拉伯帆船的愿望也落空了。阿曼是我进入阿拉伯半岛的第一站,它已经成为中东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老城和要塞已经重建过,15世纪时的历史痕迹,消失在那些超级现代的露天剧场里。
为了展现郑和曾经走过的海上古丝路,我要前往他到访过的超过37个国家的停靠港,寻找他曾经进行过贸易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的物品,体验他所经历过的陌生的习俗与文化,重现15世纪亚洲的航海世界。
实际上,今天能证明郑和令人惊叹的7次航海的证据少之又少。随着15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闭关,政策转向保守,关于郑和的大量记载和航海日志,在他最后一次返航后被有意销毁,只有时任郑和船上的两名通事——穆斯林学者马欢和费信的记载得以保留。他们对航海生活的描述,以及对登岸后的观察见闻,成为今天揭示郑和之谜、了解他足迹所至之地的主要资料来源。
我从故纸堆里找到了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以摄影师的视角规划着我希望拍摄的画面。
郑和船队的海外第一站是越南,目的是寻找珍贵的木材、朝天犀牛角、象牙、热带水果和槟榔。
在越南寻找600多年前郑和可能见证过的场景并不难,湄公河沿岸的生活节奏依然故我,渔民们依旧靠人工拉网,头戴圆锥形帽子的妇女依然在辛苦忙碌。
郑和的船队从越南前往泰国(暹罗),这个国家给船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根据船员通事记载:“如果已婚妇女和来自我们船队的人非常亲密,他们就喝酒,吃东西,举止亲密,而她们的丈夫对此很平静,不会反对。”
我选择了拍摄大城府阿玉托纳(Ayuthaya),1407年郑和抵达时,它是暹罗的首都。让我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在建于14世纪的帕楠称寺,郑和被当地人称作三宝公,并被奉为财神来膜拜。人们为他修建了21米高的黄金坐像,崇拜者们将橙黄色的丝织品抛向雕像,丝巾的另一端盖住自己的头,几百名僧人在旁边的房间齐声诵经。从庙宇的宏伟程度及装饰过的地面来看,郑和应该是满足了许多祈祷者关于财富的诉求。
马六甲曾是南中国海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郑和将这里作为重要的中国海外移民地,他在马六甲建立粮仓和货栈,方便船队储藏物品和获得新鲜补给,以便继续北上或者南下。
我到达马六甲时,正值印度教最重要的节日datak chachar,信徒们为了向神明表达感谢,会用针刺进自己的身体,用鱼钩穿进体内,这些都是在一种恍惚状态下完成的,没有流血,似乎也没有疼痛。
黎明时分,我到达旧城中最古老的庙宇——兴都印度庙,朝圣者聚集在这里,准备接受严酷考验。他们大多数是华人,是最早一批中国移民的后代,有些人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郑和时代。郑和的船队走到哪儿,中国的移民就散播到哪儿。大批中国人移居到东南亚,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在马六甲海峡,华人文化和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海外华人的后代开始信奉印度教,有些人甚至近乎狂热。
在也门,我看到的场景与郑和船队的通事马欢所描述的完全一致:男人们穿着束腰外衣,系着刺绣腰带,挂着镶满宝石的匕首;女人们头戴面纱;建筑物都是泥和砖混合的多层建筑。这大概就是辛巴达航海故事中的画面(有人说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郑和)。
也门首都萨那是我遇到过的最上镜的中东城市,我迫不及待地冲向了al mikh集市,它由外表华丽的砖泥建筑所包围,仿佛是一个开放式博物馆,一下子将我带回了郑和时代。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卖乳香的摊位——凭借味道就可以准确定位。为保存乳香浓郁甜美的芬芳,人们将其汁液贮藏在抽屉里,当乳香被用作焚香时,香味更加浓郁。
肯尼亚的拉姆群岛,14世纪贸易曾经相当繁荣,它得以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如今人们可以搭乘不太靠谱的航班到达附近岛屿,或者和我一样,驾车沿海岸线行驶,然后搭上一艘独桅帆船,用大约一个小时穿过岛上浅浅的死水区域。
传说,1418年,当郑和的船队在此停泊时,300多条船中的一条搁浅,船上的水手在当地定居下来,和当地妇女结婚,并以家乡的港口“上海”来命名这个村子——“上啊”(shangga)。当地人依旧保留着成堆的明代陶器碎片,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的最后一站,是现在附属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它也是当年郑和船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片岛屿拉近了我与郑和的距离,我越来越了解他,也越发喜欢他。

在一个极适合拍照的日子,我坐在一片名为“马特姆维”的白色沙滩上,那些单桅渔船扬起帆,排成一列纵队驶向渔场,收海藻的妇女们从我镜头前走过,身上裹着五颜六色的当地服装——基科伊(KiKoi)。
也许,郑和当年也曾亲眼见证过同样的场景。我想象着:郑和率领他庞大的船队出航,满载用来交换象牙和香料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他成功完成了任务,世界最远端的人民为他献上贡物,这一切一定使他感到满足;航程即将结束时,他无疑渴望带着所有的收获启程回家,这美丽的光线和景色,与他的家乡有着天壤之别,离开这一切,一定也让他感到些许悲伤。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追寻郑和的足迹到达了世界最远的角落,即将返回的时刻,百感交集。回家,意味着又一次冒险的结束。不知郑和当年是否曾经意识到,当他结束了最后一次航行踏上回乡之路时,他正走向一个传奇时代的尾声,那同时也是古中国称霸海上600年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