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到此为止
2015-09-10思郁
思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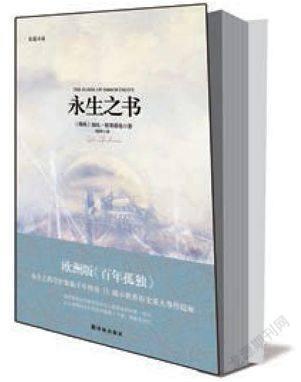
《永生之书》[ 瑞典] 加比·格莱希曼著,钱峰译译林出版社2014 年12 月
我们习惯中称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写作,真实正隐藏在这宏大的虚构叙事当中。当小说家在小说中说,他书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我们不要忘了他运用的正是以假乱真的虚构写实。就算正统的历史写作,起始的源头仍然是神话和传奇,虚构的要义正蕴含在我们的历史神话当中。所以,我们毫不奇怪,《永生之书》中,他们悬置了那本重要的线索,那本据说有一千零一页,包含了世上所有的秘密和智慧的结晶的《永生之书》,由他们家族中的本杰明·斯宾诺莎写成的一本具有神秘力量的书,正如所有的神性之书,我们无法知道书中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只知道因为这本书带来了多少的灾难,正如罗素所言,一本书就是一本灾难。但是写出这样一本书是所有写作者的梦想,可以寫出一本这样的书,一本传世的原型之书,但是最终这样的书只能出现在小说之中,虚构成就了幻想。
瑞典作家加比·格莱希曼的《永生之书》讲述了一个犹太家族千年秘史。他们几乎参与了人类历史当中所有重要的事件,这个家族如此庞大,枝蔓复杂,代代相承,为了守护《永生之书》付出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当小说的叙述者完成这本《永生之书》的小说,讲述了他们家族千年的传奇故事之后,他把家族中时代守护的书带进了坟墓,“除了我的文字,我什么也没留下。本杰明的书,我们家族的宝藏,我都一并带进了坟墓。每一个烟鬼都不愿意戒烟的,我的烟瘾即使癌症也治愈不了,每一次我写完一页,我就会从本杰明的书里撕下一页,用它来卷烟草,然后享受地吸食”。
换句话说,当他完成了自己的《永生之书》,完成了对家族历史的讲述,将他们家族中时代守护的神性之书带进了坟墓——他用了另外一种形式传承他们的家族,用另一本《永生之书》代替原来的《永生之书》,用讲述的故事,用家族的传奇,代替了那本神性之书。这到底是出于一个写作者的傲慢,还是出于一个讲故事人的荣耀?
平心而论,这本厚达五百多页的小说阅读的过程十分酣畅,绝非那种佶屈聱牙的卖弄之作。但是一个故事如何讲述,需要很多的技巧。小说的叙述者同样受到极大的困扰,“我喜欢自己在童年时期第一次听说的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再一次在我的文章中活过来。我希望,读者能像我们小时候听叔祖父说故事时那样也觉得这些人物是如此地接近自己,如此地真实。”但是一个写作者总是有某些局限,比如他只能写他能写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写他想写的东西。最终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感觉我基本写出来的都是十分肤浅的小故事。我想还原那些人的真实生活,却只能写出这些苍白的流水账”。这些确实是这本小说最大的问题,千年的家族历史,出场的人物轮番登场,我们却只能通过极力的想象,拨开历史的迷雾,尽量还原他们身上的一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听来的故事都是鲜活无比的,而落笔在纸上的那一刻却古板生硬,仿佛被钉在了纸上,失去了原本鲜活的生命。
加比·格莱希曼如此着迷于讲故事的人,很显然受到本雅明的影响:讲故事的技艺正在消亡,一个精彩讲述故事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好比我们最不可或缺的能力,现在被剥夺了:这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只有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了解《永生之书》的结局,当他写下家族的秘史的时刻,就意味着他写下了永恒。这个故事从此被固定在书页之中,再也不会通过一代代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故事到此为止,故事死了,《永生之书》注定枯萎,灭亡,灰飞烟灭,让我们回想小说最后一个句子:这一刻,《永生之书》的最后一页正化作烟雾,缭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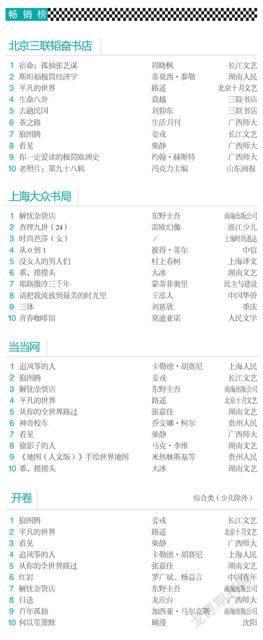
新书推荐
《追寻特洛伊》

作者从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对特洛伊传说的孜孜探求与发现入手,整合前人的贡献并进行深入考察。他走遍西亚和北非,寻找据信来自特洛伊时代的文物,并根据《荷马史诗》、诸多文献以及后来的研究逐一验证真伪,并将考察范围从特洛伊扩展至阿伽门农的帝国,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中探寻古代地中海文明中的特洛伊。作者秉持一贯的严谨态度和幽默精神,以生动有趣的文字带领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特洛伊是否真实存在过。
《寻欢作乐者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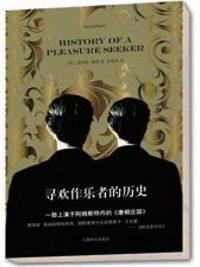
一战前,年轻的皮特·巴罗尔开始了他野心勃勃的人生冒险家之旅。不过,与女主人的危险游戏几乎使他苦心规划的锦绣前程毁于一旦……本书是一部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的出色作品,小说不但具有18世纪英国小说的传统特色,在写作手法上更是大量采用了闪回、穿插和蒙太奇等现代小说的叙述手法。小说主人公皮特·巴罗尔与王尔德笔下《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道连·格雷十分相似,可以看作是一部向王尔德致敬的作品。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本书是毛姆多部短篇小说的合集,收录《雨》、《檀香山》、《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等共三十篇,小说背景从英国到法国、西班牙,再到南太平洋的海岸边,演绎了一段又一段精彩而令人难忘的故事,不仅体现了毛姆高超的短篇小说技法,而且是对人性再度冷静而客观的剖析。马尔克斯也很喜欢他的小说,他说:“毛姆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 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