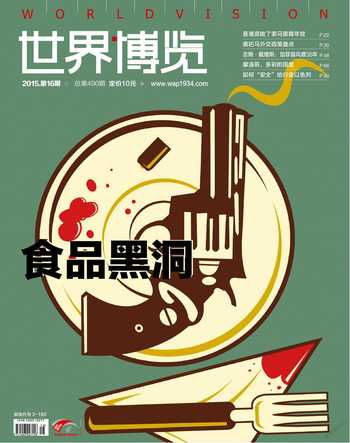用鲜血凝成的中俄友谊
2015-09-10李景贤
李景贤

在二战中,中苏军民并肩战斗,竭尽全力互相支援,而中国抗日战场的不断壮大,是对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最强有力支持。
今年是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中俄领导人决定共同庆祝这一盛大节日,并参加对方举行的盛大庆典。普京总统曾说过,俄中两国人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大盟友,其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今年5月7日,习近平主席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在《俄罗斯报》撰文,回顾了中俄共同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段光辉历史,指出两国人民在这期间一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并肩战斗。中俄人民的战斗友谊,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刚刚成立的那些峥嵘岁月。
中国人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上世纪70年代,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期间,曾到过一些城市访问侨胞。有些人告诉我,其祖辈、父辈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到俄国谋生,还“帮列宁打过白匪”,因见不到文字记载,一直不知其详。近读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在十月革命前,就有数十万华工以各种不同方式抵达俄罗斯,而且约有五万人在十月革命一胜利,就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剿匪战争。1919年春,列宁接见了红军第4团第3营的全体中国官兵,盛赞他们为打击邓尼金等白匪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90年代末,我在驻乌兹别克斯坦工作期间,听一位俄罗斯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中苏交恶那些年,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一些城市拆除了为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而牺牲的中国烈士之墓,但这一做法在他家乡高加索的弗拉季卡夫卡兹,却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而没被执行。
以上故事形象地表明,早在一百年前,中俄人民就已经用鲜血结成了兄弟般情谊,这破解了长期藏在我心间一大疑团,为何在列宁墓后面的克里姆林宫一面墙上,用金字刻着两个一尺见方的铭牌“Жанг-1917”,“Ван-1917”,意思是:“1917年的张”“1917年的王”。在墙上,我还见到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加加林(苏联,也是全球第一位宇航员)、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前第一书记)等名人同样大小的铭牌(牌后洞穴内安放着骨灰)。原来,上述两块写着“张”“王”的铭牌,是为纪念捍卫苏维埃政权(1917年具有象征意义,指当年十月革命后几年的剿匪战争)而牺牲的中国烈士们,所立的以这两个姓氏为代表的中国无名烈士墓碑。
中俄两国人民一百年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在二十多年后的二战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苏联空军勇士们的壮举
1991年初,中苏双方商定,江泽民总书记将于五月中旬正式访问苏联。此访由中联部负责组团,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让我脱产到中联部,参加访问的准备工作。我当时在外交部任苏欧司副司长,主管苏联方面的工作。
在提供给江总书记参阅的十几份材料中,有一份专门介绍在二战和新中国建设中,为中苏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苏方人士。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在访苏期间,最好安排一次与尚健在的上述人士友好会见,他亲自点了两位人士的名字:曾任苏联援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和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西林。江总书记还特别提到,在参阅材料中,有一位名叫库里申科的烈士,他是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大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其遗孀曾来过中国为这位烈士扫墓。江总书记让我们把这位烈士的遗孀也列入邀请名单中。
两天过后,江总书记对我说,他在不同时期,曾多次到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使馆又大又漂亮,与苏联友人的会见,可考虑安排在那里举行,这样,这些友好人士会有一种重回中国的亲切感。
5月16日下午四时,江泽民总书记与苏方友好人士的会见,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举行。我粗略地数了一下,前来参加会见的友人有四十多位,其中约一半穿着苏军礼服,在上衣左上方,一排排勋章、奖章数不胜数,光彩照人。这些老战士中,有的曾是苏联援华航空队飞行员,有的则参加过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他们见到江泽民总书记,都兴奋异常,纷纷回忆起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军的光荣岁月。库里申科的遗孀加丽娜·库里申科紧紧地握着江总书记的手,我站在两人旁边,只见得她双眼闪着泪花,激动地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说:1958年10月1日,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观礼,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深情地对她说:“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库里申科同志的!”江总书记听后引用莫斯科无名烈士墓一句碑文深沉地说:库里申科同志的“功勋永垂不朽”!
有一位老飞行员绘声绘色地向江总书记描述一次突袭日军在台湾机场的情景。钱其琛外长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访问期间与我方译员一道,跟在江总书记身旁,随时回答他提出有关苏联和中苏关系的问题。关于这次空袭的神奇故事,我在场听得真真切切。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苏联轰炸机群从武汉起飞后,一直在四千米左右的高空上飞行。当时,战机上都没有供氧装置,飞行员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着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他们飞入福建领空后,按照指挥长的指令,把战机的高度下降一半左右,在约两千米的空中就可以较多吸入氧气,吸饱氧后又把战机升回到原来高度,继续往东飞行。二十八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后,找准日军在台湾某机场,立即倾泻下约三百枚重型炸弹,把停机坪上三四十架日军飞机顿时炸得七零八落,把三四个油库也倾刻炸成一片火海。二十八名飞行员见状兴奋不已,异口同声地在空中一遍遍高呼“乌拉(万岁)!乌拉!”。江总书记听后也兴奋不已,连声赞道:炸得好!炸得痛快!
牵制日德东西夹击苏联
在二战中,中苏军民并肩战斗,竭尽全力互相支援,而中国抗日战场的不断壮大,是对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最强有力支持。1973年秋,苏联副外长贾丕才(汉学家,我们私下称他为“老贾”),在苏外交别墅与我国驻苏大使刘新权一道,回忆起中苏两国军民在二战中相互支持的种种事例。我给他们两人当的翻译。并做了详细记录。
老贾对刘大使说,1941年6月中旬,毛泽东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希特勒将于下旬进攻苏联。斯大林立即给毛泽东回了一封感谢电,说这一情报印证了他通过其他可靠渠道所得到的同样情报。此外,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从德军总参谋部一名军官那里,了解到希特勒六月下旬要进攻苏联的情报。蒋介石也立即把这份“厚礼”送给了斯大林。6月22日清晨四时,希特勒投入几百万大军,从苏联西部、北部三条战线突然发动空前规模的侵略战争。
老贾还对刘大使说,当年10月初,将近两百万德国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放下狂言: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上,不是斯大林检阅苏联军队,而是他希特勒检阅德国的“胜利之师”。在这个危急关头,斯大林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从七八千里之外的远东地区,静悄悄地调出三四十个师支援莫斯科战线,而这二三十万人是为了预防日本与德国相配合,东西夹击苏联而部署在那里的。12月初,德军在苏军的沉重打击下,便开始从莫斯科郊外败退,希特勒不可战胜的神话便不攻自破。老贾强调说,斯大林之所以敢于做出这样一个战略决策,是因为他判断,中国抗日这个大战场,把几百万日军死死拖住,使其无法北上进犯苏联。他还说,希特勒一直要求日军参谋本部,派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尽快入侵苏联东部。日军参谋部“北上派”与“南下派”为此争论不休,正因为中国军民的英勇顽强抗击日军,才让“北上派”与德军东西夹击苏联的图谋没能得逞。
老贾从历史经纬的角度,回顾了“东线”对“西线”无可估量的巨大支持。他说,希特勒上台后,一直垂涎于苏联的广阔领土和丰富资源,其“长线打算”是把苏联从欧洲地图上“一笔勾销”。由于英法当时的政权对希特勒采取“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希特勒很快便在欧洲中部连连得手。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斯大林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一年十个月。而在二战前夕,苏军在中、苏、朝、蒙边境地带,两次出重兵大败日军。这一对日军的惨重打击,使其再也不敢从东边对苏联轻举妄动,让苏军得以免遭背腹受敌的兵家大忌。
向斯大林请缨上战场
还有个例子让我深受感动。1996年2月6日,斯大林的孙子叶甫根尼·朱加什维利与我(时任驻格鲁吉亚大使)一道观看新拍的故事片《雅科夫——斯大林的儿子》(他本人出演其祖父斯大林)后,告诉我一个“大秘密”。他说:“祖父(指斯大林)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第二天,一名叫‘谢廖沙’的中国年轻学生,给我祖父写了一封请战书,坚决要求上前线打法西斯匪军,信的落款是‘毛泽东的儿子’。” 这是毛岸英,时年18岁。我问:“你祖父批准了吗?”他答道:“你觉得这可能吗?他可不是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斯大林的长子,即叶甫盖尼的父亲,于希特勒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当天,就被斯大林派上战场,后来英勇牺牲在德国一个集中营),而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22岁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时,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装走出机舱,给往迎的毛泽东同志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来,他后来在苏联参了军。
我听了这个感人故事后,告诉斯大林的孙子:“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把自己的长子,就是这个‘谢廖沙’送上了前线,他淡淡地说: 我毛泽东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这位格鲁吉亚朋友听后声音低沉地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故事我听说过,他的儿子也没有能够回到他身边。”
凝思了一会儿,他深情地说:“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格鲁吉亚人,这两位影响过历史发展进程的伟人,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其做法却惊人地相似:战争一开始,就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的亲生长子送上了前线,而且连出发点都一模一样——我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而且,毛泽东同志的儿子当年还向苏军统帅请缨上前线去打法西斯匪军,他这是要为苏联而战啊!这真是两位伟大的父亲!两位伟大的儿子!”之后,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两位伟大的统帅!两位伟大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