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能除千年暗(外二篇)
2015-09-10张佐香
张佐香
魏晋的一个月夜,嵇康手持精致的七弦琴,一路踏歌而行,往山间的华阳亭走去。古琴是有关嵇康的一个关键词,那看似简单的七根弦上蕴藉着他独特的气息、个性和精神内核。他身披罗绸短衫,盘坐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长夜里,十指轻搭,七弦有节奏地和着松风吟唱。那琴声如同天籁,缥缈、低缓、婉转,仿佛清澈的溪流静静地淌过水底发白的石头,仿佛雾霭一点点地浸染静谧的暮色,若有若无,时隐时现。身逢乱世,白骨横野的残暴和污浊不堪的现实,令他苦闷忧伤、愤慨绝望。琴声滑过愤慨的心灵,飞出尘世的夹缝,在一片皎洁如水的月华中寻求几许清淡。
嵇康可谓天人。他心如朗月,情深意真,寄形于天地间,而不为天地所拘。他用高贵的人格喂养了不屈的生命。乱世之秋,人命如草芥。阮籍为求自保,不得不与司马氏虚与委蛇。嵇康不像阮籍那样“口不藏否人物”,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不愿与阴谋篡位的司马昭同流合污,毅然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宁愿在乡间靠打铁为生。昔日好友山涛投奔司马昭后举荐他为官,他愤然写下绝交书,与之断交,称“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友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也”。嵇康,那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魏晋名士的精神气韵的神像。
司马昭的功臣钟会,听闻嵇康大名,前去拜访,欲劝他为官。钟会到他家时,嵇康正在打铁,一声不响,旁若无人,扬锤不辍。钟会悻悻然起身要离去。嵇康問:“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不愿中断打铁的兴致而怠慢了他。钟会恼羞成怒,回到主子身边就添枝加叶捏造罪证,说嵇康锻造兵器,有谋反之心,论断他的罪状是“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不杀“无以清洁王道”。
一千多年前一个寒冷的清晨,嵇康坐着囚车走向刑场。三千余名太学生尾随其后,欲上书,请以为师。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为他鸣冤叫屈,其人格感召力可想而知。面对刽子手雪亮的屠刀,他提出了平生最后一个要求:弹一支曲子。他神情冷傲俊逸,如同坐在华阳亭无边的夜色里。一股势不可挡的音乐急流,从他的手指间奔涌而出。山洪暴发出了怒号,黄河吼出了决堤的狂啸,千万匹腾空的野马在嘶鸣,大地塌陷了,灵魂撕裂了,雄浑激越悲壮的曲调淹没了所有人。
嵇康临终时弹的那支曲子就是《广陵散》。这首古曲写的是战国时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王的故事。只有嵇康这样刚直崇高的人,才能弹出这支古曲气势磅礴的真味。嵇康坚守自己的人格风范,听从心灵的旨意生活,他为此献出了珠玉之身,像彗星那样,在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倏忽消逝,但他却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串清晰坚实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千载之下,我时常想起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超逸风姿,独立于高天阔地之间,用他那高洁的手指,重重地拨击着琴弦,拨击世人的心魂。
伟辞贯日月
每逢端午,我总会被行吟的屈子所触。鲜绿的粽叶作毯,千万龙舟护航,无数的人们为屈原招魂,我手执《楚辞》,寻他斑驳的影迹。
屈原诞生于战国末期的楚国。他吟诵着楚辞的旋律,走过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漫长之旅,至今还在观望当代生活,参与我们的人生。屈原为楚国王室贵胄,博闻强记,娴于辞令,明察古今兴亡,洞悉纵横斗争的局势。不料,负大才为众嫉,加之他的进谏触动了腐败贵族的利益。于是,他们进谗言诋毁屈原,使其被降为三闾大夫。顷襄王继位后,屈原被放逐江南,被彻底地排除出了权力中心。一位伟大的天才不幸与一个王朝擦肩而过。
屈原仕途的坎坷恰恰成就了他作为诗人的辉煌。沅水舟上,汨罗江畔,多了一位面容憔悴、踽踽独行的老者,他那颗整日整夜燃烧着的心,只为伟大的理想和目标而跳动。屈原出入山林,徘徊泽畔,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尽管遭此厄运,但他“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无法排遣积郁的哀思,向兰蕙、湘水、楚天倾诉。他在行吟中更加接近黎民百姓,将一腔赤诚和哀思由胸中长啸而出,化作了光耀千古的《离骚》。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他仍心怀天下,求索不已。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思想,将神州大地渲染得高洁而明亮,在炎黄子孙的心中生生不息;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们追寻美好而崇高的人生境界。
夜幕渐渐拉开,辗转于汉北的屈原,面容更加清癯。他茕茕独立于无边的黑夜,仰望银河,璀璨的星群使天穹显得那样高远辽阔,深不可测。恰恰是无边的黑暗让他看到了巨大的宇宙,看见了无限的苍茫。他借着烛光和星光,为灵魂探路,对着浩茫的天际发问,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天问》。他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提出怀疑和诘问,充分展示了大胆的批判精神和极其渊博的学识。感谢古典的浪漫,感谢屈原带给我们这一份博大高远的襟怀。读《天问》,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的衣袂上沾染着月光与星光。
在中国历史上,汨罗江虽不及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却是一条遐迩闻名的圣河,它以万顷碧波拢成温暖的臂弯,迎接了悲愤难挨的诗人。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秦发动了攻楚战争。屈原目睹了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灾难,自知一生曾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了。于是,他怀着满腔悲愤,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沉。百姓为了纪念他,将这一天演化为端午节。
汨罗江可以收回诗人的珠玉之身,却永远无法收回他的杰出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穿越沧桑,光耀千古,更显高贵的人性之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固然也。天下典籍,浩如烟海,为何《楚辞》震烁古今?源于一颗伟大而崇高的心灵,源于可与日月争辉的巍巍人格。在艺术的殿堂里,心灵的质地与人格决定一切。“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楚辞》充满了屈原堂堂正正的炽热的愤慨和悲痛,充盈着贯穿天地的浩然之气,闪耀着日月经天的伟大而庄严的光芒。
向死而生
公元前98年,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让他真正彻悟了何为“向死而生”。因大将军李陵兵败被迫投降,汉武帝勃然大怒。大臣们趋炎附势,纷纷批判李陵。耿直的司马迁实事求是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他的降敌是伪降,有朝一日,他还将报效汉室。汉武帝听后大怒,司马迁被定性为“诬上”。依据汉朝的律例,当判以死刑。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出五十万钱赎罪;三是自请宫刑。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倘若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但是为了成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事业,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宫刑,去承受人生痛苦屈辱的极限,其生命价值确乎重于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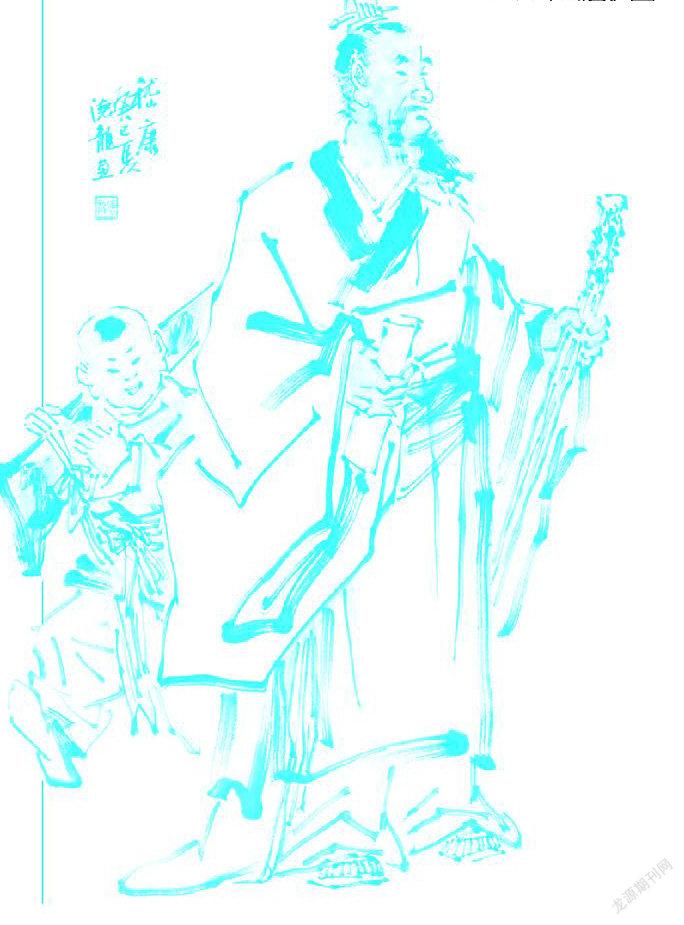
想象这样一幅场景:两千多年前那个惨无人道的夜晚,半轮冷月挂在天穹,薄雾与愁云笼罩着。那间阴暗潮湿的囚室墙角,一灯如豆。司马迁双眉紧锁,瘫坐在冰凉的地上。他的身体在流血,心在流血,宫刑所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剧痛,已将他折磨得木讷而苍老。他沉默着,沉默中饱含屈辱、忍耐和沮丧,但又酝酿着愤怒与抗争。此时无声胜有声,神思恍惚中,他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又在诵古文拜名师,又在访名迹览群书,又在着手写《史记》。想到了《史记》,他的双手骤然抓握成拳,仿佛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把他从无边的深渊里驱逐出来。过了许久,双拳缓缓松开,他将一绺披散在额前的白发轻轻地拢到脑际,紧锁的眉宇间恢复了睿智的神情,只是额头的皱纹更深了。是的,是《史记》又一次激活了他。
宫刑之后,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死了,而重铸历史的太史公新生了。司马迁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人生,看待历史人物,难免生发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慨与智慧。他自言:“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自宫’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但他咬紧牙关,承受不幸,恰恰正是这巨大的灾难激发了他惊涛拍岸的生命最强音。悲愤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他表白:“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处在最惨痛最恶劣的境遇中,司马迁不放弃精神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在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他迈出了堪称伟大的步伐。这种选择本身就彰显了人性的高贵与神圣。司马迁忍辱含垢,在书斋里呕心沥血地酝酿出了清醇的美酒。他终于完成了具有开创意义、规模宏大的历史巨著——《史记》。
伟大的受难者与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世世代代人们的敬仰。我无意颂扬苦难,但是,大大小小的苦难是每个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請别忘记司马迁这位以肉身的残缺修得精神与功德的双重圆满的永垂不朽的英雄。当不幸与苦难袭来时,请以乐观的态度果敢地迎接它。向死而生的大史公手捧《史记》启示我们:当一个人带着因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继续生活时,他的思想与创造必然会有更加深刻的特质与底蕴。
(编辑/张金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