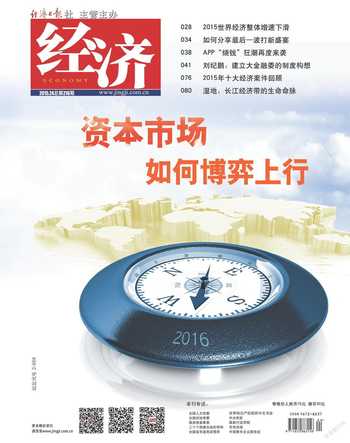戒毒社工
2015-09-10李晗
李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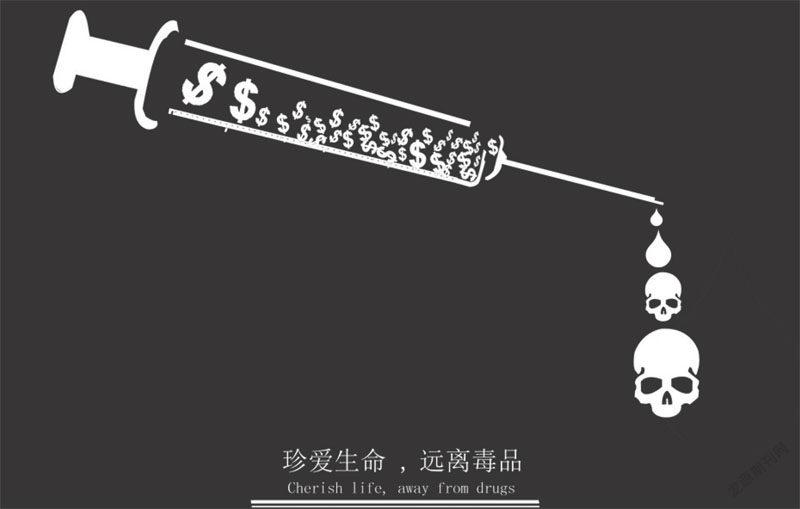
【背景】:2014年中国消耗的毒品数量达400吨,直接消耗掉的社会财富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登记在册的300万吸毒人员当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了3/4。与这些吸毒人员相对应的是,有一群人专门用尽全力与他们同行,为他们服务,对他们的就业、心理、健康等方面给予全面关怀。这类群体被称为“戒毒社工”。今天,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中,他们默默地在社区和戒毒医院中辗转奔走,用自己的坚持与付出点燃身处地狱的吸毒者,试图让吸毒者重新做人。当我走近吸毒者时,我深刻感受到了毒品带给他们的灾难、悲痛;当我走近戒毒社工时,我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无奈、着急,还有感动。
【接触群体】:戒毒社工
【接触地点】: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合作共建单位——北京高新戒毒医院
刘晓倩心里很没谱,她不知道自己明年还能不能继续做戒毒社工,“如果明年招投标失败,意味着我们将会没有启动资金来维持戒毒项目的运行。”

戒毒社工最早出现在香港、广东、上海等地。用曾开恒的话来总结戒毒社工的职责,就是“启发吸毒者的戒毒动机,鼓励并安排吸毒者去戒毒,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曾开恒是香港的一位无国界社工,有着38年的社工经验,如今被外派到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担任执行总干事一职。
记者在采访之前,心里也十分好奇,戒毒社工到底是怎样帮助吸毒者戒毒的?根据国家禁毒办的数据显示,全国已建立乡镇级社区戒毒康复领导小组2.3万个,配备专职社工2.7万人,兼职社工6.8万名。可要真实地接触到这一群体,却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戒毒社工真正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在南方等地,不是圈内人,根本接触不到。
另外,在一些自愿戒毒的医院或戒毒中心,吸食毒品的人不愿意让除了医院之外的其他人看到他们戒毒的模样,在走进自愿戒毒所之前,99%的吸毒者最关心的就是“我在这戒毒的消息会不会泄露?”这里面的戒毒社工多为兼职,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戒毒社工。
再者,“戒毒社工”这个行当还有些忙,他们或是在帮戒毒者脱毒,或是在给吸毒者家属做工作,或是忙着回答网上有戒毒需要的人的疑问。

最困难:获取戒毒者的信任
“针扎在我身上,你没有感受过,我不信你能帮助我。”
“我什么也不需要。”
“你能帮助我什么?”
刘晓倩试图先与戒毒者沟通,然后再根据戒毒者的需求和脱毒的阶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却不曾想,戒毒者给出了以上的回复。
随后,刘晓倩致电这位吸毒者,手机却传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刘晓倩觉得很无奈,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不了了之。
刘晓倩所在的机构是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该事务所成立于2013年。两年来,她们先是通过禁毒志愿者引荐的方式去接触戒毒者,遭到拒绝。后来成立成长小组,并与北京各大戒毒医院或者戒毒所合作,定期定点为戒毒者及其家属进行毒品相关知识的传达,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但效果并不好。与上海、广州等地相比,北京社会组织的戒毒社工发展相对滞后,从他们和吸毒者接触这方面就能感受到。即使接触到吸毒者,也是以外地到北京戒毒的人居多,“自愿戒毒的北京本地人不接受戒毒社工的帮助。”她进一步解释说,吸毒者并不知道戒毒社工是做什么的,也不相信戒毒社工能够帮助到他们。
因此,她们以项目的方式切入进去,试图帮助吸毒者走出阴霾。刘晓倩面露难色地说,无法全面了解每一位戒毒者的情况,偶尔的接触很难与戒毒者建立联系,“无法获得他们的信任。”
“这是最大的困难,第一步都走不了,后面均为零。”刘晓倩说。
曾开恒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北京这边的戒毒和他早些年在香港做戒毒社工的情况不一样。香港的戒毒社工是和戒毒者生活在一起,与戒毒者一起经历戒毒时的各种困难,有很深的感情,“像伙伴一样,手把手扶持着往下走。”
刘晓倩摇摇头,她认为社会组织的社工运用这种连接方式在北京暂时还不可能,她说:“顶层设计还需更完善。”
最危险:精神错乱,毒瘾发作
刘晓倩、张珊等小组成员在分工摆弄着要给戒毒者提供的音响等器械。一位眼神迷茫、缥缈迷离的戒毒者用胳膊肘碰了碰其中刚毕业的一位女社工,挑着眉说:“小姑娘,约吗?”这位女社工吓得直往后缩。戒毒者依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继续用肘碰了碰这位女社工,不死心地说:“都是出来玩的,装什么。”
这一幕被刘晓倩看见了,径直走向戒毒者,说:“这是我们的社工,请您保持尊重。”
戒毒者话锋一转,有些恼怒地说:“我要点首歌,你,快去放。”
这时,那位刚毕业的女社工已经吓坏了,待在角落不敢出声。
事后,刘晓倩分析,这位戒毒者当时精神是错乱的,应该是出现幻觉了。“他把这个地方想成了KTV或其他娱乐场所。”
当时幸好有其他人制止了戒毒者的行为,要不然戒毒社工的处境相当危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刘晓倩话语中也稍显不悦。
的确,吸毒人群中男女比例大概为7:3,而戒毒社工中以女性居多。
不仅戒毒者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时很危险,他们毒瘾发作时也同样危险。
在北京高新戒毒医院,三楼和四楼分别住着吸冰毒和海洛因的自愿戒毒者。楼层与楼层之间用铁门隔开,并配有电子出入卡,“以防戒毒者私自跑出去。”北京高新戒毒医院业务院长邓刚向记者解释说。
就在这样的层层封锁下,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制止不了戒毒者,医护人员受伤的情况。就在记者去采访的前两天,一位吸食冰毒的人毒瘾发作,用各种方法要出去,医护人员和戒毒社工百般劝说都没有效果。这位戒毒者直接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位戒毒社工,以此作为要挟,最终把戒毒社工的头发抓掉了几根。
在旁边的戒毒者家属不停地给戒毒社工道歉,戒毒社工潇洒地站起来,右手顺势捋了捋头发,笑着说:“没事,不会和他们计较。”随后,戒毒社工淡定地下了楼。
邓刚像讲平常事一样手舞足蹈地讲述着。
北京高新戒毒医院的兼职戒毒社工景女士向记者说:“这只是戒毒者毒瘾发作时众多发泄方式中的一种。”有时候戒毒者会以自残的方式逼迫医院的人放他们出去,“双眼充满红血丝,看着都难受。”
最痛心:不知吸毒者能否戒毒成功
“99.99%的人都知道吸毒不好,但摆脱不开毒品对心理的捆绑。”谈及此,曾开恒十分痛心。
他解释说,戒毒的本质就是帮助吸毒者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捆绑。生理上的比较容易,心理上的是最难的,也是不易把控的环节。
一般情况下,如果吸毒者吸食的是海洛因,将其关上一个星期,基本上痛苦都能消失。戒毒的第一天戒毒者没什么感觉,第二天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第三天和第四天最痛苦,这个阶段戒毒者对毒品的欲望增强,熬过去之后,第五天就会出现转好的迹象,第六天、第七天身体就已经基本康复。
但如果戒毒者吸食的是冰毒等对大脑神经系统有损害的毒品,不仅要先给其身体脱毒,更重要的是后续拔出戒毒者心理上的毒瘾。
说到这,曾开恒明显有些哽咽了。他记得很清楚,就是多年前他帮一位湖南吸毒者戒毒时的经历。那时候他与一帮有志戒毒的吸毒者成天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以兄弟相称,彼此之间的感情很深。
在戒毒的第三天,这位湖南籍的吸毒者要求离开,曾开恒不同意,极力劝说,“都坚持三天了,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待在这里,我们一起把毒戒掉,你可以想想未来美好的生活等着你。现在出去就前功尽弃了。”这位戒毒者抡起砖头就砸在自己的头上,眼中闪着泪花,对曾开恒说:“兄弟,对不起。”
曾开恒当时哭了。他知道这位戒毒者也不想半途而废,因为前两天他在很用心地戒毒,但可能真的是受不了了。“每一位来要求戒毒的吸毒者,我心里都很清楚,要完全戒掉非常难,基本上一次性戒掉的很少。”曾开恒说着说着,心情愈发沉重,“但戒毒之初,我还是尽量鼓励他们,说只要努力、用心,一定可以戒掉,我和你们一起。”
这位湖南籍吸毒者还是出去了,最终没有成功戒毒。
更有甚者,戒毒者不堪重负,出去后采取自杀的方式来摆脱毒品的捆绑。细数这些年帮助过的戒毒者,曾开恒算了一下,大概有20多位离开戒毒所之后,回归社会,在不同时段分别去世了。
虽然这些年戒毒成功的人也不少,但到现在曾开恒依然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戒毒者要采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摆脱毒品。”
在接触了足够多的吸毒者之后,曾开恒猜想,“可能是受不了心理的压力,他们明知吸毒是不对的,但无法摆脱,所以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失落:难寻吸毒者及其家属“痛点”
记者见到刘晓倩和张珊时,她们叹了叹气,失落的表情溢于言表。
她们刚刚结束了对吸毒者家属的心理疏导,效果明显不太好。这是她们和北京高新戒毒医院的合作项目,在医院时间、家属时间统一,并且机会合适的情况下,她们才能去讲解相关知识。
刘晓倩向记者抱怨说,这次面对的对象是吸毒者的家属,原定这次讲解的主题是“家属对缓解吸毒者压力的认识”,不料PPT刚播放到第一页,家属们就说“这个我们不需要知道。”刘晓倩在征得家属同意之后,提前讲了下期的主题“家属如何与吸毒者沟通”。
结束时,3个家庭的家属反馈分别为“觉得有收获,好。”“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不好。”“这种讲解可有可无。”
刘晓倩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家属们心里都很急躁,他们已经过了担忧的阶段,他们只希望“你给我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让我的家人顺利戒毒”。
这样的要求着实打击到了刘晓倩她们。据她们介绍,为准备此次讲课,她们写的活动策划书、做的PPT,已经改了不下十次。总体方案确定下来之后,还请了专门的指导老师来评估这次讲解内容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再多次实地调查,进行细微改动,才确定最终方案。
“失落归失落,也一定程度说明了我们的定位和帮助不够精准。”该项目负责人、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戒毒社工张珊总结说。
戒毒者在戒毒过程中一般会经历6个阶段:不考虑改变阶段(懵懂期)、考虑阶段(认知期)、准备阶段、行动阶段、保持阶段、复发阶段。戒毒社工要根据吸毒者所处的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服务,采取不同的措施。然而,现在北京这边的戒毒社工只能做综合帮助,方向上的普及。“一方面,合作一般只有一年的时间,去接触戒毒者的次数有限;另一方面,只有综合性展开,才能申请到项目资金,整个戒毒社工才能不至于落到还没开始就已消失的地步。”张珊对此十分苦恼。
据她介绍,今年的项目资金来自福彩公益基金,共批下来15万元,主要用于项目的开展。目前,平均来说,戒毒社工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一般为3000元。“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存压力很大,很多社工做了几年,就因为入不敷出而离开了社工群体。”张珊说。
最期待:做好顶层设计,系统戒毒
社工的宗旨是“助人自助”,在戒毒社工这一块,主要是要起到连接的作用。然而现在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甚至连进入社区,与已经康复的戒毒人员接触都很难。”在采访中,曾开恒多次提到社会组织在进入社区戒毒的难度。
他表示,在香港,已经有很成熟的模式,一环扣一环,每年吸毒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香港的戒毒社工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在戒毒中心的戒毒社工,他们和戒毒人员一起生活,随时了解戒毒者的动态,并及时作出处理。这种效果最好。二是在康复中心的戒毒社工,以门诊的方式帮助吸毒者戒毒。三是在社区做后期跟进工作的戒毒社工,督促已经康复并回到社会生活的戒毒者定期进行检查,以免出现复吸的情况。与此同时,戒毒社工还跟踪了解戒毒康复者融入社会的情况,必要时给予帮助。
此外,香港的戒毒社工在地位上很受人尊重,是戒毒各个环节的“万金油”,就算出现被吸毒者辱骂的情况,戒毒社工也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
当地政府提供的配套措施也足够多,可以有很多资源去帮助戒毒者。比如,如果吸毒者有戒毒的意愿,但家里生活困难,申请核实后,政府会给予资金上的资助。有的吸毒者戒毒之后,不能回家,“怕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突然回到以前的环境会出现二次复吸”,在经过戒毒社工的汇报之后,政府会提供免费的中途宿舍让其居住,以此作为戒毒者再次融入社会的缓冲,“在这里,他们是自由的,有专门的戒毒社工督促他们,帮助他们,但要遵守统一的规定。”曾开恒解释说。
当戒毒者完全康复,再次融入社会,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时,当地政府有专门的职业训练局,提供各种职业培训。曾开恒说:“这个过程是免费的,在此期间,政府会给予津贴,并介绍工作。”
但这些在内地几乎都还没做到。
在采访中,张珊也强调,“咱们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缺乏顶层设计。”
她进一步解释说,戒毒应该是个系统工程,每一部分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比如同伴教育,即已经戒毒成功的吸毒者帮助正在戒毒的人,这部分群体与戒毒者有相似的经历,能感同身受,他们主要是帮助吸毒者康复;戒毒医院主要负责吸毒者的生理戒毒;康复所主要负责吸毒者心理康复;社区戒毒人员负责吸毒者康复后的跟踪帮助。在这些都完善的情况下,戒毒社工起到的就是资源连接的作用。
“但现在这几部分各自在做各自的,谁也不相信戒毒社工,有的对这类人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因此,起到资源连接作用更是难上加难。”说到这,张珊和刘晓倩明显着急了,声音不自觉地增大了许多。
此外,社区戒毒作为戒毒工作重要的一环,也不可忽视。“吸毒人员复吸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回归社会后一定要有相应的人来帮助他们。”曾开恒多次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