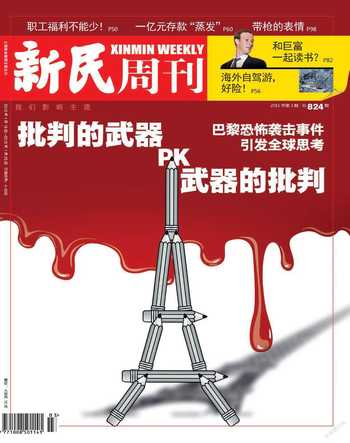历史学家的可信度
2015-09-10刘洪波
刘洪波
写历史与讲故事是不同的两个行当。讲故事的是说书艺人,写历史的是历史学家。两者间有粗疏与精致之别,更有史观、史识的差异。
即使说书,也是不无史观和史识的,忠孝节义、君臣纲常,便是史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史识。这是很坚强的东西,关公的红脸和曹操的白鼻子,如影随形。
历史学家不同,史料要多,史实要准,史识要独立,史观有自觉,史思要深邃,还有所谓史胆、史感,如此等等。历史学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门类,这样一讲,门槛就立起来了,谱也摆起来了,可信、严肃、高贵等属性也站起来了。历史既然是一门学问,也就有其逻辑结构,历史关节的叙述建立在诸多史实的相互参证之中。历史重视但讨厌孤证。孤证首先就要面临是否可靠的质疑,质疑通过,才考虑能否足以修正某个结论。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得以公开。很正常地,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直接读到日记的人还很少,但谈论民国历史、国共关系时,引证它的人很多。这当然是历史学家的功劳,历史学家去档案馆里抄录日记,见到来自当事人的先前未曾见到的记载,不免兴奋,希望凭日记去“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从一般情理而非从历史学家来要求,也不算过分;若以为一套日记就可以真实复原某个人,那就情同儿戏了。
《蒋介石日记》是真实的,这个判断有多重含义,一是日记真为蒋介石所写而非他人伪托,二是日记中的行止或心迹流露真切而非虚饰。前一点,现己确证;后一点,历史学家试图确证,但不无疑问。日记里记了每天做什么事、在里面骂人,这可以说真实;但某事是怎样做的,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骂人,就是个人角度。个人角度,即使代表真实的认识和意图,也未必符合客观事实。个人角度还有可能是自证合理。
日记为谁而写,也是一个问题。日记可能仅仅是面向自我的内心,永不公开;日记也可能是“暂不公开”但终将公开的“起居注”。即使永不公开的日记,当其不是“记过即焚”而是日积月累,也可能形成一种万一面对某位读者的“写作自觉”。如果日记记录时已有“终将公开”的预感或准备,那就更有可能埋伏解释或交代自身的“导向”。
如果更加彻底地看,文字记录心迹和行为,但从心迹、行为到文字,未必是如实的,未必是不经修饰的。任何记录,不仅无法完全还原实际行为和心理过程,而且很容易在“文字转换”中进行事实和心情的剪裁、取舍和修饰。一本日记是否真实,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并不相同。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历史固然与大人物的细行小故、临事决断、心迹意愿分不开,但历史终究不在宫帏或总统府里,而在天下苍生和时代走向之中。《蒋介石日记》中是否看得到那一时期人民的生活状况,从介绍和引用来看,没有见到。当然,这原本也不是日记必须承载的内容,甚至怎样看待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都“内举不避亲”也不必有,怎样用嫡系、门生和旁枝来区别治理也不必有,四一二、皖南事变等也可以基本不记。但如果这些都没有,日记还能还原真实的蒋介石吗?更重要的是,既然记录是选择性的,谁能保证这只体现于选择记哪些事之中,而没有体现在被记的事情记哪些、怎么記、从什么角度记、用什么方法记呢,《蒋介石日记》可以作为直接取信的史实吗?
《蒋介石日记》从日记被确认为史实,这有一段距离;从确认史实到采纳写史,这又有一段距离;从采纳写史到据此断史,这更有一段距离。《蒋介石日记》一出,历史据此重断,这需要在史实准确、史识独立、史观自觉上产生多大的跨越才能做到?
不只《蒋介石日记》,其实任何人的任何个人记录,当其进入历史学的视野时,都同样要成为史实、史识和史观的审验对象,而不是直接信录,否则历史学家的可信度就跟说书艺人相当,但演义是说书艺人本行,历史学家又是做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