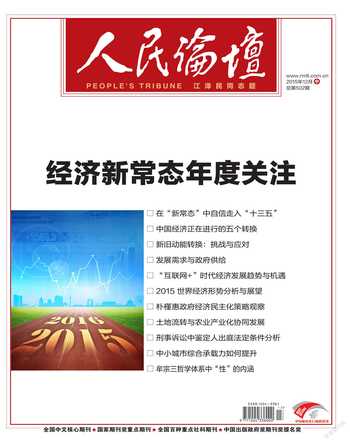美国航空自由化进程思考
2015-09-10彭金芝
彭金芝
【摘要】在世界民航史上,美国率先开启了民航市场开放和天空开放的进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航空自由化、航空市场一体化已成为民航发展的新趋势。美国航空自由化的进程是值得研究的对象,回顾美国民航迈向自由化进程的历史,总结其相关经验,对于分析中国民航业在航空自由化进程中遭遇的新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航空自由化 美国 开放航空管制
【中图分类号】F563/567 【文献标识码】A
美国航空自由化进程
在世界民航史上,美国率先进行了航空自由化的探索。回顾美国航空自由化历程,大致经历了航空规制取消、“市场开放”政策推行、“天空开放”推进三个阶段。
航空规制取消。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民航处于幼年时期,航空公司也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政府担心,在航空公司技术设施和经营管理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市场的过度竞争将导致航空资源浪费,也不利于航空安全保障。为了避免航空市场的过度竞争给新兴的航空业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国政府颁布了《民用航空法案》,用以规范和控制各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法案明确规定,航空公司的成立、进入或者退出某一航线市场、票价的制订均需得到政府的批准。同年,美国成立了航空运输管理委员会(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这一机构被授权对国际间的价格、航线、邮件的价格和航空安全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管辖,其中包括航线经营权的授予。在此后的40年中,航空运输管理委员会一直严格地使用着它的权力。
20世纪70年代,管制内航空公司和管制外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反差极大。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IATA)的资料统计,1971年美国国内航空公司的平均客座率只有48.5%,直到1977年,从没有超过5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受航空运输管理委员会管辖的美国各州内航空公司,如位于加州内的太平洋航空公司、位于达拉斯的西南航空公司,它们的票价比受管辖的航空公司平均低32%~47%,却深受旅客欢迎。这一状况的存在,也使反对航空规制的呼声日益强大。
1974年下半年,美国参议院司法分会的一个肯尼迪听证会①后,一份关于美国航空运输管理协会管理改革的特别报告出台。报告列举了航空运输管理协会在管理航空运输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排除了新航空公司进入主要航线的可能性;保护了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航空公司的利益;导致了航空运输业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和过高的服务成本;缺乏对价格竞争的注重和价格—质量水平的权衡,难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②
1978年10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航空公司取消规制法案》。该法案要求逐步排除航空运输委员会对航线进入退出、票价变动、航空公司成立等方面的管制,允许航空公司自主进入市场、自主拓展业务,允许自由兼并与重组。航空运输委员会也于1985年1月1日被撤销,这标志着美国航空政策从限制竞争转向了鼓励竞争。
“市场开放”政策的推行。《航空公司取消规制法案》的通过,宣告了美国航空自由化的开始。在国内航空运输业获得了一个更加自由的运营环境后,美国政府将更自由航空运输环境的争取进一步推向了国际市场。从1977年至1985年,美国政府与多个国家进行了激烈的双边谈判。其中1978年3月,美国政府与荷兰政府重新修订的航空运输协议为美国推行的“市场开放”政策树立了典范。双方同意淡化政府在运力、班次、砍价及市场等方面的监管角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规制体系的概念被引入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航空运输业的规则也在新双边协定的签订中发生了改变,一个更加自由的国际航空经营空间逐步打开。在新的双边协定中,市场准入开放是一个重要变化,缔约国之间的通航地点增加,并给予空运企业更广泛的第五航权,取消了对包机权利的限制;在航权方面,允许缔约国各方根据自己需要指定任意多的空运企业经营商定的航线,并增加了允许半途更换机型的权利;③在运力安排方面,取消了对航班次数和运力的限制;在运价管理方面实施“双不批准原则”,即只有在双方政府均不批准报审运价的情况下,运价协议才无效,这意味着航空票价向自由化迈出了一大步。
“天空开放”的推进。在“市场开放”协定签订和实施后的10余年里,大批新兴的航空公司倒闭或被兼并重组,在美国航空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大公司,如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等。这些大航空公司不满足于“市场开放”政策下的国际航空经营范围和自由程度,强烈要求进一步推进航空自由化。
1992年9月,美国与荷兰政府签署了第一个“天空开放”协定,标志着国际航空运输规制的进一步放松。相比较于1978年的双边协定,新的双边协定中完全放开了市场准入,缔约国双方的航空公司有权飞往对方国家的任意一点,突破了原协定中外国航空公司只允许飞往美国境内有限几个通航点的限制;在航权方面,缔约国都提供无限制的第五航权;在运价管理方面,“双不批准原则”被自由定价取代,除非是为防止出现歧视性价格等情况,政府一般不干预票价的制定。新协定中增加了航空公司可以自由签署代码共享协议或其他商业合作协议。
20世纪90年代末,在欧洲市场通过第二套一揽子措施基本实现了欧洲航空市场自由化之后,美国又先后与新加坡、文莱、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取消在航空运输业中大部分限制的协定,开拓美国与亚洲的“天空开放”市场。到2000年5月,美国与6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天空开放”协议。2003年6月,欧洲运输部长理事会授权欧盟委员会与美国进行磋商,全面开放欧美之间的航空运输。美欧双方于2007年4月30日签署了欧美“天空开放”第一阶段协议,协议于2008年3月30日生效。根据新协定,欧盟27个国家的任意一家航空公司都可以从本国境内的任意城市飞往美国的任意城市,反之亦然。协议在为双方航空公司提供新的航权的同时,为欧美双方管理当局提供了广泛的合作平台,消除了跨大西洋及更远航线在市场准入、运力、运价方面的障碍。欧美“天空开放”协议的签订,拉开了跨大西洋航空运输市场建设的序幕。
2010年3月25日,美欧初步达成了“天空开放”第二阶段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协议实现航线开放的基础上,新的协议着重关注实现欧美航空业的投资开放。新协议规定,如果美国国会批准解除外商在美国航空企业的投票权限制在25%的规定,欧盟将允许美国对欧盟航空公司拥有主要所有权;如果欧盟立法机构修订关于机场噪音的限制规定,欧盟航空公司将可以经营美国至欧盟以外的国家间航线,同时欧盟在非洲或其他地区的第三方航空公司享有主要所有权后经营美国航线的权利。欧美空运量约占全球空运总量的60%,欧美“天空开放”协定的签订是航空自由化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意味着跨大西洋统一的航空市场正在形成。
美国航空自由化的影响
《航空公司取消规制法案》的签署开启了美国航空自由化的进程。航空管制的放松意味着原来由政府垒筑的相对稳定的航空市场被自由竞争所取代。放松管制实施后,美国涌现出大量的中小型航空公司。据统计,1978年前在美国具备大型飞机(61座以上)经营定期航班资格的航空公司只有36家。而到1984年,具备这种资格的航空公司达到123家。航空公司数量的迅速增加和政府保护壁垒的突然消失,使得各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纷纷采取各种手段以降低成本。如在飞机的使用上,购买或租赁经济性能好、省油的机型;在劳动力方面,重新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使工作流程更趋合理化,实行一专多能,甚至延长劳动时间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航线设置上,以中枢辐射航线系统取代原来点对点的直线式航线网,以努力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利用促销来开拓市场,以维持和提升市场的占有份额,保有和提升航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激烈的竞争导致大量航空公司倒闭、破产或被兼并。从1985年开始,美国的航空公司数量开始下降。据统计,1978~1986年间,共有198家航空公司进入市场,到1987年时仅剩下74家。当然,放松管制对推动美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航空管制的放松,美国定期航班平均载运率由1975的54%上升到1992年的64%,定期航班旅客里程收入增加了62%;国际航班载运率由1975年的50.4%上升到1988年的72.8%,旅客人数增加88%。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广大旅客购买到了更低价格的机票。据1989年的数据统计,美国有90.5%的旅客购买到打折票,平均折扣率是66.5%。到1991年,旅客票价平均降低了15%。
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航空自由化的进程,航空管制的放松和航空自由化已是不可逆的世界潮流。在美国实施放松航空管制之后,1983年7月,欧洲运输部长理事会颁布了《区域内航空服务规章》(CEC,1983),为欧洲开放航空运输市场铺平了道路。自1987年开始,欧共体通过三套一揽子措施,逐步实现航空市场自由化和天空开放。随着欧美航空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都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的签订,加快了迈向航空运输自由化的步伐。2001年5月,美国、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5个太平洋国家共同签署了一项多边“天空开放”协定。随后萨摩亚、秘鲁、蒙古、汤加等国也加入进来。2004年1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宣布了一项旨在10个成员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区域内“天空开放”的计划。至2008年12月,其各成员国首都间的航空运输权利已全部开放。
就中国民航发展的历程来看,1980年,邓小平提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的要求正契合了世界民航运输业放松管制的潮流。几年后,1987年又开启了以“政企分开”、“机场与航空公司分设”为主题的第二轮民航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民航的这次改革其实质就是一次放松航空管制的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民航各类企事业单位从民航局中独立出来,政府从航空运输企业直接经营管理者的角色淡出,经营自主权回归企业,航空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时,自1980年9月中美两国政府正式签署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之后,2004年和2007年两国政府又重新对协定进行了修订,大幅度扩大了中美双方的航权。据中国民航局统计,2013年夏秋航季,中美两国共有16家航空公司每周经营443班客货运航班。两国的航空运输市场由2003年的70万人次、20万吨货邮增加到2012年的268万人次、57.7万吨货邮。而且,截至2013年9月,中国已签订了114个双边航空运输协定。这些都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已经走在了航空自由化的道路上。
航空自由化潮流对中国民航的挑战
航空自由化、航空运输市场的开放,为中国民航开拓更广泛的航空市场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使我们的航空企业不仅要遭遇国内同行以及行业间的市场竞争,还需面对国际同行的市场竞争。因此,航空自由化进程也会对中国民航带来更大的挑战。
防止航空垄断。美国政府无论是签署《航空公司取消规制法案》,还是推进“市场开放”、“天空开放”政策,其意图都是要为美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营造和拓展更广阔的自由竞争的航空市场。然而,在放松航空管制后,航空业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兼并风”,大的航空公司变得更强,行业集中度变得更高。就美国国内而言,美国八大航空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在1978年是80%,而至1989年已高达94%。各大航空公司在竞争中强化其市场的控制力和占有度,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对市场资源的瓜分。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航空市场竞争日益强化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航空公司通过联盟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和瓜分。这其中反响最为强烈的是1996年底世界民航运输领域的两大巨人—美利坚航和英航开始的结盟谈判。由于美利坚航和英航占据北大西洋航路市场的份额高达70%,结盟后无疑将形成独一无二的垄断局面。航空公司之间的联盟对于航空运输业的规模化发展、航空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有积极作用,然而垄断的出现却违背了营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航空市场的初衷。就中国而言,我们的民航业起步较晚,整体实力仍然有待提升。在世界航空自由化席卷而来的潮流中如何保有自己的市场份额、如何促使航空公司在结盟的同时防止垄断发生,使航空市场仍然保持良性的竞争环境、避免不公平竞争是中国民航在世界航空自由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挑战。
防止航空自由不对等。美国在航空自由化进程中虽然开出了增加通航门户城市或者给予合作伙伴反垄断豁免的诱人条件,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双边协定的某些内容仍具有不对等性特征。如在“市场开放”阶段,在航空市场准入的协定方面,美国的空运企业可以由美国境内的任意一点飞往对方国家,而对方国家的空运企业却只能飞往美国境内有限的几个通航点。对美国空运而言,实现了市场准入的完全开放,但对其他协议缔约国而言,却只是有限开放。在“天空开放”协议中,美国对本国航空公司也有多方面的保护。如美国承运商可以竞标英国或其他国家的航空邮件运输,但其他国家的承运商却不能竞标美国的航空邮件运输,其邮政总局的国际航空邮件只能由美国的运营商来承运;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可以租用外国的飞机和机组人员,但他们却可以向外国航空公司湿租自己的飞机;美国政府合同产生的货物运输需求只能由美国空运企业来承担。④可见在航空自由化的两个阶段,在美国与缔约国签订的协定中均存在着不对等性。因此,在双边协定缔结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和保有话语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双方的平等地位是中国民航遭遇的又一挑战。
应对航空资本多元化。在欧美“天空开放”协议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欧美航空业投资开放。在2010年3月25日达成的新协议中提出,如果美国国会批准欧洲投资者持有美国航空企业的多数股份,欧盟也会做出对等的安排。最新协议中的这一重要内容彰显出航空运输业市场投资的开放是航空自由化正在拓展的领域,也意味着将出现航空资本多元化的局面,而这也将是中国民航发展遭遇的又一挑战。早在2002年8月,中国民航总局就已经出台了《外商投资民航运输业规定》,而目前我国民航利用外资总额也已经超过300亿美元。随着航空运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迈进,这一数据仍将不断增长。然而,我国对外资注入民航后的管理规章尚不完善。如何完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服务于我国民航强国战略的实施,仍然是中国民航需要思考和应对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本文系中国民航大学重大预研项目“中外民航发展历程比较研究”和中国民航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实用主义与美国航空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3122014P005、ZXH2012F005)
【注释】
①此次听证会的主要目标是对美国运输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过程和控制方法进行改革。
②黄为:“美国放松管制得失谈”,《民航经济与技术》,1999年第3期。
③指定空运企业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中间点将一个航班所使用的大型机更换为小型机,并允许飞往其他国家。
④[英]里格斯·道格尼斯:《迷航:航空运输经济与营销》,邵龙译,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