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协商新常态:广泛、多层、制度化
2015-09-10向立力
向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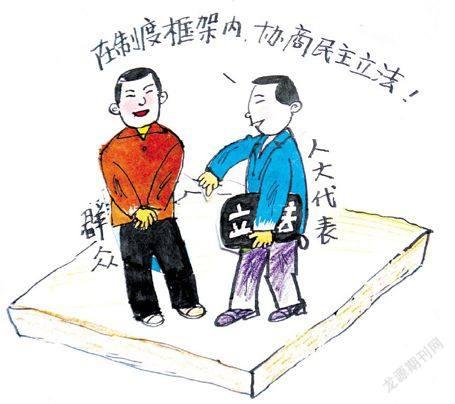
西方选举式民主的制度精髓——“多数决”,因不利于兼顾少数群体诉求而显现出功能困境。1980年,美国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提出“协商民主”概念,旨在鼓励参与、表达与倾听,进而在全社会养成理解、宽容和妥协的民主精神。他强调政府应以更加平等、公正的心态对待分歧与差异,通过对话、讨论等过程,使决策更符合实际。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并不晚于西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见证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形成和推开。改革开放后,协商式民主更加成为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重大问题,在决策中开展广泛协商、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日前,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入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即是《意见》针对立法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立法是立法机关遵循立法程序,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转化为法律文件的过程,是社会重大决策中尤其核心的部分,故而也是协商民主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协商民主与人民选举民主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确保立法决策最大程度的汇集民意、集中民智。长期以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展立法协商民主探索,有不少可供总结的经验。《意见》的印发则是一次正式的宣告,未来立法协商民主将迎来一个广泛实施、多层次运用、制度化确立的新常态。
广泛实施立法协商民主,首先意味着协商事项广泛化。经过对立法工作环节的分解,立法工作的决策过程可以细化为多环节的子决策,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律法规草案、重大制度设计等等各个环节的决策过程中,都应当引入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工作方式。广泛实施立法协商民主,还意味着协商对象广泛化。立法机关长期坚持的“开门立法”工作理念与协商民主思想不断融合,立法机关要更多地倾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公民个人等等,只要言之有理、有据,其意见均应受到审慎的对待。立法机关还应当重视发挥基层人大代表的作用,以及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让听取意见、展开协商的平台深入到与待调整的社会关系利益最密切的群体当中。
多层次运用立法协商民主,首先意味着协商主体多层次。常委会党组、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在各自权限范围内,都应当开展协商民主的尝试。人大常委会具体承担立法工作的处室乃至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当不断增强协商意识,掌握具体开展协商的本领。多层次运用立法协商民主,还意味着协商渠道多层次。立法文件解读机制、起草阶段沟通机制、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定期通报机制;立法文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专题立法调研、走访、社会调查等等,只要有利于兼听,立法机关都应当勇于尝试,渠通则水至。
立法协商民主制度化,首先意味着协商内容制度化,经过实践证明行得通、有效果的民主协商内容都应当梳理形成制度;立法协商民主制度化,还意味着协商程序制度化,将立法民主协商予以程式化。制度化的意义在于将立法协商民主纳入法治视野,使民主协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确保协商民主的结果符合民群众根本利益,而非以协商之名行滥用权力之实,就必须依靠法治的约束。只有程序合理、井然有序的民主协商才称得上名副其实。因此,立法协商要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内运行,依法协商,依法决策。
立法协商民主与我国《宪法》、《立法法》确立的人民选举制度相辅相成,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开展立法民主协商,不是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票决制的取而代之,而是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对立法工作理念和方式的全面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