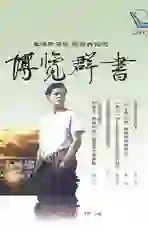“定体”与“大体”:散文的边界之争
2015-09-10赵婷婷
赵婷婷
近30年来,中国的散文写作迎来了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激活着散文的创作。一方面,散文大面积地吸收了其他文体的元素,积极地更新着自己传统的创作模式,展现出无比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过度的自由与开放似乎让散文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像“散文”。百年以来,散文形成的基本形态与核心元素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破界,于是,“散文的边界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14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刊发了古耜的《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一文,作者在该文中对新世纪以来相继现身文坛的“非虚构”“跨文体”“大散文”“新经验”,以及“民间语文”“纪实文学”等层出不穷的新散文概念或形式表现出关注,在对散文充沛博大的生命力进行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在散文一路高歌、不断拓宽领地的今天,“是否还需要拥有自己的版图和边界”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散文这一文体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拷问。
在随后的阐述中,作者径直提出了“要么强调开放性,要么倡导文体规范”的二元对立命题,并对散文边界的开放性表示了支持。他认为散文试图厘清文体与边界问题的努力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因为已有足够的文本可以证明散文具有显而易见的开放性和嫁接性。因此,“把散文看作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在性质上完全等同于小说、诗歌和戏剧,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这种主张取消散文独立的文体地位而将其看作一种文章类型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散文作家和散文创作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撰文,就这一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随后,《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系列关于散文边界之争的相关文章对此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的《“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3月31日),广东省文学院院长、散文家熊育群的《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4月21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家朱鸿的《散文的文体提纯要彻底》(5月12日),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剑晖的《散文要有边界,也要有弹性》(6月16日),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南帆的《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散文边界之我见》(7月14日),山东省作协主席、作家张炜的《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9月2日),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的《从抒情审美的小品到幽默“审丑”“审智”的大品——在建构中国散文独立范畴系统的使命面前》(9月29日)。
其中,与古耜的观点类似的是张炜。张炜对于散文的边界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界定是多余的。比起文学体裁,他更倾向于将散文写作看成是其他一切文类写作的基础,即先于小说、诗歌等写作的一种培养“文从字顺”的基本和正常的表达能力的训练。张炜甚至将广义的散文写作等同于写作与生活本身。与之观点相反的是散文家熊育群和朱鸿。熊育群认为否定了“散文”而重新回到“文章”是一种粗野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朱鸿认为,散文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涵盖太宽泛,负荷太累赘,范畴太大,作为审美性文章的散文不可不明晰边界,厘清外延,否则散文的艺术发展将会受阻。而其他论者则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肯定了散文边界存在的必要性。何平认为:“如果一种文类漫无边际地‘取消边界’,甚至‘无边界’,可能恰恰意味着这种文类的死亡。”陈剑晖认为:“无论从散文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当前的散文创作态势着眼,都有必要对散文的边界进行深入辨析。”南帆和孙绍振在梳理了中外古典文学史上并不存在“散文”文体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散文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边界”的存在决定着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内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了散文写作的不规则与散文边界的模糊与宽泛。即便是主张取消散文边界的古耜与张炜,也在表达主张之后依然承认散文创作亦有“大体”和“一定之法”。此说法来自于金人王若虚《文辩》:“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在这里,“定体”意味着标准,“大体”意味着方向。既然散文已经不属于一种文体,又何来的“大体”?这“大体”的存在恰恰就意味着散文这种文章类别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某种边界,只是这种边界比起小说、诗歌、戏剧等有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西方理论体系的文体来说,更为模糊。而一旦边界存在,散文这种独立文体的存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事实上,正如各家对散文历史进行梳理而发现的那样,首先,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代西方,其实都没有明确提出“散文”这一文体。与之相似的古代的“文章”与西方的essay与prose,更多的只是一种表述方法,而不是正宗的文体类别。诚如古耜所说的那样:“散文一直都是一种纷乱驳杂、宽泛多样的存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的出现乃至繁荣是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起的个性解放要求紧密结合的。尽管此后“散文”的创作实绩在中国文学史上不绝如缕,但相应的散文理论研究却一直处于一种落后于创作的混乱无序的状态。仅有的一些论述也只是停留在一种感性的印象式的赏鉴层面。这从散文这种文体本身层出不穷的命名便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美文”之说,胡适的“小品文”之说,王统照的“纯散文”之说等。另外诸如随笔、杂文等名称也曾一度概念混乱。总之,现代散文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理论失范的状态。
因此,自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产生之初,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概念就一直相伴而生。诚如徐迟所说: “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的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塔尖、塔顶不能无塔身、塔基。有时,塔尖已塌,身基还在。然有了塔基、塔身,就会有塔顶、塔尖。”因此,“狭义散文”更像是“好散文”的描述,而“广义散文”才是界定散文与非散文的标准所在。事实上,众多论者对散文的“边界”之争,其实也就集中在“何为狭义的散文与何为广义的散文”的问题之上。
主张“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的熊育群和主张“散文文体的提纯要彻底”的朱鸿提出的所谓散文的范畴与标准,其实就是狭义散文或者说“好散文”的范畴与标准。朱鸿认为,散文是一种非实用性的具有艺术性和审美性的自我表达,具体包括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和小品文。而熊育群的态度则更为坚决,他认为散文首先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必须要具有审美特征,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等文学性。其次,作为具有文学性的散文,艺术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它区别于迎合市场的通俗散文和非散文。他以刘锡庆对于“艺术散文”的定义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写法,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裸露心灵、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篇章。”因此,艺术散文要有第一人称的独白、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表现生命体验等要素。此外,他还以自己的散文创作追求作为“标本”,补充了一些散文的特性,如强烈的生命意识、时空意识,东方式的“悟”与最大限度逼近体验的文字等。
事实上,这些标准看似具体,实际上却还是停留在“印象式”的描述上。这些只能说是他们认为的“好散文”的特征,却不能作为区分“散文”与“非散文”的特征。但他们的描述依然概括出了散文的一些核心要素,即散文在形成、衍化过程中,人们对其本质形成的较为固定的见解。首先是艺术性和审美性,这是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首要条件。其次,是彰显自我的“自由性”与“独特性”,第三,是“真实性”。其中,对自我的彰显并不仅限于抒情,也可以有议论和叙事,但无论怎样,都是为了表达个体的独特感受与生命体验,由此衍生出散文“非实用”的要求。对于这些一直以来被恪守的要素,有些论者对其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而这些质疑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散文与其他文体比较的基础之上的。何平明确提出了“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的观点。通过对小说和散文实践的考察,他发现小说家以其写作一直在实践着“非虚构”的范例。而散文也在对小说学习从生活跨入文学“我”的创造性和想象性重构的能力。在揭示了当下散文创作过度依赖日常生活的弊端后,他指出散文对于小说的这种学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散文对于想象性的借鉴并没有取消散文的独立性,因为“散文在重构日常生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类属性”,即相比于小说,“我”是裸露的且呈现方式也可以是碎片化的。在提出散文对于“实”的想象性重构与再造的同时,他也未雨绸缪地提出告诫:必须警惕散文由于“我”的强烈“在场”的特性而导致的对生活的劫持乃至合法化,从而假文学之名对生活进行篡改、涂抹与僭越。
同样,张炜也提出了散文的“虚构”问题。不过他的提出是建立在认为雅文学小说是与散文趋同的基础之上的。他所说的虚构不是在事件(情节)人物方面的虚构,而是在“语言的虚构”上。这种“语言的虚构”,也就是作家的“语言风格”。而南帆在这个问题上则干脆抛开“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认为散文的不虚构是其不屑于虚构而非其不能虚构。因为小说的虚构是为了借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和乏味,而散文的自信来自于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
可以发现,每个人对所谓的“真实”与“虚构”的理解都是不同意义上的。何平所说的虚构指的是文学之“我”对生活进行重构的必然要求,而张炜的“虚构”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南帆则直接认为散文没必要虚构。事实上,散文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真实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作者情感的真实,心灵的真实。尽管正如何平所说,“主体的真实情感”是一切真正文学的底线,不是散文独有的底线。但散文必须遵守这个底线却是不容置疑的。散文所谓的“虚构”与“非真实”可能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或文学之“我”不可避免的虚构。同样,对于散文彰显自我的“非实用”性,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南帆和张炜都认为,“实用与否”并不能作为散文驱逐异己的标志。南帆是从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实用性”的公文都成为了散文名作的史实出发来说明的,而张炜则干脆认为:“从实际使用的目的出发形成的一些文字,往往会收获最好的散文。”因为“自然天成、朴素和真实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再审视一下坚决排斥散文的“实用性”的论者的理由,大多集中于“审美”二字,认为实用性文章艺术性不足,审美性不够,连文学都算不上更不用说是散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实用性文章都不具备审美性,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文学史上已经有许多的家书、日记、演讲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无需赘述。认为所有的实用性文章都没有审美性或审美性不足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如果非要纠结于是否“实用”的概念辨析,那么,正如张炜所说的,一向被认为散文正宗的表达自我的抒情性文章,也是“因为作者的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倾吐不行。这种抒发也是一种‘使用’”。因此,“是否实用”实际上并不能够成为判断散文是否的标志。坚持散文的非功利性,其实还是出于对散文进行“提纯”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
因此,判断散文边界的问题最终还是得落到什么是“广义散文”的问题上。“广义”也就是散文的“大体”。“大体”形成于散文百年以来创作的历史。它没有严格规定“散文是什么”,但却给人们提供了感知和把握“散文应该怎样”的依据。在这一点上,不同的散文批评家对散文文体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的看法各有不同。除了上面所提到了审美性、艺术性、真实性、主体性、自由性等观点外,还有古耜认为的“叙述自有笔调”、南帆在将散文与其他文类比较后得出的“日常的烟火气息”“对平淡生活的洞悟”,张炜认为的“自然天成、朴素和真实”,孙绍振在梳理散文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散文从“审美”(注重叙事与抒情)到“审丑”“亚审丑”(注重谐趣)再到“审智”(注重智趣)的发展过程。在散文的“大体”,也就是散文边界的弹性上,陈剑晖走得更远。他认为散文文体的边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不管如何变化,散文的审美性(诗性)、艺术创造的要求确是永恒不变的。在这样的观念下,他将除了小说、诗歌、戏剧和已经独立出来的杂文、报告文学、散文诗之外的只要具有较强审美性的作品都纳入了散文的版图。在此基础上,他也谨慎地对散文提出了处理好“自由”与“节制”、“大与小”、“思想性”与“审美性”的关系的要求。但这已属于“如何提升散文”而不是厘定散文“边界”的范畴。何平则另辟蹊径,从维护散文生态民主本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散文写作应该摒弃一直存在的先验等级观念,将散文写作还给人民大众,从而得出“散文应该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最大可能包容个人‘私想’的文类”。这就将广义散文的范围从写作主体方面进行了最大努力的拓展。
至此,尽管我们对散文的“大体”已经有了一个了解,但对于“散文的‘定体’到底是什么”似乎还是处于一片迷茫的状态。散文产生之初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理论的缺失导致了这种“迷茫”似乎注定是不可消除的。这种“厘定”的焦虑使得散文批评者们始终无法走出散文的范畴论、特征论这样一种怪圈。很显然,如果散文研究始终纠缠在“散文是什么”的观念之争上,那么对于这种文体的更深入的研究只会变得举步维艰。
在这个问题上,南帆跳出了“是与非”的概念怪圈,抓住“文类”一词,提出了“范式与枷锁”的看法。首先,他指出:“层出不穷的文体不是来自某种观念的事先设计,历史提供的文化氛围才是这些文体的助产婆。”也就是说,文体的产生并不是先验的安排,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的确,审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史,其实就是时代对散文文体特点的选择史:从五四时期散文应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产生的“叙事与抒情”特征,到抗日战争时期为迅捷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轻骑兵”的“通讯与报告”特征,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歌颂新时代而衍生出的“诗化”与“形散神不散”的畸形创作模式,乃至当今对应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层出不穷的求新求异突破陈规的新型散文!诚如刘勰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文类既可以汇聚造就,也可以被瓦解破坏。随后,他提出:“文类的权威虽然给该类文体的写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交通规则,但这种理论范式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很可能变为拘禁作家创作的恼人的枷锁。”事实上,一个时期散文的成功常常缘于一批作家对散文原有审美规范的突破和创造。一篇散文的成功常常不在于它对某种成功技法和风格的继承,而在于它发展了散文技巧或风格的某些方面。
因此,文类实际上一直处在“通”与“变”的辩证转换与发展之中。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当下各种跨文体写作成为常态的原因:范式就意味着枷锁,文体就意味着突破。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所有的所谓“文体”其实都只是“定体则无”与“大体须有”的结合。这里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难以机械厘定的意思。每一种文类,我们都难以对其“定体”作出详细而标准的界定。文类产生乃至最终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其“大体”不断细化的过程。因此,相比于产生之初就以“杂”为特色的散文,小说、诗歌与戏剧的“大体”只是相对更为具体和细致而已。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考虑的话,散文边界厘定问题似乎就失去讨论的意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散文这一文类。散文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明确地形成了自己区别于其他文类的“大体”,正如孙绍振所言:“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才华恰恰表现在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发现散文的艺术价值。”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其“大体”相较于小说、戏剧等其他文类更为模糊就野蛮地将其降格成文章。只要散文是一种文类,它的边界就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难以精确描述,这正是为何散文一直以来难以机械厘定的根本原因,却也正是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生命力所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散文的“定体”或边界到底是什么,只要坚持散文“大体”的存在就能保证散文边界的存在。而散文“大体”的存在乃至细化必须依赖于“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并行不悖以及良性互动。一方面,广义散文以其充分的开放性和嫁接性,开拓着散文的表现空间,发挥着散文文体的创生作用,给散文的发展提供广袤而丰富的土壤。但一味地提倡广义散文的开放性,势必又会助长粗陋庸俗“散文”的泛滥甚至脱离散文发展的正道。而强调审美艺术性,追求散文文体的纯粹性的艺术散文等狭义散文的存在则对散文文体的发展起着纠偏的作用,从而良化散文创作与研究的生态环境。事实上,不仅仅是散文,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可能树立起唯一的正宗的“定体”类型,所谓的正宗也只能是针对当时创作的具体情况或时代需求而言。换句话来说,一种文体的最理想的发展状态并不是某一种类型成为“定体”,而是多种“大体”的并存共生。
或许,与其孜孜执着于对散文的概念与边界的论证,散文理论家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散文创作主体的多层面的艺术实践上,并对此做出恰当而及时的评介。就像孙绍振所说的那样:“散文理论家,比之小说和诗歌理论家,面临着一种先天的不利局面,那就是没有西方文论,包括流派更迭的丰富资源。这也可能成为优于小说和诗歌理论家的条件,即没有那么多权威理论的遮蔽。”因此,我们既可以对散文的创作实践直接进行原创性的概括,独立形成范畴,并构成系统,同时也要追随散文日新月异的创作实践,突破陈腐观念的束缚,从而调整、颠覆乃至重构中国特有的散文理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