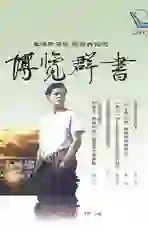以生命的诗性为散文正名
2015-09-10张金城
张金城
陈剑晖的散文研究专著《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于2014年7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散文是中国文学中的大文类,但是由于纷繁的创作状况及传统理论的认识局限,界定和言说散文显得困难重重。散文的理论建构也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与蓬勃的诗歌、小说乃至戏剧理论相比,散文理论建设可以说是贫乏萎靡,乏善可陈。以致有学者感慨说:“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孙绍振)”。《诗性想象》却迎难而上,针对散文研究的落后状况,立足学科前沿,以现代的批评立场和视野,以“诗性”为核心,试图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散文理论体系,在多个维度拓展了散文研究的空间。
理论建构恢弘,体系完整严谨是《诗性想象》的一大特色。作为“百年散文探索”丛书之一,该作以“散文话语的重建”开篇,认为重建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地基”。作者通考了五四以来百年散文发展的概况,指出当下散文创作贫弱的现状与理论话语的缺失直接相关。接着,又辨析了传统散文理论中一些习用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继而以“诗性散文”为核心,分别从“人格主体”“生命本体”“诗性智慧”“文化本体”等多个方面构筑散文的诗性内核,再从叙述、意象、结构、意境、语言等多种形式要素,对散文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深入研究。循着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画出一幅完整而严谨的散文理论架构图,梳理出一套有着严密逻辑关联的散文理论话语。可以说,作为一部系统性的散文研究专著,《诗性想象》大刀阔斧地为学术拓进扫清了障碍,是一个富于原创性和拓荒性的学术成果——这种努力有一定的冒险性,也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学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信与担当的治学态度,在当代避重就轻的学风下,很值得我们省思。
《诗性想象》既有宏观的理论建构,又有微观的概念创新。例如书中指出,要拓展与深化新世纪散文研究,途径之一就是要“化西方”和“中国化”。“化西方”是“引进西方的文论作为参照”,但又不以之为唯一标准,这是对“西方化”的一种反拨。而“中国化”则指要将“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交汇融合而创造出现代精神。旧词新意,观点独到,这两个词汇都体现了作者散文理论的独创性。又如在论述“散文的生命本体性”时,作者思接千载,从古希腊、古罗马谈到尼采,再从德国的生命哲学潮流谈到黑格尔、克罗齐、苏珊·朗格,又转而到中国的《周易》、庄子,最终将分析重点落到中国现当代散文上——从而在整个人类文学艺术史的考察中完成了关于“生命诗性”的世界性意义的论证。实际上,在《诗性想象》一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当代散文从来就不是孤立和狭隘的,而是与世界文学文化,甚至整个人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在纵横捭阖的论述中读者很容易感知论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厚的人文情怀。
学术著作最忌枯燥无味,令人无法卒读,《诗性想象》却因为书中洋溢着浓郁的学者个性,读之令人意趣盎然。当下的学术争鸣,往往只限于论文商榷,在杂志上见真章,鲜有见诸专著者。而在《诗性想象》中,作者却不讳言与诸家观点的相容或相左,直抒己见。作者在评论某一问题时,往往先举证各家观点,充分评述,再推出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自我学术建构就自然而然地带上一种阔达的气度、一种史学的厚重感。诸家观点展露无遗,平等对话,得失由读者评判,实际上是由读者参与了思想的交锋与争鸣。另外,《诗性想象》文风谦逊而不失自信,语言晓畅又饱含诗情。例如作者提出自己的散文分类标准时,也承认是“颇具难度的问题”,是一种挑战,反映出学者谦和的个性和负责任的治学精神。
陈剑晖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散文研究,是全国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多年来一直疾呼散文的崛起,为散文的正名而奔忙。《诗性想象》作为他最新的成果,既有严谨的学理思辨,又有诗性的文风,更不乏学者的意气和个性,全书在以生命的诗性来倡扬散文的未来。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该书是了解百年散文理论发展及近期学术焦点的一扇窗口,深窥则犹有濡染学人学理学风的教益。而于普通读者而言,书中多有对古今诸多散文名家文风的精彩述评,相互比对,洞见幽微,读之令人耳目一新,有独到的妙处。《诗性想象》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艰涩,有很强的可读性,说雅俗共赏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