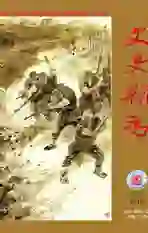关于《宋诗选注》注解中的缺失
2015-09-10孙山民
孙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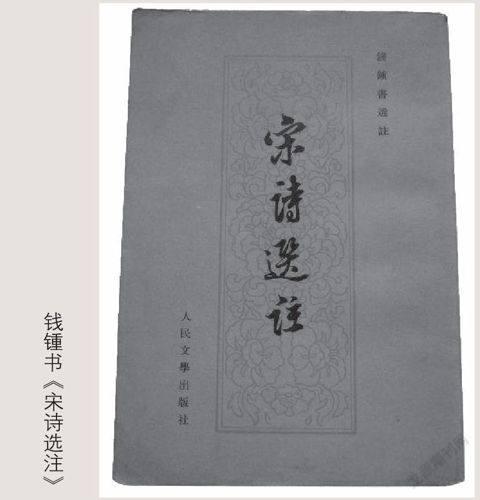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莳未匝”注解之误》。短文指出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78年重印)中“莳未匝”句的注解有误。短文有幸在《文史杂志》2003年第6期上发表,随后,得到一位读者不满意见的回应;再后,更有读者当面向我质疑:钱锺书先生是当代学术权威,其《宋诗选注》是公认的佳作,岂有“硬伤”可言?
我以为,像这样的“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况且能借以请益于方家也很好。窃以为,钱先生文才得天独厚,学问渊博,然而不是农民出身,或恐不谙农事而致训解中存在某些相关的失误。况且,就此提出意见,丝毫不构成对学界权威的贬损。下面,摘录我那篇小文开始的一段:
宋人杨万里诗《插秧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钱锺书《宋诗选注》“莳未匝”句注云:“秧还没插得匀”。在下句“照管”下注云:“小心提防。”
秧苗“插得匀”否,实与“提防”无关,就因为“莳未匝”不得其解而语意欠安……
接着,短文在后面论证其“注解之误”,并着重说明诗中之所谓“莳未匝”,是说移栽水田的秧苗还未生根分孽等等。
那篇短文所引起的质疑至今还存在,反倒让我有一丝欣慰,说明这类文章还有读者;今天再以指出,多加解释,还有意义,或许能够有益于活跃“学术”氛围。现在这里关于《宋诗选注》的又一篇文章,仍欲说明钱先生著《宋诗选注》时,因不熟悉农村某些情况而致对宋诗有关词语注解的缺失与错误。以下扼要列出,借助古今某些农村情况来加以说明。
一、对赵汝鐩《耕织叹》“耘耔”注解之误
《耕织叹》叹耕织两事,各一段,兹录前面“耕”段:
春耕农工动阡陌,耕犁纷纭牛背血。种莳已徧复耘耔,久晴渴雨车声发。往来巡视晓夕忙,香穗垂头秋登场。一年辛苦今幸熟,壮儿健妇争扫仓。官输私负索交至,勺合不留但糠秕;我腹不饱饱他人,终日茅檐愁饿死!
《选注》对这整首诗的注解共四项,以上“耕”段只占一项,即注解[二]:
“莳”见杨万里《插秧歌》注[二];“耘耔”两字出于《诗经》里《小雅》的《甫田》,“耘”是除草,“耔”是下肥。
上面说过,《选注》对杨万里《插秧歌》“莳未匝”注解有误,这里对“种莳已徧复耘耔”也就难免跟着误解。诗人赵汝鐩《耕织叹》在深深叹息农民“愁饿死”“愁冻死”那缺食少衣的境况,容易看出:耕、织两段各叙四季生活,下面单说“耕”的四季。
春耕季节农民繁忙辛苦,耕牛也遭罪,“牛背血”极言其犁耙之苦;夏季,既要收割小春作物、又要忙大春的插秧,是最为繁忙劳累的季节,正如华岳《田家诗》所说“老农锄水子收禾”那样。这个繁忙季节,在此后约八百年的当代“人民公社” 时期,就叫它作“大战红五月”!到了秋季,谷穗“勾头”(农家语),即“香穗垂头”,就忙于收割、打谷、晒场、收场,天气炎热难熬而农民却希望天天大太阳!入冬,收了粮食却不能吃饱饭,因为“官输、私负”交相索要,几乎只剩下秕(不饱米的谷粒)糠了。由此诗可见,这个宋朝“江湖派”诗人熟习的农事,连今天的村社(乡)干部也未必知晓。
钱锺书先生对本段的注解(见前引注[二]),正好又能看出对“莳”的训解失误。“种莳已徧复耘耔”的耘耔两字固然可见于《诗经·小雅·甫田》,但那“甫田”中的“耘耔”却不是这里对“莳”(水稻)的“耘耔”。
《小雅·甫田》云:“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孔疏:“言彼适于南亩,耘耔黍稷”,“耔,音兹,壅禾根也” (《毛诗正义》卷十四)。孔疏甚明,“甫田”所种是高粱之类,其“耔”为下肥壅土,当然不错;而宋诗《耕织叹》“种莳已徧复耘耔”之“耔”,《选注》谓为“下肥”就不确切了。这诗说“种莳已徧复耘耔”,就是杨万里诗所说栽插秧苗全部完成后,即“莳已匝”后的耘耔,实即“薅秧”。水稻秧苗栽插完毕(徧有遍义),而且秧根已牢、秧苗已开始分孽粗壮(莳已匝),就忙着先后薅秧了。“徧”训“遍”,且又与“周、匝”同义。《汉书·高祖纪》载“围宛城三匝”就是围了一遍又一遍。这里指秧苗(莳)滋长分孽,株围增大,就要及时薅秧,从而更利于分孽成长。上世纪中期以前,农民下水稻田薅秧须三次,“人民公社”时,农民常饿肚干活,被干部骂为“磨洋工”,薅秧就更好磨,当然谈不上耘耔,甚者致杂草竞长,谷穗稀疏,可见其“耘耔”之重要。从前的年代,农民常在水稻田“薅秧”时为缓解疲劳曼声歌唱,即为“薅秧歌”,非今之所谓“山歌”也,这里顺带提及。
再看紧接“种莳已徧复耘耔”的下句 “久晴渴雨车声发”,更见农民种水稻何其辛苦了。若田高不能导水引流灌溉,又没有设置筒车汲水的有利条件,而久晴不雨,就必须用水车汲水灌溉了。那需要两人并排协作,各以双足用力“车水”(协作如耦耕),水车之声常有夜以继日的。且说在天府之国都江堰自流灌溉地区常见水力运转的“筒车”(又名“龙角车” ),只要小河流水,就有日夜汲水的依呜声。没有自转的筒车,又急需灌溉,就只能用上述木制机械的“水车”了,水车咕噜不停,是谓“久晴渴雨车声发”也,这里指的正是人力足登汲水车。稻田保水,直至“香穗垂头”,才能减、停,以待刈割。当然,种水稻也有老天照顾之时,即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所说“南山雷动雨连宵,今年不欠秧田水”,岂有时常下雨之理?那是诗人的乐观之论,水稻田的辛苦灌溉决不可少,只想打雷下雨,肯定不行。
后面“官输私负索交至”句指秋收以后的事,这是指官私一体,即晚唐皮日休《橡媪叹》中所写,“熟稻”舂为米粒纳于官家,而“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以权谋私的事,唐宋早已有之,是谓“索交至”也。紧接下句“勺合不留但糠秕”,说稻粮终于收刮殆尽,给官家上缴了白米,留下了谷糠和“秕”。秕,我天府之国农民称作“二粱子”,不够碾米的资格,碾也碾不出米粒,即“不成粟也”(《说文》)。《左传》段注:“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即至今还有骂人所说的“恍壳”。
本文不惮辞费,意在说明诗歌所言并不夸张,上世纪的特殊年代,农民连糠秕也吃光。或问“但糠秕”的南宋农民又如何过来?答案应是“瓜菜半年粮”,至于瓜菜、糠秕也吃不上了,就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时算一时,只怕“愁饿死”的忧虑都麻木了。
《选注》对“耘耔”注解有误,对以上重要的“章句”注解有失,这里不妨补充出来。
二、对戴复古两诗的农事注解有误有失
先说戴复古《织妇叹》,《选注》注解一处失误,另两处应解而失解:
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注解)[一]赎回当掉的东西。
《选注》未深解“赎典”而误注。这两句应是说:织绢未成已计划上交官家,缫丝未完已准备取回债据。窃以为,“典”应有“典当”与“典质”二义。“典当”,如杜诗《曲江》“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此时杜甫仍有当年“裘马轻狂”(《壮游》)的洒脱气,况且“杜曲尚有桑麻田”,家境还殷实,所以此诗第三句敢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了。典衣在安史之乱前,时杜甫还相当于“官二代”。 也许杜甫真把“轻裘”之类衣物典当了,他是有物可典;而宋诗《织妇叹》中,这农家一贫如洗,还有何物可“当掉”?不能度日也得想法度,只有以画押的字据为“典”了,也就是“二月卖新丝”(李绅《悯农》),其实是悲哀的“预售”。
《织妇叹》共八句,以上是第三、四句。再说末两句:
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二]。
本句《选注》的注解[二],征引五项用“尚可”的例句来解释“自可”。如《古乐府·独漉篇》“泥浊尚可,水深杀我”、《汉书·王莽传》“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后汉书·南蛮传》“虏来尚可,尹来杀我”等等。窃以为,这些“尚可”句组的两句紧密相连,“尚可”作两相比较的关连词。例如“泥浊”与“水深”比,犹言“泥浊只算小事情,水深要命才可怕”,其它仿此。以这些“尚可”来解释“自可”,并不切合。反不如引证王安石《示德逢》诗中的“自可”:“处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借一刘龚”。“自可”一词,宋朝即有,不必远求“尚可”。尚可句这种比较判断的感叹与织妇“有布得着犹自可”的“自慰”之叹显然不同。织妇叹息:我的衣裳还勉强能穿(“织妇布衣仍布裳”),说有衣蔽体自身还过得去(“有布得着犹自可”),而父母丈夫儿女衣衫褴褛怎么办啊?吃的问题大(种稻梁),而穿的问题也不小(种桑麻),饥寒始终困扰着农民。在农村,可以说桑麻与赋税系连,与生存攸关。“但道桑麻长”“把酒话桑麻”就是人们都知道、关注的。上世纪,凭布票才能买到棉布,“烟麻”尚且一度由国家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可见还没有棉布纺织的宋朝种麻是多么重要了。然而织妇一家为能“输官”“赎典”,有时又不能不放弃种麻,当然会有“今年无麻愁杀我”之叹了。
以上有关农民生活及其所思所想,《选注》则有所不知而误解或失解。
下面再说戴复古另一首《庚子荐饥》,诗歌分两段,前段摘录如下: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
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
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拙文说这段:宋嘉熙四年,岁在庚子,史载外患接连,饥荒不断,“饥民掠人为食”,“劫数”之惨烈,岂忍目睹!赵宋王朝竟想到“赈恤”而行文,诗人悲叹“不过是文移!”这“文移”实即红头文件,即赵汝鐩《翁媪叹》中所说“朱书急急符”;当时“文移往返”(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就指“指示”“报告”“批复”“转达”之类,有司岂不知饥民外逃流窜?“文移”之词已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元年”:“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注:“文书移于属县也”,或谓文移即指文令笺表之类。皇朝统治者搞这些名堂于民何益?
《庚子荐饥》这前段,《选注》无注解。窃以为,诗人陈述农民惨苦,是此诗文献价值所在;末句,尤为重要,而“文移”应加注解,这里就不免词费了。
三、对华岳诗《田家》第三首注解之误
这首诗说农民家一天生活情况,摘录如下:
拂晓呼儿去采樵,祝[二]妻早办午炊烧;日斜枵腹归家看,尚有生柴炙未焦[三]。
(注解:)[二]请求。[三]表示儿子采来的柴不好。
两注恐皆误,先说注[二]:窃以为应作“吩咐、叮嘱”解。祝与属、注,同一声系,其义互通。《诗·鄘风·干旄》“素丝祝之”,郑笺:“祝当作属”;《国语·晋语五》“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注:“属犹注也”;《老子》四十九章“百姓当注其耳目”,朱谦之案:注犹聚也。据以上例证看,“祝妻”是叮嘱山妻(今流行称“老婆”):注意准备装肚皮的啊!“祝”从示旁,固然有祈愿义,但在这诗中倘作“请求”解,不妥。且说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自暴秦之后逐渐跌落,况且此诗中,说“良人”要下地赶农活,他当然清楚妻子在家辛苦,所谓“请求”,并不妥帖。
再说注[三]:(农汉)在天刚见亮时就叫儿子早早出门砍柴枝,又叮嘱妻子备午炊(实即午后的“晡时”之飧,近晚那第二顿饭),太阳落西,肚皮咕咕大叫,饥饿疲乏,呼吸也有气无力,收工回家一看,柴生饭难熟!虽有俗谚云:湿柴怕猛火,但必须借助干柴燃烧,而柴山上的干柴几乎找不着了,儿子采回的生柴只能慢馒在灶膛焖烧。唐诗杜荀鹤《山中寡妇》“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谁不愿有好柴呢?得过且过,临时砍点生柴来烧煮,是农民都能体验的。当然,也有持斧去找干柴(或较干)卖的专业户,如萧德藻《樵夫》“一担干柴古渡头”的;但这要远走上山去采,不是那急于赶农活的“田家”。上世纪的成都郊县农村,公共食堂下放,燃料奇缺,远郊山区烧湿柴的时候常有。不过城镇居民有蜂窝煤供应,对《田家》烧柴的领会不多。
再说那“枵腹”的况味,不同于今天所谓“肚子饿了”( 大约是肚皮底子的差异)。这只有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农民才理会得深些。
总之,《选注》的注[三]所说不恰当,不应是“表示儿子采来的柴不好”,实在是一来要抓紧时间,二来山上也只能采到“不好”的柴了。
结 语
钱锺书《宋诗选注》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学问,这是当代一般学人难以企及的。钱锺书先生出身书香名门,具有突出的学术天分与素养及作为大学者能享受到的优遇,是同时代人一般难以达到的。然而任何学问都会留下研究的馀地,也就留下了让别人学习的兴趣;也许这就是“学术问题”之能让读书人由此得到的快乐吧!
人们对学术大家的钦服是常情,而对有所“指谬”的文字难免讶怪,也是常情。不过,窃以为,不是出身农家或难免有不谙农事知识之谬,这比起出身农家而谬说农事,如说一亩产粮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来,是否更当讶怪?而后者恐怕就不是做学问难免留下一些瑕疵那么简单的问题了吧!再说拙文的“指谬”,倘有不是或不足,亦因学识浅薄所致,尚祈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