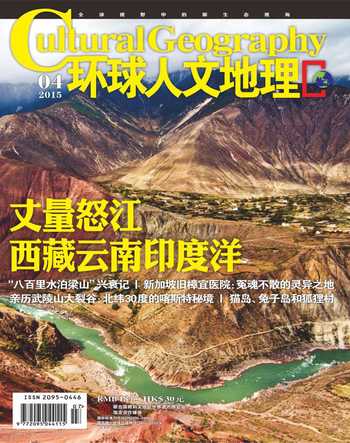穿越沙漠:宗教、旅行或探险
2015-09-10沈苇
沈苇
诗人,一级作家。生于浙江湖州,大学毕业后进疆,现为新疆文联《西部》文学杂志总编,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著有诗集、散文集、评论集15部,编著和舞台艺术作品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等。
假如一个人穿越沙漠,艰难跋涉,九死一生,没有把自己的命丢掉,这是他的幸运。当他终于回来,他的身体变了──沙从他眼中夺眶而出,他捂也捂不住,用水也无法清洗干净——沙漠长到他心里去了,包括一幕幕海市蜃楼的幻景。我想起法显、马可·波罗、斯文·赫定这些沙漠旅行家,总能听到他们体内流沙沙沙作响的声音,他们死后的骨灰可能是一捧温热的细沙。
中国高僧越沙西去
无论是地理的、生态的,还是心理的、象征的,沙漠都是一幅可怕的地狱图,令人心惊胆战,噩梦联翩。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作“死亡之海”,据说它曾在一天之内吞噬了360座城市。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语含义是“棕黄与空旷”,它高大的沙丘像群山一样连绵起伏,最高可达一百多米。硗瘠和荒凉是沙漠的主宰,最可怕的是缺水,更可怕的是它的一望无垠,对于疲惫不堪、形容枯槁的旅行者来说,它似乎永远没有一个尽头。而沙尘暴一旦形成,就呼啸着,咆哮着,遮天蔽日,其威力能把大地连根拔起,它的狂暴正是“上帝的愤怒”……
倒毙在沙漠里的人、马、骆驼变成了一堆堆狰狞的白骨,秃鹫在高空盘旋,不停地寻找动物腐尸,一只荒漠狐蹲伏着,鼻子上还留着几小时前猎物的鲜血,蜥蜴为了躲避袭击,用松散的沙子隐藏自身,一只母蝎背负一窝小蝎急窜,而狼蜘蛛面如鬼怪,8只眼睛中两只打盹,
其余6只闪着吓人的光芒……然而这一切并未吓退人们跃跃一试的决心。千百年来,进入沙漠的探险队、商队、寻宝者、劫匪、朝觐者络绎不绝,怀揣的目的也各自不同,吸引他们的也许不是湮没的文明、黄金宝藏和别的什么,而恰恰是沙漠恐惧的魅力。
两位去印度取经的伟大的中国和尚领教过沙漠的恐惧。晋代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这样描写敦煌附近的白龙堆沙漠:“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法显以后的一百六十多位中国求法僧,有一百二十多位死在了沙漠、高原或异国他乡。慧立和彦宗合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忠实记录了玄奘取经的故事,归国途中他在沙漠中九死一生:“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时如雨……水尽,渴不能进……”当佛教越过昆仑,穿越干旱,在沙漠边缘留下繁星般的洞窟,在敦煌则隆起为一个壮丽屋顶,而光芒一直到达潮湿的中国沿海和东亚、南亚。
西方旅行家越沙东来
1224年,马可·波罗经过罗布沙漠。他写道:“这片沙漠是许多罪恶的幽灵出没的场所。它们戏弄往来的旅客,使他们发生一种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些旅客白天睡过了头,或被其他事情羁绊了,滞留在后面,而骆驼大商队已转过了山脚,走得不见踪影。那时,落后的人们会突然听见有人呼唤他们的名字,并且口音又很熟悉,他们误以为自己的同伴在呼唤他。这时候如果循声而去,必将误入歧途,迷失方向,酿成坐而待毙的惨剧。”马可·波罗相信沙漠幽灵的存在,这些幽灵会在空中发出鼓乐齐鸣、管弦并奏的声音,有时又枪声大作,人喊马嘶,所以穿越沙漠的牲畜脖项上都挂着响铃,一方面便于集中走散的人畜,另一方面用来吓退那些可怕的幽灵。探险家巴格诺尔德在撒哈拉沙漠听到过一次怪诞的合唱,持续了五分钟又重归寂静,当地人说这是被流沙掩埋的寺院从地下传来的钟声。古代阿拉伯人也相信沙漠中有隐形精灵存在,它使人听到一种声音,只能觉察其嗓门,而无法发现发出声音的身体。
斯文·赫定把流动沙丘比作“没有十字架的坟墓”,每一次探险队的出征如同出殡。1895年春,他率领五人探险队,带着8峰骆驼、两条狗、3只羊、10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从喀什出发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找传说中的达克拉·马康古城,并绘制这一未知区的地图。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死亡之旅,斯文·赫定称之为“我在亚洲东奔西跑中最悲惨的时刻”。可怕的灾难发生在17天之后,探险队已滴水不剩,只能用羊血、鸡血和骆驼尿来解渴,人和动物都疲惫不堪,奄奄一息,每走一步(确切地说是爬)都变得十分艰难。断水的第五天,斯文·赫定抛弃他的探险队和一切辎重,独自去寻找生还的希望。这是一次神助,在绝望的尽头,死神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深绿──树林!和田河!水!当听到水鸟拍打翅膀的起飞声,斯文·赫定知道自己得救了。他写道:“我喝、喝、喝,不停的喝……我身上每一个毛孔和纤维组织都像海绵似地吮吸着这给我以生命的流质。我干瘪得像木头似的手指,又显
得膨胀起来。像经过烘烤的皮肤,又恢复了湿润和弹性……”
荒芜的自然,宗教的沃土
人在沙漠,因为绝望,因为死的恐惧,他更加频繁虔敬地祈祷上帝,指望上帝将自己从死神的手掌中解救出来。当他终于逃过劫难,得以生还,他由衷地赞美上帝,将奇迹归于上帝,他对上帝就越发坚信,也更加忠贞。对上帝的思慕变得如此急切,它在困厄的人身上切开无数伤口,但也开凿了一个个流水淙淙的涌泉,使他在沙漠中不至于焦渴而死──宗教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注意到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正是脱胎于沙漠背景,因为沙漠催醒并保护了人的宗教意识。沙漠对于自然来说,是一种荒芜;对于宗教来说,却是一片沃土。
恐惧感是宗教的一个内在源泉,英语中Religion(宗教)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ligio,意为人在精灵神鬼面前感到的恐惧和敬畏。沙漠同时结合了《创世纪》和《启示录》的大荒景象,它激起的恐惧是巨大的,成为宗教强劲传播的一个前提。诞生于印度丛林的佛教以其阴性特征渗透进阴柔神秘的东方,而从沙漠走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如一场飓风,一种阳性的征战,将信仰的火种撒进辽阔、广大的人群。
9世纪末的某一天,喀什噶尔喀剌汗王朝16岁的苏图克·布拉格汗在沙漠中游猎,看到一个中亚穆斯林商队到了日课时间,将自己的行装和货物散放四周而不顾,却面向西方不停地起跪礼拜。他大为惊奇,认为这一虔诚信仰和严格纪律可帮助自己铸就大业,就毅然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便在当地扎下根来,并在几个世纪后成为整个塔克拉玛干地区唯一的宗教。这是一次奇缘还是巧合?诞生于阿拉伯沙漠的伊斯兰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盆
地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诚如史学家希提所言:“对沙漠居民来说,沙漠不仅是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而且是他的神圣传统的守护者,是他的纯粹的语言和血统的保卫者……沙漠里的人民只要遇到机会就能够汲取别人的文化,这是他们的显著特征……”(《阿拉伯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