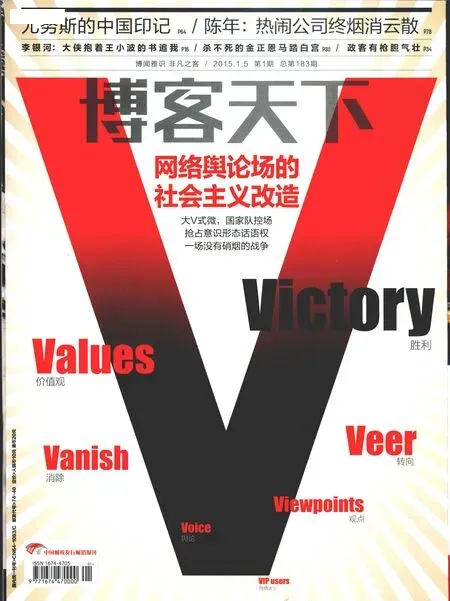尤努斯的中国印迹
2015-09-07梁君艳
本刊记者 / 梁君艳
尤努斯的中国印迹
本刊记者 / 梁君艳
30年前,尤努斯通过向穷人发放贷款,逐步建立起格莱珉借贷模式。他挑战充满阶层歧视的银行系统,也挑战反对民间借贷的伊斯兰社会。这位“穷人的银行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多次访问中国,叩开了中国小额信贷之门。他像一位超级明星被中国信徒热情环绕,而他没有贫困的理想、社会企业理念,依然走在寂寥的路上。

2014年12月17日下午5时,江苏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200名妇女聚集在村口,打着腰鼓,舞着折扇,一遍遍高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在声声交织的热闹中,尤努斯快步从大巴车上走下,迅速摘掉灰色帽子,低头弯腰,接过陆口村妇女送上的绿色花环。在人群环绕中,他露出习惯性的慈祥笑容,微微前倾身子,与送花环者握手交谈。
这是74岁的尤努斯第一次踏足真正意义的中国农村。
这位孟加拉经济学家对中国并不陌生。20多年来,他先后到访北京、上海、广州、海口等地参加论坛,但从未真正有机会走进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然而,作为一名致力于乡村金融的“穷人的银行家”,考察中国农村现状及贫困起因,给予针对性的意见,才是尤努斯心之所念。在去往陆口村的高铁上,他一直在问随行翻译、“格莱珉中国计划”常务经理肖欢琦有关中国的事情,包括留守儿童、年轻人就业等。
寒冬中的陆口村妇女,用她们所能设计出来的最高规格的农村礼仪喜迎尤努斯,兴奋地呼喊着这个过去两年来萦绕于耳的名字。无疑,这是陆口村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外事活动。
对尤努斯来说,亲访这个内陆乡村颇有象征意义。
30多年前,出于对贫穷的愤怒与对传统银行“贷富不贷贫”的不满,尤努斯创立了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在孟加拉语中意指“村庄”),即通过小额借贷的方式扶助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鼓励她们社会交往和创业致富。因其“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2006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获奖后的尤努斯,旋即应中国政府之邀访问中国。2006年10月,他不仅获得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见,还与吴晓灵、易纲等财经高官深入探讨。通过小额贷款激活农村金融需求,推动农村扶贫和经济发展,在当时成为政策共识。
借助这股小额信贷春风,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推出文件,对长期垄断的金融体系进行有限松绑,以小额贷款名义成立的金融机构遍地开花。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
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尤努斯获奖引发的蝴蝶效应。
然而,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集中在城镇,服务对象往往是中小企业。其运作通常是基于担保、抵押等传统银行业务模式,而非尤努斯所设计的“格莱珉模式”。
尤努斯深知,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依然没有被满足。也因此,对陆口村—纯正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唯一试点,他期望甚殷。这一项目成功与否,意味着格莱珉所代表的消除贫困模式在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90年的60%下降到2010年的12%。但根据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依旧很大。消除贫困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也将给世界树立一个很好的样板。”有着浓厚中国情结的尤努斯告诉《博客天下》。
“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
瘦骨嶙峋的人们涌遍孟加拉首都达卡全城,老人看起来像孩子,儿童又看起来像老人。他们没有念叨任何口号,只是静静地躺在地上等死。
1974年,尤努斯回到独立仅3年的祖国孟加拉,这幅赤贫世界里的饥荒景象,就以如此震撼的方式铺陈在他面前。彼时,尤努斯怀着建设战后祖国的美好愿望,辞掉了美国的大学教职,出任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
身为孟加拉富商之子,尤努斯却对经商致富了无兴趣。他的志业是教书育人。这位学霸从小就喜欢以教师姿态教导自己的弟弟妹妹,只许他们拿最高分。
但近在咫尺的饥荒惨状,令尤努斯惧怕授课了。以前,他在课堂上教授高雅的经济学理论,快意十足,而在1974年,他开始自我怀疑。“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他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如是反思。

尤努斯开始从课本中逃离,立志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学,“我想教给我的学生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
这位生活优渥的精英分子并未想到,此后自己会长久驻留在穷人世界,兢兢业业地做着扶贫斗士。当象牙塔里的学究们还在死守理论教课时,教授尤努斯重新做起了“学生”,以吉大港大学附近乔布拉村的穷人为“老师”,深入调研贫穷的起因与出路,但收效甚微。
1976年,一天只挣2美分的21岁农妇苏菲亚·贝格姆,帮助他明白了问题的本质。
有着3个孩子的苏菲亚以编织竹凳为生。无钱购买22美分原材料的她,属于银行判定的“金融不可接触者”,只能以仅高于成本2美分的价格,将竹凳卖给借高利贷给她的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令尤努斯震惊的是,类似苏菲亚的妇女,在孟加拉农村比比皆是。一周之内,他便拿到了一个42人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足27美元。
“我的天啊,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只是因为没有27美元!”尤努斯在《穷人的银行家》一书中写道。他既愧疚又坐立难安。这一年,经历了与孟加拉国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艰难交涉后,尤努斯开创了一套面向穷人贷款的银行体系,1983年正式冠名为“格莱珉”。
尤努斯秉持的信条是,为穷人服务,就是为国家服务。尽管一直面临争议,但他从不与反对者正面交锋,只是坚定前行。尤努斯理念的中国践行者高战,回忆起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的早期推广时,仍不免感叹尤努斯之不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孟加拉妇女仍处于“遮蔽”习俗的时代,女子不得随意与陌生男子说话和活动。早期,尤努斯向乡村妇女推介信贷时,不得不请女学生做助手陪同前往村庄游说,而他本人必须站在几个家庭的公共过道里与妇女们说话,甚至要通过聊孩子的方式慢慢打开妇女们紧闭的内心。
尤努斯团队游说贷款的行为,也很快遭到男人们和宗教人士的反对与阻拦。宗教头脑威胁说,妇女若从格莱珉接受贷款,就是擅入禁止女人进入的邪恶领域。在他们眼里,现金的控制权只由男人掌控。他们警告妇女:加入格莱珉将受惩罚,死后不得以伊斯兰葬礼安葬。不少接触借贷信息的妇女甚至因此被家人殴打。
但作为一名反传统的斗士,尤努斯认定,妇女具有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是整个家庭最称职的经理,能把家庭理财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些最绝望的、没有食物的、被丈夫遗弃的、只能靠乞讨来养活孩子的妇女,通常是最坚决的,不管谁威胁她们都要加入格莱珉银行。她们别无选择。”尤努斯坚信这是一个等着被拯救的世界,通过改变妇女的观念,激发她们的尊严,妇女完全可以改变世界。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他反复强调。
从孟加拉到中国
对尤努斯来说,格莱珉银行不是深思熟虑后的计划,相反是一时冲动的产物,是“对挫折感和极度震惊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模式获得了空前成功。贷款者纷至沓来,格莱珉模式也被多个国家复制和推广。
有个试点项目的故事令他至今不忘。这个项目向乞丐提供5美元的贷款,帮助他们烘制饼干等商品供应市场。按照尤努斯的设想,能有1000名乞丐贷款就心满意足,惊人的是,最后参加者却超过了10万名。“两年时间里,便有超过2.5万名乞丐彻底停止乞讨,成为出色的上门推销员。”2013年6月,在纽约举行的福布斯慈善峰会上,获得福布斯终身成就奖的尤努斯回忆起此事时,一脸笑容。
如今在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已成为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共有850万个贷款客户,其中97%受益者为妇女;贷款余额为15亿美元,存款余额达到17亿美元,贷款回收率则超过了99%。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广东人陈泳斌,曾作为格莱珉银行志愿者,在孟加拉农村待了一个多月。他发现,当地许多妇女尽管从事与父辈相同的编织、缝纫等工作,但已经盖起了砖房用上了电。
尤努斯认为,格莱珉模式之所以在全球有如此高的知名度,2006年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功不可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荣誉,”尤努斯以一种玩笑似的口吻说,“获奖之前,没人关心我,他们通常会说,‘这家伙是谁?他疯了!’获奖之后,人们开始倾听我的想法,之前一直紧闭的大门也向我打开。”
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帮尤努斯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尤努斯与中国的接触始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杜晓山是格莱珉模式最早一批学习者和介绍者。他回忆,那年他与同事以河北易县为试点创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并得到尤努斯支持,获得了格莱珉银行5万美元的贷款。然而,囿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他的实践并未引发太多社会影响。
在杜晓山等人眼里,格莱珉模式无疑是非常独特的。尤努斯为格莱珉银行制定了严格的贷款界限,规定只能贷款给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甚至赤贫人口,尤以妇女群体为主。
尤努斯也设计出一套特殊的贷款机制。借贷者无需任何担保,但个体借贷者需自发寻找和建立5人村民小组,小组成员通过格莱珉银行的考察、培训、口试后,借贷者才能拿到贷款。贷款采取整取零还的方式,每周还一次,借贷者同时也是银行的存款者,存款一律不分红。
格莱珉银行正是通过这样看似简单的借贷方式,把乡村妇女融进社会价值网络中。妇女不再是被银行拒绝和歧视的对象,她们变身为银行股东,一些人甚至成为企业家,创富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而小组贷款形式的设立,为妇女提供交流和分享机会,并增添相互督促的力量。
受“格莱珉模式”启发,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现任国务院参事汤敏参与的龙水头扶贫基金会也于1990年代在山西临县诞生,专门向穷人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与杜晓山的“扶贫社”相似,龙水头扶贫基金会长期得不到合法身份,只是借助茅于轼、吴晓灵等人的社会影响力,才未被取缔。汤敏回忆,1998年至1999年,中国公益小额信贷非常活跃,高峰时一度达到300多家,如今只剩下10多家。
在汤敏看来,格莱珉模式难在中国落地,根源在于缺乏政策支持,有些地方甚至受到政府限制。又因不能吸储、不能赚钱,其业务运转缺乏后续资金;此外,中国不像美国,格莱珉银行缺乏大企业家捐助者。
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引发了热潮。在“发展至上”的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引进格莱珉模式,推动农村地区发展。2008年,海南省政府举办了小额信贷国际峰会,尤努斯受邀作了主旨发言,并被聘为海南省政府顾问。当时的政策宣示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农村小额信贷实验区,但在中国权力架构下,金融政策决策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缺乏能力来推进金融创新。格莱珉银行和海南省政府签订的合作框架,大多数停留在纸面上。
此时的尤努斯尚不知道,在陆口村出生长大的高战,2010年无意中接触《穷人的银行家》之后,连夜读完了这本著作,深感自己的所有理想都在书中得到实现。如同深夜迷航的船只找到了灯塔,高战不可自抑地自学起格莱珉模式。
“为他人谋乐是一种超级的幸福”
在众多尤努斯理念的信徒中,高战的经历比较特殊。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他对中国乡村的凋敝有着强烈的内疚,也一直怀有参与乡村建设的理想和激情。在茅于轼感召下,2003年,高战在家乡陆口村成立了村民互助基金会,旨在将有闲钱和需要贷款的村民联合在一起,实行资金互助。

2014年12月17日,格莱珉银行与京东达成合作备忘,拟共建农村金融新模式。
但对高战而言,这与其说是资金互助会,不如说是促进社会参与和培育乡村公共精神的试验。贷款的道德自律条款,如无赌博、小偷等行为,不从事污染环境的行业等,虽只列为考察性项目,却难免令村民们萌生怯意,加之信贷员腐败、资金流向大户等危机,高战再造乡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他极其苦闷。
有此试验在前,2010年,当看到方法和理念如出一辙,但更为系统和专业的格莱珉模式后,高战顿时将尤努斯引为知己和偶像。“不要把它理解成银行,货币只是它的一个媒介。这是相互发展的一个社会途径和家庭微型结构。”12月17日,在去往陆口村的高铁上,高战告诉《博客天下》。
高战始终认为自己与尤努斯有缘。2012年,他亲赴孟加拉邀请尤努斯到中国演讲,格莱珉银行的工作人员起初对他希望会见尤努斯的请求未置可否,当高战的表现引起他们的注意之后,也只答应安排15分钟。但两人相谈甚欢,一谈就是2小时。
高战回忆,当他带着连夜赶做的PPT如约而至尤努斯办公室时,尤努斯一反常态地要求先看他仿照格莱珉手册制作的小册子。册子上列有格莱珉银行“四项基本原则”和“16条公约”,还有还款信息列表。册子封面的图案仿照格莱珉银行的LOGO,又增添了一棵大树,五瓣绿色树叶被设计成手拉手的造型。
“My God!”高战在电话中模仿尤努斯看到小册子时的惊叹声,“他觉得我理解了格莱珉银行的5人小组是核心。”
高战的理想主义气质,让尤努斯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由此成为尤努斯最认可的门徒。那次会面,尤努斯痛快答应前往中国演讲,又当即表示支持高战在中国推行格莱珉模式。当年8月,“格莱珉中国中心”揭牌,高战被任命为执行长。2014年7月初,孟加拉信贷专家萨克尔进驻陆口村,手把手带领中国团队践行尤努斯精神。
尤努斯曾经提醒高战:“如果没有长期待在基层的意愿,以及对底层人的尊重关怀,光靠这套模式是做不好的。”而在学习过程中,高战与他的团队也发现,格莱珉模式看似简单,实则奥秘暗藏。
格莱珉模式有16条公约,包括利用空地种蔬菜、送孩子上学、饮干净的水等等,被高战视为格莱珉银行的“灵魂”。“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太厉害了,一旦定下就成了绩效考核的唯一指标。所有员工不断地谈这些指标,还款率反而放在最不重要的地方。”高战告诉《博客天下》。
令高战钦佩的还有格莱珉专家与底层民众打交道的技巧,如穿着简朴;要表扬家里的亮点、孩子以及家庭的整洁;入座时不能坐得比主人高;每周开会和还款时,双方要相互起立敬礼。高战认为,正是这些看似和信贷无关、简单又可执行的信条,有力地帮助妇女恢复信心,促进公共生活。“格莱珉模式,是理想主义和商业设计结合的复杂体。”他如是评价。
在他看来,招募符合要求的从业人员并做好培训,是实践格莱珉模式的关键。但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实施,除了人才瓶颈,高战还不得不直面政府监管、资金投入等难题。“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一定要让政府觉得,这是他的政绩,不是在挑战他的权威。”汤敏提醒高战说。在中国,民间金融仍处于灰色地带。
因为国情与文化差异,高战也曾担忧格莱珉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或者不可持续。但每次话才出口,便被尤努斯打断。“一个母亲爱家庭爱孩子,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只要你坚信这一点,格莱珉模式就可以推行。”尤努斯淡淡解释。
格莱珉中国国际联络员苏玛称尤努斯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他眼里,尤努斯对底层穷人始终怀有强烈的责任感。高战则认为,这个睿智清醒的老人一直在不断创新和超越。于尤努斯而言,小额信贷只是一部分,它不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公共卫生、年轻人的就业等,需要创办多元化的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来推动。
“60%的人口只拥有全世界总收入的6%,他们的贫穷是制度失灵所致。”尤努斯说。在他看来,社会企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或公益慈善组织,它首先是一家企业,需要通过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不过,社会企业并非以赚钱为目的,企业对社会应有关爱和互助之责。
当有人把尤努斯和伟大慈善家相提并论的时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二者的区别。他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位银行家、一位企业家。慈善家做的是慈善,是一种给予;而他做的是一种发现,是发现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最底层的个体,其实都可以有信用,都有创造财富的意愿。
根据尤努斯的解释,小额信贷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发展,是人通过行使某些权利,逐渐激活信心和信念,刺激积极人格成长的过程。对于那些被剥夺的和被压迫的社会底层来说,这种积极人格的成长,才是改善生活的最大动力。
作为经济学家教授,尤努斯认同市场经济,但认为利润不是全部。他说,人性除了自私自利的一面,还有无私利他的一面。认同自利的人,可以通过参与商业企业,通过市场过程创造更多财富;认同利他理念的人,则可以通过社会企业机制来帮助更多的人,从而获得快乐。
“赚钱是幸福的,为他人谋乐是一种超级的幸福。”尤努斯反复重申这一观点。
在他看来,商业企业的分配规则往往是,处于上层社会结构的人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则获得很少。社会企业是对这种机制的必要矫正。社会企业把资源从上层转移到社会下层,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只有同时承认人的这两种天性,并设计与此对应的社会机制,才能让社会,尤其是社会上的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才能走出畸形的资本主导的社会。
青年、技术与互联网
在陈泳斌和肖欢琦眼里,尤努斯与大多数领袖人物一样,特别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总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4年前,尤努斯在孟加拉国设立了一个“社会企业创新实验室”项目。每个月,尤努斯会定期主持实验室会议,与年轻人共同探讨创业的想法与困惑。这些参会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底层。此次中国之行,尤努斯专程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演讲,肖欢琦认为,尤努斯可能是觉得改变现状比较困难,而要让想法变成现实,鼓励年轻人多多参与是一种途径。
尤努斯信奉技术可以改变生活。他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开通了个人账号,重要微博还配上中文翻译,大多时候在谈论梦想、企业家精神、人性、危机与机遇、消除贫穷、社会企业等。这是他理念的传播渠道之一。这位加V的经济学家,粉丝数已有80余万,不过,他显然还未引发中国民众的热情拥抱,他的帖子鲜有回应和互动。就在最近,他又注册了微信。
12月17日,尤努斯和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在北京共进了一顿早餐。他们谈论起各地的大事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技术。
互联网技术正在逐步渗透进格莱珉中国区,一种新的农村金融模式正在中国酝酿,它的推动力量并非源自中国的金融系统,而是尤努斯和刘强东。当天,格莱珉银行与京东达成合作备忘。日后,中国农村推行格莱珉小微金融模式时,将可借助京东的电商渠道和供应链资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被京东划为第一批目标区域。
在农村生活了18年的刘强东用“疯狂”来形容农村高利贷现状。“这剥夺了很多劳动人们的成果。”他说,希望这一合作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改变力量。两者的合作意味着,格莱珉模式在中国从此插上了互联网技术的翅膀,双方在线上的银行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众筹、大数据风控等方面,将与线下的格莱珉小微金融模式形成互补。
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京东格莱珉合作产生的新模式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在许小年看来,小微借贷难,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利用京东的网上大数据,可从大量信息中分析贷款申请人的信用状况,会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京东嫁接或借鉴格莱珉银行的小微贷款模式,可构建社会基层微型结构,使得贷款的跟踪和回收成本降低。
实践20余年,汤敏也发现,中国的小额贷款完全走传统商业化模式行不通,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小贷公司又因成本过高而举步维艰。在他看来,格莱珉模式引入互联网,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不过在尤努斯眼里,年轻人、技术与互联网其实都代表着创新力,代表机会和未来。
随着小额信贷和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火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尤努斯,钦佩尤努斯。此次中国行,尤努斯犹如明星,不停地被粉丝们拉着合影留念,不少小额信贷公司的老总甚至前往陆口村,希望从尤努斯这里取得真经。
尤努斯反复倡导的社会企业理念,却没有引发同等程度的热情。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追寻商业利润、快速寻求回报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心态,但他并未感到沮丧。他说,只要时间允许,只要有召唤,他就愿意飞来中国,不厌其烦地和中国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媒体和利益相关者讲述他的信念。
“陆口村之行是一次美妙的体验,很多重要的变化迹象已经发生。社会企业的理念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接受并实践。”说这话时,尤努斯一脸自信。■
(本刊记者何楯之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