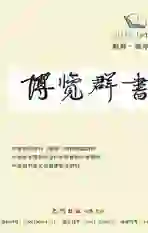分裂、焦虑与迷失
2015-09-06彭凯
彭凯
摘 要:面对新时期多种话语共生的震荡及龃龉,如何透过文本叙述的裂隙,重新把脉作家的创作心像,对重返当时的语义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张贤亮的小说,特别是80年代前期的作品,在其叙述策略中或隐或现地透显出对“身份”寻找与确认时的动摇和焦虑,以及“重述”面纱下的“身份”的变形、伸缩和扭曲。
关键词:张贤亮;症候;叙述转移;控诉
一、分裂、焦虑与迷失—张贤亮小说中身份认同的症候式分析
“四人帮”倒台之后,面对历史又一轮分化重组,如何在动荡的语境里把握时代精神的偏倚,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讲述”中重新确立个体的身份认同,成为作家们不可避及的话题,当然也渗透着某种被动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对张贤亮小说症候式分析,管窥当时复杂话语博弈下的“身份认同”的叙述迷宫,是本文致力解决的问题。
二、投怀大众:身不由己的迎合
张贤亮小说中主人公,如许灵均(《灵与肉》)、石在(《土牢情话》)、章永璘(《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右派”知识分子,被遣往偏远的劳改农场接受改造。劳改目的就是脱胎换骨,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认同。张贤亮在《灵与肉》的题记中写道:“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这个“儿子”原本想要在革命的镜像里体认自己的身份,但“臭老九”的声音打破了他的幻想和自我陶醉,他见到自信和尊严被掏空的躯壳,幻想的自我意识烟消云散,在拉康所说的“父亲”统治的符号世界里犯了失语症。
无边的旷野,重新找寻的过程,处处承受着精神的抵牾和情感的嬗变。迫切认同的焦虑以及背后自相矛盾的分裂,从1980年发表的《灵与肉》为始,如投石之纹,不断漾开。道德评价机制先验性地介入,使得这两种生活看似是二元对立(灵与肉)的平等博弈,实则仅仅是认同主题下关于“报恩”戏码的一次变相演绎;看似是灵魂激烈斗争的虔诚皈依,实则不过是对矛盾所激生的焦虑的逃避,章永璘“通过留下来的行为,他缓和了焦虑,在现有的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之初)中取得了合法性”。[1]毕竟,“人民”在整个现代中国具有神圣的语义背景和崇高的道义色彩,“新时期”依然难以摆脱“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样的话语制约。黄土地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回归则是“爱国者”精神世界梦幻般的升华。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许灵均“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并且从财务科领回五百块钱补助回家的描写:
“喂,秀芝,……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是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显而易见,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撮合已潜藏了关于生活方式、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危机四伏的矛盾,并且呼之欲出。但这些分歧在作者的笔下被悄无声息地引向了道德的宽阔地带,“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三、想象失陷:叙述受挫与转移
张贤亮将置身西北黄土地上饱受摧残的“右派”知识分子,被广大劳苦大众温暖人性所抚慰、滋润、感化的“落难/拯救”的故事模式移植到了《绿化树》,试图延续和修缮关于知识分子灵魂涅槃以及民间认同的叙事神话。
甫一开始,罗列稗子面馍馍、稠粥与稀粥、萝卜等一系列食物群像的方程式,展现出一种面对贫瘠匮乏时所必须习得的强韧的生存哲学。而且,还不忘“添油加醋”地把章永璘如何巧妙地利用几何体的视觉差多得到监狱里的稀粥、如何在土豆换萝卜的复杂逻辑运算中以欺骗老乡、如何发挥生活的经验打一口柴省火旺的炉灶、如何用烧红的铁锹煎稗子面糊的情形巨细无遗地描绘出来。显然,“吃”在融入人民的漫旅中是不得不攻克的关卡,也是不得不遵守的既定法则。
当然,张贤亮还在进行着企图修补裂痕的努力。小说中,《资本论》玄奥的逻辑思辨、晦涩抽象的文本以及跳跃华丽的语词;古今中外情思并重、不失风雅古典诗歌;直白朴素、高低婉转、苍凉忧伤的“河湟花儿”小调,在看似自由共生的话语平面中来回穿插,缠绕交合,多种力量客体像游魂一般在表述的边际不断巡狩。作者竭力平衡和弥合随之而来的力量对峙,以“吃”与“人性”为砖瓦,来搭建知识分子通往人民的桥梁,而且还不忘在破棉絮中塞上一本《资本论》,让知识分子在黑夜的海上不至于迷航。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不经意窥视到正在芦苇丛里洗澡的黄香久,结下了宿命一般的缘分。多年以后,二人几经波折终于相逢;困顿日子里,干柴与烈火迅速结合。不料章在情欲的压抑中落下了生理的病根,尽管不久痊愈,但多方面复杂的矛盾还是使得二人分道扬镳。表面看来,这是一次滑向低俗的边锋探险,实际上是作者一次极为机智的偷天换日,因为“性不仅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生理行为,性同时是革命,是政治,甚至寓托了民族或者国家的命运”[2]。
由此,重新回过头来看这篇小说,张贤亮之所以将一切纠葛与矛盾通通简化为肉体的修辞学,将性功能的缺失等同于政治觉悟的阉割,是因为如果仍然执着于人民认同与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焦虑的魔障里,那么在通往政治神坛的道路上便会不断受到阻隔,也必将把知识分子精神的匮乏、反思的无力、依附的软弱暴露无遗。推及到前面的作品,人民的意义也似乎被架空,她失去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成了知识分子验证自我政治觉悟高低的语义场:章永璘在抢险后恢复了性功能只有在黄香久的温床上才得以证明;马缨花对章永璘的拒绝毋宁说是他政治改造得还不够彻底才遭嫌弃;许灵均回到黄土高坡也就是对罪孽的持续洗清,一次光明正大的政治献祭。
四、话语博弈:“控诉”还是“忏悔”
“右派”作家曾经被流放,现在宣告归来,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经历无疑可视作其英雄载誉而归的勋章。对于那段苦难的讲述不仅能够修复甚至重构历史,而且也是论证自我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作为幸存者的“证言”,张贤亮的作品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声音的鼓荡:“控诉”和“忏悔”。被放逐的经历以及竭力摆脱“失信”的焦虑,使得“无罪的声张”与“有罪的悔悟”悖谬地萦绕在历史文本统一的表述中。endprint
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等帽子并不被知识分子所承认,他们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是历史被迷蒙了双眼,一时糊涂冤枉了好人。因此,他们对亲历的体验、记忆的提取,也就还原了那段黑暗的野蛮的“历史面貌”;苦难也就成为历史篡位中对个体无辜地戕害。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已经将严酷的劳动改造视为返祖的满足和愉悦:“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便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对他们来说,革命和政治依旧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而苦难就是在严重的政治受挫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认同的证据。
洪子诚先生在谈及加缪《鼠疫》时,将80年代初的文学与其作了对比,鞭辟入里地指出关于作家(叙述者)在自我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鼠疫》叙述者清醒的限度意识。虽然叙述者认为是在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但也不打算让这种‘代表性的能力、权威无限膨胀。”[3]正是基于对“幸存者”这一身份、姿态持警惕的立场,使得《鼠疫》没有沉浸于收集“不幸”的“自怜”与“自恋”以及毫不犹豫地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而是在一段黑暗历史结束的瞬间看到另一种荒诞的延续。张贤亮的作品少了这种警醒的意识,为自我“正名”,为历史“代言”的欲念颇为急切地想要为前一个时代划上句号,为下一个黎明拉开帷幕;甚至在某些时刻把强烈的幸存欲望幻化成了“危险”的“感激之情”,根本顾不上清扫历史积垢。或许,“归来”本身就带有身份意识的狂热,使得这一次历史的书写,以“铭记”为初衷,却给“忘却”做了嫁衣。
注释:
[1]房伟:《荒野中的迷失——从张贤亮小说谈新时期文学救赎意识之批判》,见《风景的诱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2]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3]洪子诚:《“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见《重返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房伟.荒野中的迷失——从张贤亮小说谈新时期文学救赎意识之批判.风景的诱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5.
[2]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5.
[3]福柯.性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5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