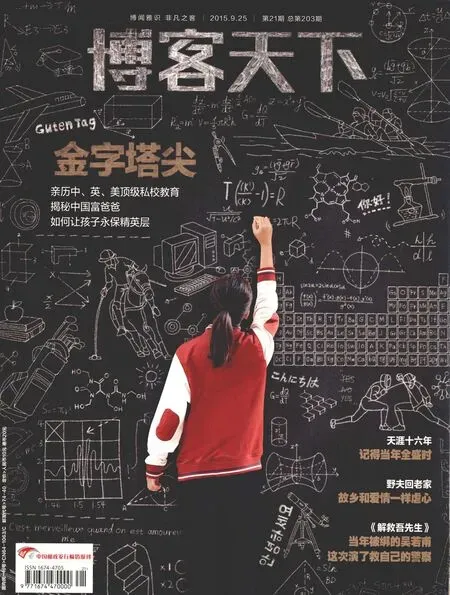李泉:所有的不自然都无法通往自由
2015-09-03李冬梅尹夕远
文 李冬梅 图 尹夕远
李泉:所有的不自然都无法通往自由
文 李冬梅 图 尹夕远
年少时痛苦的练琴经历,对名利的追逐不时成为李泉的噩梦,为了自由,他选择了流行音乐
当李泉弹钢琴唱歌时,十指好像要将琴键击碎,表情和肢体语言瞬间丰富起来。忽而怒目圆睁,忽而仰天沉醉,上一刻还在调皮嬉笑,下一刻就深情款款,黯然神伤。如果钢琴有一张脸,那么,它的表情就时刻显现在这位弹琴者的脸上。
即使在《蒙面歌王》的舞台上,藏在漆黑的蝙蝠侠面具后面,他那双写满表情的眼睛还是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有人告诉他,面具可以遮住你的脸,却遮不住你的演奏和演唱。李泉解释说,他知道自己怒目圆睁的样子“不太好看”,但那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太压抑,最后变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我今天真的没有任何悲喜,比赛只是个游戏。”在这档音乐真人秀节目中,李泉在第四轮即告失败,还沉浸在被他演绎得惊心动魄的《草帽歌》中的猜评团刚刚擦干泪水,一脸惊愕。“他的能力真的凌驾于我们之上”,他的“对手”“流浪者”说。
选择摘下面具的李泉,面对失败,眼里只有平静和羞涩。“可惜了,可惜了”,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评论,可惜的并非是李泉的过早离场,而是他的“不红”。
46岁的李泉早已过了对“不红”耿耿于怀的年纪,“想去别人玩儿的地方玩一下而已”,他这样解释自己近两年来出现在几档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上的原因。“我在玩我自己的东西,根本没想过要当第一名。玩音乐就要把音乐玩得特别潇洒。别人可以玩你的音乐,玩名次,但你不能在心里跟他们玩同一种东西。你们都在玩,但玩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

自由
14岁的李泉呆坐在剧场舞台上的那台钢琴前,汗如雨注。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等待着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第二乐章在他的十指间奏响。这是李泉人生中第一场个人音乐会。计划90分钟的演奏,已经顺利进行了一半。长达15分钟的《意大利协奏曲》是老师帮他挑的,光谱子他就背了一年半,此时,曲谱却从他头脑中不翼而飞,台下的老师同学面面相觑,观众议论纷纷。过了一会,李泉猛然站起身,夺门而逃。
“巴赫,我恨他入骨。”李泉回忆说,这个噩梦仍阴魂不散。在梦中,他是一个拼命回想着自己在即将开始的比赛中要弹奏的曲目却头脑空空的少年,醒来时,往往满身冷汗。“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曲谱)了。”又一次被这个噩梦惊醒后,李泉才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比赛过了。
李泉曾经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少年琴童”之一,被下放到贵州山区的父母把4岁的李泉“过继给了钢琴”,这是儿子的户口留在上海的唯一希望。从8岁到大学毕业,李泉是在大大小小的钢琴比赛中度过的,除了钢琴,“不知世间尚有他物”。
每到上海进入寒冬,僵直的十指触到冰冷的琴键,李泉回忆练琴之苦,“几乎每一个指尖,因为开裂都包裹着厚厚一层胶布,而考试演奏会时为了触键敏感又必须取下,害得我们每个人上台演奏前都要先擦拭前一位在琴键上留下的血迹。”在过关斩将进了音乐学院,他每天练琴至少四个小时,最高荣誉拿过亚洲钢琴比赛的大奖,但这样的成绩在强手如云的音乐附中只排末尾,因为其他同学会练七八个小时的钢琴。“我从小就生活在功利中”,他痛恨无休止的比赛、竞争,因为这些是“是非常不人性的东西”。
“我是为了想要自由才想要唱歌的。”坐在自己制作公司的办公室里,李泉将双手轻轻地搭在沙发上,窗外是一片开阔的高尔夫球场。他回忆起当年决定进入流行音乐这行时,没有选秀节目,没有《我是歌手》,中国的音乐产业也不甚发达,唱歌、写歌看上去并不能成为职业。“练琴太苦了。”所以,流行音乐拯救了他,欧美、港台、爵士、摇滚、电子、流行……他甘之如饴。
他开始自己写歌,唱歌。“每天在练琴的时候偷偷弹唱十分钟自己喜欢的歌,找三五同学围绕聆听,是一件无限惬意的事。年级舞会,大家高潮之时,我唱着自己写的歌,看着大家相拥簇簇,便是我无限满足之时。”
流行音乐成为他的“一个新的出口”。“我就觉得,哇,在这个出口里面,还有些音乐是那么真实的!这比我们从小练的辛辛苦苦去比赛,要真实得多。”
“古典音乐的叛徒”,老师和家长这样定义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剑拔弩张。李泉回忆,虽然父亲经常在外地,却经常回家检查他的功课成绩,“不行,就揍一顿”。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有一次,父亲竟然从贵州回到上海,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偷偷跟踪了他两天,为的是看他“有没有好好练琴”。结果,又是一顿暴揍。
“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这种生活没法过了。”18岁的寒假,又一次与父亲发生冲突后,李泉“突然就不行了”,“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在学校可以干坏事但是在大人面前绝对服从的人,但那天我就突然一下不行了。”趁父亲下楼买东西的空暇,他跑了出去,“大衣也没穿”,在通宵电影院和街心公园睡了四天后,他投奔了一个自己也不认识的同学,与家庭彻底决裂。
那一年,父母按计划移民美国,他拒绝同往。此后八年再没有跟父亲联系。“我前半辈子都是被强迫的。但就从那天开始,所有的世界都改变了,所有的生活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真实
“我做唱片的初衷就是‘真实’。我做第一张唱片,一开始,我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是因为要真实才选择这个行业的。”李泉告诉《博客天下》,1993年,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他与魔岩唱片的张培仁签约,“就想要自己做乐队自己写写歌”。
1992年,作为魔岩文化创始人之一的张培仁,将产业化的制造法则带入“一无所有”的内地,成功缔造了“中国火”、“唐朝”和“魔岩三杰”的摇滚神话。1994年,他以“中国摇滚新势力”之名,让内地的地下摇滚歌手像流行明星一样站在了红磡舞台上。“我那时候的革命情怀是很重的。我说革命情怀一点都不夸张,我身边那几个人包括张培仁,我们是要来这个音乐里面革命的。就是要革那些我们讨厌的假大空的命,就是要做真的东西。我们是热血的。”李泉回忆那时呼唤英雄的乐坛,每个人身上的理想主义都被点燃了。
除了“中国火”,魔岩还有一个“中国海”计划,签约对象是上海的何训田、丁薇、李泉。然而1995年,魔岩突然从大陆“战略性撤退”,没有留下任何交代便不辞而别。留下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张楚‘死’了”的江湖传说,还留下了一个茫然的李泉,“(魔岩在大陆的)整个四年我们这些人情感都是投入在里面的。我在魔岩出了两张唱片,几乎没怎么发行,也没有做过什么宣传……我当时是不接受的。我比他们(魔岩三杰)更气愤,至少他们火了一把,我什么都没有。”那时的李泉留着长发,长身玉立,器宇轩昂,梦想成为像Sting、Queen那样的巨星,把“所有人都爱自己”视作理所当然。
好好做音乐就行了。我们那代音乐人,心态要非常平和才行。他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行业里的“老工匠”、“老师傅”
带着疑惑和失落,带着滚石时代留下的理想主义烙印,李泉一边稀里糊涂了答应了系主任留校任教的邀请,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一边继续与何训田、朱哲琴们做着小众音乐,也帮范晓萱写了《我要我们在一起》《哭了》这样的流行爵士歌曲。
1999年,李泉去台湾时,跟张培仁在酒吧偶遇,“他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李泉说着,大笑起来,“这段尴尬的经历过去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他至今与张培仁仍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我的明星梦曾经做过两次。当然,第一次其实是英雄梦。”
第二次明星梦是签约BMG后,李泉觉得自己终于迈入主流唱片业,他雄心勃勃。《走钢索的人》让他在港台一举成名,公司为他量身制定“明星计划”:新加坡、台湾、香港、内地……未来看似一片坦途,“明星梦又开始膨胀了。”然而命运再次踩灭了他对声名的渴望。2000年,正准备大举进军亚洲市场的时候,台湾民进党上台,规定只要是有大陆背景的艺人都不准在台湾表演。这个规定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里没有更改过,“从那年开始我就不做明星梦了,因为我不是这个命。”
现在,在被问及命运的可能性时,他半真半假地笑着说,“如果不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的话,可能我也会变成一个明星,写着更流行的歌”,像汪峰,像周杰伦。
平和
现在,李泉慢慢走向了真正的平静。“好好做音乐就行了。我们那代音乐人,心态要非常平和才行。你有什么作用,就起一点。哪怕很小,起一点就行。”他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行业里的“老工匠”、“老师傅”。
“我是一个特别膈应的人。”李泉对《博客天下》说,以前的自己不接受媒体采访,30岁前“连谈恋爱都不说话”,到台湾某电台宣传《走钢索的人》,每次DJ问他要放哪首歌,他都要说:我现在觉得这张唱片真的做得不太好,可不可以不要放歌?有人劝他,你这首歌如果这样写,也许别人更容易接受,他说:“我如果这样写,会觉得我没穿裤子。我是习惯穿裤子的。”不被理解,他暗自感叹:“听过好的,尝过好的,可能就是一种悲哀吧。”
内地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终结于1996年。随着唱片业的急速衰落,音乐成了一门最不值钱的艺术,用李泉的话说就是,“都快成要饭的了”。
“再往下走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要妥协了。我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彻底撒一地。”
2005年,做完《划火柴的女孩》后,他决定彻底放弃歌手身份,“用其他方式去坚持”。他先后创办了音乐学校“泉音堂”和音乐公司MBOX,“泉音堂”成立的第一年,他几乎赔光了自己做音乐时攒下的所有积蓄。
“开始是我跟两个同学,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教课、写教材、弹曲子。头一年半,每天都在学校。我编了趣味性的教材,想让一个小孩一周就学会一首歌,一年会弹三四十首他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他们不需要去弹那么多枯燥的东西。”这个实验最终败给了沉疴宿疾的教育体制,直到李泉做出妥协,聘用专业的校长和管理团队,“也帮小孩考级”,才刚好能自负盈亏。
2014年6月的一天,正在跟李泉一起录唱片的李荣浩接到了电话,通知他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两人没反应过来,“莫名其妙”,五味杂陈。少有人知,十年前,李荣浩曾经是李泉与朋友合资开办的音乐公司MBOX旗下艺人,他看好李荣浩的才华,送他参加唱歌比赛,想给他出唱片。然而公司其他股东却毫无信心:谁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呢?大家更不知道如何操作李荣浩。
这正是转型成为经营者的李泉的矛盾,一方面,他内心始终放不下音乐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市场瞬息万变,音乐产业像流水线工厂,在不断复制相似的产品的标准下,没有人愿意冒险尝试新的事情,也没人愿意“花时间慢慢做”,他还签赵薇做过歌手,“因为她的演出和销量是绝对有保证的。”他想要让赵薇的粉丝“通过她去欣赏这些作品,然后慢慢改变听音乐的结构”。
什么样的想法都有过,什么样的纠结都有过,什么样的实验都做过。李泉说,他不能说是一个所有实验都做完的人,但的确想过很多东西去改变音乐市场。
2012年,在李泉放弃做歌手的第七年,他决定回来了,做一张没有任何商业考量的唱片:《天才与尘埃》。唱片是自己掏钱出的,做了两年多,头一年已经录好,他不满意,重新找了团队,重新编曲,重新写歌,反复的打磨让他几乎弹尽粮绝,收尾时,为了省钱,他住进了苏黎世一家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旅馆。
到了巡演,为演出做市场推广的甚至不是专门的演出公司,台下坐的都是朋友,台北、北京、上海,三场演唱会,“如果纯粹靠票房的话,那会很惨”,虽然演出没有挣到一分钱,但他感到了久违的松弛,“那三场音乐会对我特别重要。”他想好了,自己就想做一个反规矩的事儿。“行业已经没落成这个样子,在这个行业中你即便顺从了规矩,也是半死不活的,你还不如坚持做自己。”
“我们从小是因为追求自由才玩的音乐,后来自由变成套在身上的枷锁了。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就这样了,那你怎么办?成天躲在家里发神经?”他想通了,希望自己能活得“自然一点”。他在微博里写:“所有的不自然都无法通往自由,就像所有的不宽容都无法通往爱。”
“终于明白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尘埃。”那一年的北京演唱会,他在台上唱,台下的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他做的音乐。
责任
时间仿佛并不存在。和几十年前一样,李泉如今依然孤身一人,和几十年前一样,他在上海的家依然是理想主义者的音乐据点。“我的同事朋友都知道,我家永远都是有人的,即使我不在家的时候,也可能是有人的”。他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喜欢跟有才华的人在一起,互相激励,也激发灵感,“一块儿搞音乐的朋友,是我的哥们儿,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了。”
这些有才华的人中,有他学院时代的目空一切的钢琴兄弟聂钧,大学里终日与他排练、“聊着看不到明天的理想”的乐队哥们儿安栋,也有被他带到《蒙面歌王》的返场舞台上的电音才子B6。
钢琴和电子,也正是他在“裂变”路上的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无法调和的李泉。
十几年前那个发誓要“用自己的才能打动世界”的少年,如今只想要用音乐“跟世界聊聊天”。
2014年,他又出了一张唱片,《再见,忧伤》,“可能这将是我最没有企图心的唱片”,他的标准是自己觉得好听即可。“记得小时候写歌,就好像是要把自己炖得喷香的大酱汤倒出来给大家喝的感觉,因为那时外面好清新,内心很沸腾。现在满街闻着都是味精好喝的大酱汤,心里反沉到安静,倒要好好炖出一锅锅自己的味道来了。”
成为玩家的李泉享受着他的自由,开始频频出现在上海爵士音乐节和摇滚音乐节等现场演出的舞台上,他戴着大号荧光潜水镜与B6玩电子乐;他去内蒙古采风,去贵州做与民族音乐有关的音乐剧;跟建筑师朋友合作声音建筑展,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跟导演张元合作,拍摄音乐微电影《艳遇》。
另一方面,他仍然放不下学院派的“责任感”。要求自己“即使上电视,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表演,也要拿出以前在录音室的态度来进行表演。”《蒙面歌王》的舞台上,他选歌的标准是“值得传承”和“有价值”。“音乐首先是个行业。一个行业是怎么传承的呢?不是因为别人喜不喜欢你来传承的,而是你真正的内涵,真正的技术,真正的对这个行业追求的体现。一个艺人也好,一个艺术家也好,他应该把自己最诚恳、最经过磨练的东西拿出来,而不是像商人那样去斤斤计较别人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