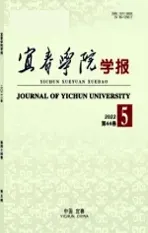“妥协论证”与“方便教化”——牟子和契嵩对于儒学的不同抉择
2015-08-15陈坚
陈 坚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什么是抉择
说到“抉择”,就会想起“选择”。从语文上讲,这两个词显然应该是同义词或近义词,然词义上有较大差别,不得混用。抉择明显有着凝重的“生死存亡”的生存论意涵,而选择则要相对轻松自由得多。如果说选择的主题是生活,那么抉择的主题就是生命;如果说选择体现人的自由意志,那么抉择就是体现人的生存困境,因为抉择是在受到特定他者制约的情况下所需要做的。虽然从语义上讲,抉择也是一种选择,但抉择是一旦选择了就无法更改因而在选择时会很有压力的那种选择,而一般的选择则即使选择了也还可以更改,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更改的话,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放弃选择,但却不能放弃抉择,也就是说,当某种抉择语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做出抉择,不抉择还不行,而且还只能由你自己来作出抉择,不像选择那样有时还可以由别人来代替。类似的抉择过程也体现在佛教初传中国时对儒学的吸收上,这在牟融(170—?)所著的《牟子理惑论》中就有明显的反映。
二、牟融对儒学的抉择
《牟子理惑论》是佛教初传中国时由东汉末年的好佛——还谈不上信佛——文人牟融。牟融,后人也尊称为牟子。《牟子理惑论》一开篇便向读者引荐了牟子:
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
可见,牟子不但好佛精通佛法,而且对中国本土的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也是广泛涉猎,尽管不见得对它们都能喜欢或认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养,所以在其所撰写的宣扬佛教但颇有点另类的问答体著作《牟子理惑论》中,牟子大量引用中国本土的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这些在自称“内学”的佛教看来实际上都属于所谓的“外道”①——来证明佛教的合理性,这是牟子对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抉择。牟子并没有专门抉择儒学,而是在抉择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过程中涉及了儒学,而且主要还是儒学,毕竟儒学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的荦荦大者,怎么可能不涉及不以之为主呢?有鉴于此,同时也是为了合乎本文主题以及方便叙述,我们这里只谈牟融以儒证佛对儒学的抉择。
以儒证佛,这难免会给人以一种“拧麻花”的感觉,为什么不直接谈佛理而要如此转弯抹角地拿儒学来说佛教呢?我们都知道,内外有别,作为“内学”的佛教本来就与在佛教的语境中属于“外道”的儒学不同(甚至是正相反对),就像生理学不同于物理学一样,尽管两者多少可能会有些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很难想象用生理学原理怎么去说明物理学问题。既然如此,那怎么能用儒学来证成佛教呢?这样做岂非方枘圆凿不相契合?然而,《牟子理惑论》就是以儒学之“方枘”入了佛教之“圆凿”,而且就这么方枘圆凿安然无恙地流传了近两千年直到现在,其故云何?我们先看牟子本人的回答:
问曰:“子云经如江海,其文如锦绣,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牟子曰: “渴者不必须江海而饮,饥者不必待敖仓而饱。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师旷虽巧,不能弹无弦之琴;狐貉虽熅,不能热无气之人。公明义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转为蚊虻之声,孤犊之鸣,即掉尾奋耳蹀躞而听,是以诗书理子耳。”(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皆引自《牟子理惑论》)
对于牟子引儒家诗书以证成佛教的“拧麻花”做法,坊间肯定不无疑虑,于是牟子遂设上述问答以消除这种疑虑。“子云经如江海,其文如锦绣”,你不是夸赞佛经浩如江海而且“文如锦绣”吗?那为什么不直接引用佛经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要舍近求远弃美从丑地引儒家的“诗书”来回答,如此“合异为同”,其理安在?难道不会驴唇马嘴吗?这是关乎《牟子理惑论》 “生死”的一个问题,真是个“大哉问”。如果牟子对此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牟子理惑论》就成了一叠废纸,就像赵本山在某小品中讽刺宋丹丹的《月子》时所说的,可以放到村头厕所里擦屁股了,那《牟子理惑论》是否真的就沦落到了《月子》的份上了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牟子是如何回应的。
牟子的这个回应,其意思有三层,(一)从你的问话中可以看出,你是同意我所说的佛“经如江海”的,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要说了,一个口渴了的人,不一定就要饮江海,一碗足已,最多两碗也就顶天了;同样道理,一个饥饿了的人,也不必要整座粮仓,也是一两碗就够了。现在对佛教因不懂而怀疑的你就像一个佛教饥渴者,我也没必要给你说“如江海”之佛经,引用点儒家诗书给你说说就行了,而(二)我之所以要引用儒家的诗书,完全是因为你对它们很懂很内行,“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你懂,所以我引;你若不懂,我引它干啥?比如(三)因为你不懂佛教不懂佛经,所以我如果引“佛经之语”来回答,那无异于是“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简直就像“公明义为牛弹清角之操”(成语“对牛弹琴”即源于此),有何益处?虽然牟子的上述回答足以堵住问者之嘴,但是却难以征服其心,也就是所谓的“口服心不服”。不但问者“口服心不服”,就是牟子自己心里也不会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毕竟不是儒家,你拿儒家的东西来为自己“作嫁衣裳”,就像拿别人的钱来买衣服,即使别人愿意,你穿在身上也不会太有滋味,这与穿着用自己的钱买来的衣服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牟子拿儒家来证成佛教,肯定是经过了艰难的抉择,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当他“锐志于佛道”的时候, “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②一句“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将牟子左右为难“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的抉择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牟子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最终作出了“引(儒家)圣贤之言证解”佛教的抉择。事不过三,聊引其中的三个证解案例:
例一
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踰经传美圣业哉?窃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子贡云:‘夫子何常师之有乎?’尧事尹寿,舜事务成,且学吕望,丘学老聃,亦俱不见于七经也。四师虽圣,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尧舜周孔且犹学之。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五经事义,或有所阙,佛不见记,何足怪疑哉?”
例二
问曰:“夫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自苦而无奇,自极而无异矣。”牟子曰:“夫长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狭后。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妻子财物,世之余也。清躬无为道之妙也。老子曰: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又曰:‘观三代之遗风,览乎儒墨之道术;诵诗书修礼节,崇仁义视清洁;乡人传业,名誉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随珠,后有虓虎,见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后其利也。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舜孔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反淑贤,以背妻子之欢,是不为奇,孰与为奇?是不为异,孰与为异哉?”
例三
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绝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夫履道者,当虚无惔怕,归志质朴,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说鬼神之余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谓见外未识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问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经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又曰:‘生事爱敬,死事哀戚。’岂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为武王请命曰:‘旦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夫何为也?佛经所说生死之趣,非此类乎?老子曰:‘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复其明,无遗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实贵寂寞,佛家岂好言乎?来问不得不对耳,钟鼓岂有自鸣者?捊加而有声矣。”
以上这三段引文,稍微有点古汉语阅读能力的人都能读懂,我在这里就不作具体解释了,其基本模式概括起来无非就是,问者指责佛教的某个观念违背了儒学的某一道理,针对这种指责,牟子毫不回避,并且还来它个“就地还钱”,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引儒学本身的思想和典故来说明佛教的这个观念其实一点都没有违背儒学,不唯不违背,反而正是儒学中本来就有的观念。在这个论证过程中,牟子也都不忘连带着引用老子道家来助一臂之力,因为在他看来“丘学老聃”老子乃是孔子的老师因而儒道一体——我把牟子这种“以儒证佛”的方法称为“妥协论证”,即他不是“愣头青”一样地非得说佛教对而儒学错了,而且退它一步甚至一万步,向儒学妥协,即我权且承认你儒学全是对的,至少我不明确说你儒学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从儒学中找出与佛教类似的思想和观念来证成佛教,从而给人以佛教其实与儒学同一鼻孔出气有时甚至比儒学还要儒学或在儒学的道上走得比儒学还要远的感觉。牟子就这样在儒佛之间证来证去,其间牟子并没有半句话要求问者一定要认同佛教,但最后就像春晚魔术红人刘谦所说的,“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哇!问者居然心服口服自愿地信了佛,这就是《牟子理惑论》结尾所描述如下情节:原本高傲的问者经过与牟子的一番问答,最后不得不“缴械投降”。他先是承认牟“子之所解,诚悉备焉,固非仆等之所闻也”,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然后恭恭敬敬地“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蒙瞽,生于幽仄,敢出愚言,不虑祸福。今也闻命,霍如荡雪。请得革情,洒心自敕,愿受五戒,作优婆塞’”,希望受佛教“五戒”做一个“优婆塞”,也就是做一个男佛教徒或男居士,而包括男居士“优婆塞”和女居士“优婆夷”在内的居士佛教,到了契嵩(1007—1072)所生活的宋代,就已经蔚为大观成了中国佛教赖以存在发展的僧侣佛教之外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地影响了契嵩对儒学的抉择。
三、契嵩对儒学的抉择
在谈到中国的居士佛教时,黄海涛先生说:“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来逐渐形成了在寺院修持的僧侣佛教和在家修行的居士佛教两大派别,两者互相支撑,彼此消长,共同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期间居士佛教随高僧大德们的弘法译经而滋生,至隋唐佛教宗派林立,僧侣佛教较为兴盛,居士佛教略显暗淡,以唐武宗、后周世宗毁佛为转折点,僧侣佛教盛极而衰,进入宋元,居士佛教得到发展,明代居士佛学达到兴盛。”[1](P220),也就是说自唐末五代宋以来,僧侣佛教衰落而居士佛教开始不断发展。居士佛教的发展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普遍认同,是佛教广泛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正面反映。不过,评说由人,既然有正面反映,肯定也就会有负面反映,天下事莫不如此。这里的所谓“负面反映”,就是一些有识之士因“僧侣佛教盛极而衰”出现种种问题而对佛教的批评乃至批判。虽然对佛教的批评和批判,自佛教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天天都有一日不无,不足为奇,但是直到唐代韩愈(768—824)因为维护儒家“道统”而极力排佛结果被朝廷贬谪潮州,才真正激起了以儒学“安身立命”的文人学士们的儒学危机感,即在他们看来,日益膨大的佛教有可能给中国本土儒学带来灭顶之灾,也就是宋儒所感叹的,“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氏”。有鉴于此,唐宋以来,一大批面对“挤儒”之佛教而心有不甘的儒学“卫道士”们便纷纷出来寻找佛教的毛病并群起而攻之。面对如此之尴尬局面(对佛教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危局而只是有点尴尬而已),一些有责任心想要“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③荷担如来家业的僧人开始“退而结网”,“面壁思过”,反思佛教的成败得失,寻找佛教因应儒者排佛的对策,其中就有契嵩。“契嵩禅师‘至钱塘灵隐,闭户著书’,契嵩禅师后住杭州灵隐寺,一室倏然,闭户著书,‘自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乃作《原教论》、《孝论》、《辅教编》三卷等,十余万言。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排佛之说,读者畏服。”[2]对于契嵩禅师这种沟通儒佛的学术努力,与其同时代曾做过屯田员外郎后弃官隐居的陈舜俞(1026—1076)曾有如下的评论,曰:
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仲灵(契嵩,字仲灵)独居,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遇士大夫之恶佛者,仲灵无不恳恳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后有好之甚者,仲灵唱之也。所居一室,萧然无长物;与人清谈,靡靡至于终日。客非修洁行谊之士,不可造也。[3](P648)
契嵩禅师就因为撰《辅教编》 “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而使得很多原本排佛的儒士(其中就包括陈舜俞)都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并与契嵩禅师交好而成为“修洁行谊之士”,也就是成了佛教居士,比如,当其“在世时,契嵩禅师与诸多禅僧和儒士就有广泛交游,彼此谈文论道,互有影响,欧阳、富弼、李覯(1009—1059)等士绅或许多因契嵩而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2]并开始学佛。关于儒士学佛,契嵩禅师曾举例说明学佛对于儒士乃是好处多多,他说:
余尝见本朝杨文公之书,其意自谓少时锐于仕进,望望常若有物碍于胸中,及学释氏之法,其物暴然破散,无复蔽碍,而其心泰然。故杨文公资此终为良臣孝子而天下谓其有大节。抑又谢大夫泌与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为人能仁贤,其为政尚清静,而其所治皆有名迹。及谢大夫之亡也,沐浴俨其衣冠,无疾正坐而尽。昔尹待制师鲁死于南阳,其神不乱,士君子皆善师鲁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会朱从事炎于钱塘,闻其所以然,益详朱君善方脉。当师鲁疾革而范资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谓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也?脉不可也。”而师鲁亦谓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说其素学佛于禅师法昭者,吾乃今资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隐几而终。余晚见《尹氏退说与其送迴光之序》,验朱从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谓佛无益于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4](P653-654)
契嵩禅师在这里提到了四个人,即杨文公、“谢大夫泌”谢泌、“尹待制师鲁”尹师鲁和“朱从事炎”朱炎,此“四君子”中,杨文公、谢泌、尹师鲁是实实在在的学佛者,而对于朱炎,契嵩禅师只是说他是尹师鲁学佛受益的见证者,未明说其本人学佛,但眼见为实,我估计他也会从尹师鲁身上感受到佛法的好处。然而,正像在《金刚经·正信希有分》中“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是不是“颇有众生”所有一切众生之类都能相信佛所说的呢?非也!“佛告须菩提: ‘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也就是说,在“如来灭后,后五百岁”的末法时期(契嵩也是生活在这样的末法时期,甚至我们现在也都还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真正有“善根福德”的信佛之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你别看有些儒士因受契嵩的影响而信佛并且从中受益,但契嵩周围反佛排佛的儒士更多,这不禁让契嵩感慨系之:“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与己教不同而然也,此岂非庄子所谓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吾欲诸君为公而不为矜也。”[4](P652)什么是“矜”呢?“矜”者,自大也。在契嵩看来,佛乃教化天下之善法,而儒士们之所以要排斥善之佛法,仅仅只是因为佛法与他们所信奉的思想不一样,这纯粹就是一种盲目的自大,与孔子在《论语》中的教导相违背,君不见“语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圣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尝以与己不同而弃人之善也?”[4](P652-653)你看,连儒士们的祖师爷孔子都教导说不要仅仅局限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而要“多闻”多听并“择其善者而从之”,决不能因为“与己不同而弃人之善”,这是何等的肚量啊!你们这些儒士怎么就充耳不闻而拼命反对善之佛法呢?契嵩在这里依然还是沿着其老乡牟子的路子“引(儒家)圣贤之言证解”佛教,而接下来,他便正面阐述了佛法对于社会的巨大意义,他说:
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恶滋甚,礼仪将不暇独治,而佛之法乃播于诸夏,遂与儒并劝,而世亦翕然化之,其迁善远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赖之,故吾谓佛教者乃相资而善世也。[4](P653)
虽然“佛之法为益于天下”非常有益于社会和个人,但“人不可得而辄见”且谓“佛为害于中国”。面对这种状况,契嵩除了殚尽竭虑地为佛教作辩护以外,更多的乃是委曲求全诉诸实践,很多时候宁可不谈佛学也要提倡儒学,以一佛之身而开启儒学之教化,视儒学为佛教的“方便法门”,主动将儒学纳入其佛学体系而实现儒学与佛学的无缝对接,比如他在《原教》中说,佛法有所谓的“五乘”,这“五乘”,“上极成其圣道,下极世俗之为农者商者技者医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声闻乘,次四曰缘觉乘,次五曰菩萨乘,后之三乘云者,盖导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洁清污直趣乎真际,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窥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胶甚而其欲不可辄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谓也,一曰不杀,谓当爱生,不可以己辄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盗,谓不义不取,不止不壤他物也;三曰不邪淫,不乱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语,谓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饮酒,不以醉乱其修心。曰天乘者,广于五戒谓之十善也,一曰不杀;二曰不盗;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语,是四者其义与五戒同也;五曰不绮语,谓不为饰非言;六曰不两舌,谓语人不背面;七曰不恶口,谓不骂亦曰不道不义;八曰不嫉,谓无所妬忌;九曰不恚,谓不以忿恨宿于心;十曰不痴,谓不昧善恶。然谓兼修其十者,报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资之所以为人也。脱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4](P649)为什么如此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佛教之“五戒十善”, “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4](P649)比如,“不杀必仁,不盗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乱,不绮语必诚,不两舌不谗不恶口不辱,不恚不仇,不嫉不争,不痴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诚于身而加于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4](P650)在契嵩看来,佛教之“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等价值观念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上乃是一回事——契嵩写作《原教》的目的就是要阐明这个观点,正如他在作为《原教》之续篇的《广原教》中所说的:“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为《原教》,急欲解当世儒者之訾佛。若吾圣人为教之大本,虽概见而未暇尽言,欲待别为书广之。”[4](P654)意思是说,我契嵩以前写作《原教》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等而同之相沟通,当时只是因为急于平息儒士对佛教的批评和诋毁,实际上,佛教的内容哪是儒家的“五常”所能涵盖?我这样做实在是有点削足适履之无奈。有鉴于此,我现在准备再写一篇《广原教》以申明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可见,作为一代佛教高僧,契嵩之将儒学引入佛教而自矮佛教,完全是出于方便教化的需要,是一种方便善巧而不是一种究竟定位,可以想见其间他肯定是经历过艰难的抉择,只是与牟子的抉择儒学思路不一样罢了。
四、两种抉择思路
要理解牟子和契嵩对儒学不同的抉择思路,看看他们两人如何处理“孝道”问题就大致明白了。在《牟子理惑论》中,有问者指责佛教“不孝”,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对于这个责难,牟子“巧妙的援引《孝经》中泰伯断发文身的故事加以申辩,指出孔子对于泰伯的行为尚且不批评其不孝,反而赞其‘可谓至德’,沙门的剃发毁服实质上是和泰伯一样的性质,由此可见,沙门的行为也并没有违背圣人之言(而)不符合孝道”。[5](P295)好,我姑且承认你佛教的“沙门剃头”亦即僧人剃发是合理的,那难道僧人不娶妻生子也是对的?于是问者进一步责难曰:“夫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对于这个问题,牟子通过援引《老子》的理论,指出妻子财务都是身外之物,追求佛道之人是不应追求这些世俗之物,而应恬淡处之,才是符合大道之妙用。牟子指出:“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舜孔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5](P295)你看,像许由、伯夷、叔齐这样受儒家推崇的圣人也不娶妻生子,那佛教僧人不娶妻生子“夫复何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和指责的呢?在牟子看来,不但儒家不反对独身,道家的《老子》更是支持独身,因为唯有独身才能了无牵挂地求道。总之,牟子为了反驳问者对佛教“不孝”的责难,并没有用佛教的思想来正面回应,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反而引用儒家甚至道家的思想和事例来证明佛教相关思想和做法的合理性。对于牟子的这样一种“妥协论证”,郭美星先生指出,虽然这种“论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有其论证的不科学性”,因为郭先生判定,向牟子发难的问者乃是一个儒者,而“牟子引用道家的观点来应对儒家的指责,这本身就是没有把握住儒道差异之根本,尤其是有关孝道方面,《论语》中早就记载有:‘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时期,儒家和南方以道家文化为核心的孝亲观念就存在本质的区别,以这样的观点来回应儒家的指责显然是不能得到儒家的认可的”;其次,牟子所“引用的被儒家称为仁者、圣人的案例来回应儒家的指责这也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知道,儒家在面对贤圣之时,是从果上讲”,而牟子“则恰好相反,以出家修道之行代果,并且以特殊性讲普遍性,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再次追问,自古以来,又有几人真正悟道呢?又有几人做到荣亲耀祖了呢?显然,为了面对儒家的指责,后来佛教徒还需要继续下工夫”,[5](P298-299)这其中就有契嵩的贡献了。
契嵩不是像其前辈牟子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以儒证佛,而是毫不隐讳地根据《法华经》的“方便”思想“当下全是”地直接将儒当成佛,将儒家思想当成佛教的“方便”来加以大力宣扬,并撰写了宣扬儒家思想的名著《辅教编》。更有甚者,他还利用自己与皇帝的亲密关系游说后者并取得其同意将这《辅教编》编入佛教《大藏经》,不但与当时天台宗提倡儒家《中庸》自号“中庸子”的智圆(976—1022)一起引领了宋明僧人的说儒风潮,而且还开了僧人儒学著作入藏的先河。所谓《辅教编》,顾名思义就是以儒学来辅助佛教教化,此时的儒学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佛教体系了,不像在《牟子理惑论》中那样儒学还是外在于佛教。我们且来看其中的《孝论》。
我们都知道,“孝”是儒家的核心理念,犹如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可见,“孝”乃是儒家仁义之根本,正因如此,所以儒家作有《孝经》。然而,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孝经》,因为后来被好事的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作了“以忠配孝”的注释而失去了其原本的淳朴,于是乎就像一个女人被皇帝巡幸后一般人便碰不得也不敢碰一样,《孝经》后来连“四书五经”都没进去,在民间更是无人敢碰(当然也有不屑于碰的)。不过, 《孝经》虽然被上收束之于高阁不待见于民间,但“孝”依然还是实际上什么时候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流行主题,而且这个主题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论的话语支撑。原本的支撑者就是儒家的《孝经》,而现在儒家的《孝经》撤出了,留下来一大片话语空白等待新的支撑者,这个新的支撑者后来就由佛教来提供,著名的比如作为“伪经”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以及契嵩的《孝论》,尤其是后者,它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儒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影响。契嵩在《孝论》开篇自述其写作动机曰:
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虽然其说不甚著明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而吾尝慨然甚愧。念七龄之时,吾先子方启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长,诸兄以孺子可教,将夺其志,独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摄衣将访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 “汝已从佛,务其道宜也,岂以爱滞汝?汝其行矣。”呜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极,何以报其大德!自去故乡凡二十七载,未始不欲南还坟陇,修法为父母之冥赞,犹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婴难,而明年乡邑亦婴于大盗,吾父母之坟庐,得不为其剽暴?望之涟然泣下。又明年,会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论》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发明吾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会夫儒者之说,殆亦尽矣。吾徒之后学,亦可以视之也。[4](P660)
契嵩在这里并没有空谈孝论,而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说明佛教徒应该尽孝。契嵩说,想当初自己出家的时候,虽然“诸兄”和“族人”都群起而反对之,但却得到了父母的允许、支持和鼓励,这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佛教都是无上的功德,他是感恩不尽的,因而时时想着“何以报其大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⑤自己出家在外二十七年,因法务匆忙,不能尽孝,即使父母亡故后,一次也没有回老家看过坟,都不知道父母的坟墓是否会遭受劫难是否还完好,想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颇有所感,于是提笔撰写《孝论》来展示自己的孝心,大有以此文纪念或献给已故父母的意思。当然,作为一代高僧,他还是想“假私济公”,希望藉此论展示佛教在“孝”这个问题上的“奥理密意”从而会通儒佛以使后辈僧众也能从中受益并杜塞排佛反佛者之口。 “在《孝论》中,契嵩列举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顺父母的故事,对出家人是否应尽孝道进行阐述,说明出家人不应忘却亲情,同样要守孝道。在契嵩看来,出家人的行善如果不能泽及生养自己的父母,那就谈不上关爱万物,更谈不上修行。他觉得出家人不应忘本,行道应从亲恩做起”,[5](P299)比如慧能大师(638—713)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你看“惠能始鬻薪以养其母,将从师,患无以为母储,殆欲为佣以取资。及还,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见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终亦归死于是也。故曰: ‘叶落归根。’能公,至人也,岂测其异德?犹示人而不忘其本也”。[4](P662)作为创宗立派的一代禅宗大师,慧能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异德”至人,然而即使是这样的高僧,也还是以“孝”为本不忘亲恩,正如他在《坛经·决疑品》中所说的,“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在慧能看来,行孝即是持戒,即是修禅。基于慧能大师这种“以孝为戒”、“以孝为禅”的思想,契嵩在《孝论》中将儒家的“孝”作了完全佛学的诠释和发挥,他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也就是说佛教比其他诸教更为尊重“孝”,因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 “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耶?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经曰:‘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4](P660)我不知道契嵩说这段话的依据何在,也不知道他所引的这段经文究竟出自佛教的哪部经,然而,在这里作考证已属多余,因为契嵩这样说只是为了传教的需要而运用一下大乘佛教的“方便”法门,既然是“方便”,那就没有必要去追究“究竟”了。按照契嵩的“方便”言说,释迦牟尼创教之初便将“孝”立为佛教的根本“大戒”,一如基督教“摩西十诫”中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 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⑥有着佛教“宪法”的地位,而且他自己之所以能“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能成佛,也是因为有“孝德”而不是其他得什么德,他这样一说无疑是将儒家的“孝”提高到了无以复加至高无上的高度,使“孝”成了凌驾于佛教一切佛法之上的佛法,直接与《金刚经·依法出生分》中所说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相矛盾。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佛教传入中国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矛盾和“方便”,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否则中国佛教只能跟在印度佛教后面亦步亦趋。回到契嵩,当契嵩将儒家的“孝”当作是佛教最高原则的时候,佛教与儒学便圆融无碍了,佛教便中国化了,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便将打破了儒佛之间的壁垒而将儒家的“孝”发扬光大到了极致,诚如契嵩所言,“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见儒而末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4](P661)而孝之所以能“至且大矣”,完全得益于儒佛圆融。
结语:儒佛圆融
儒佛圆融乃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之一,无论是牟子的“以儒证佛”,还是契嵩的“以儒入佛”(也可叫“以儒为佛”),都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儒佛圆融”的重要策略。在中国强大的儒家文化语境中,当牟子和契嵩将儒家堂而皇之地引入佛教时,儒家和佛教各自借力对方而使自己得到了比独自运营更好的传播,此之谓通过“儒佛圆融”而达到了“儒佛双赢”,习近平主席今年3 月底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就把这种“儒佛双赢”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6]可见,儒佛圆融和儒佛双赢,不仅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而且更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历史一种现实,既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也体现在个人生活中,古代有之,当代亦不无,比如梁漱溟(1893-1988),他“在《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等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其早年思想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思想近于西洋功利主义思想,第二期转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第三期再转入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变,即相当于由佛入儒”,[7](P161)以至于被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称为“最后的儒家”。然而,梁漱溟真的就成了“最后的儒家”而“纯儒非佛”了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梁漱溟确实高调宣称过放弃佛教而转依儒家,但他的这种“由佛入儒”完全是为其当年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所作的一种理论姿态,通俗地说就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至于其个人生活却是须臾不离佛教,而且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根本离不了,这不,“1987 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 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出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8]原来,梁漱溟还是一位相信“轮回”的铁杆佛教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不仅仅是梁漱溟的生活,而且还是其生命,只是在中国文化氛围下以及碍于自己先前“由佛入儒”的声明, “怕人家笑话”,所以才一直没有将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公之于众。如此看来,梁漱溟也是一位“儒佛圆融”之人,即当面向社会时,他是一位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儒者,而回到个人生活,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实际上,牟子和契嵩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儒个人佛”,即他们为了社会公众能更好地接受佛教,将儒学引入佛教,而作为一代佛教祖师,其个人生活则显然是是佛教的是阿弥陀佛人生。真是无巧不成书,牟子、契嵩都是广西梧州人,而梁漱溟则是广西桂林人,广西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向来被认为“无甚说头”,然而,这三个广西人居然却把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至关重要的“儒佛圆融”给诠释了。
注释:
①佛教自称“内学”而将其他精神体系都称为“外道”或“外学”,其中“外道”是在宗教意义上说的,而“外学”则是在佛教学术上说的。
②犹如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所说的,“然不能杜默,聊复厝言以拟之”。
③《金刚经·持经功德分》
④《论语·学而》。
⑤《孔子家语》卷二。
⑥《圣经·出埃及记》或《圣经·申命记》。
[1]黄海涛. 试论明代佛教的变革及其走向[C]//2014 崇圣(国际)论坛论文集,2014.
[2][宋]吾省. 灵隐契嵩禅师的行业道迹(二)[J]. 人海灯,2014,(3).
[3][宋]陈舜俞. 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G]//大正藏. 第52 册,CBETA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07 版,
[4][宋]契嵩. 镡津文集. 卷第一[G]//大正藏. 第52 册.CBETA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07 版,
[5]郭美星. 试论契嵩大师对儒佛合流的推动意义——以佛教“孝亲观”为中心的探讨[C]//首届杭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论坛论文汇编,2014.
[6]新华社.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EB/OL].[2014-03-28].http://edu.people.com.cn/n/2014/0328/c1053-24759429.html.
[7]刘泳斯. 简析近代儒门“三圣”与佛学思想的互动影响[M]//中国佛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谭特立. 梁漱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EB/OL].[200-08-13].http://www.xuefo.net/nr/article2/15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