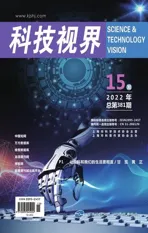论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之变革
2015-08-15王冉
王 冉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中国 天津300300)
1 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
为更好地保护海上运输承运人的利益,促进海上运输的发展,1924年8月的《海牙规则》首次确立了责任人不实际赔偿的原则,即责任限额制度。这一制度自产生后,迅速被其它产业借鉴吸收,航空业就是其中之一。在随后的短短七十年之间,责任限额制度在国际航空领域经历了一段翻天覆地的蜕变过程。
1929年10月,《华沙公约》在《海牙规则》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承运人责任限额制度,《华沙公约》第二十二条将旅客的责任限额规定为125000法郎,当时约折合8300美元;1955年9月,《海牙议定书》将责任限额由8300美元提高到16600美元;1966年5月,《蒙特利尔协议》将赔偿责任限额提高到75000美元(包括法律费用)或者58000美元(不包括法律费用);1971年3月,《危地马拉议定书》提出将责任限额提升至100000美元,但是该议定书并未生效;1999年5月,《蒙特利尔公约》突破性地规定了双梯度责任制度,对每名旅客的损害赔偿在100000特别提款权以上实行过错推定责任,100000特别提款权以下实行严格责任,这一数额于2009年经复审提升至113100特别提款权,2014年的复审维持了这一数额。
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自产生以来,赔偿数额在逐步攀升,直至《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定以100000特别提款权作为分水岭,这实际上是对规则原则划定的一个区分边界,而非责任限额的设定,公约实质上已经抛弃了责任限额制度。①故此,责任限额制度在国际航空法历史中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从无到有再到无的演变历程。
2 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的理论争议及其评述
如前文所述,承运人责任限额制度来源于海上货物运输,其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承运人利益,降低运输风险,从而促进海上运输的蓬勃发展。航空法最初借鉴此制度的理由与海商法如出一辙。华沙体系诞生之初,国际航空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科技水平的落后,对于风险防范与处理机制的不成熟,意味着承运人每一次飞行都有可能承担濒临破产的商业风险。出于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政府必须做出政策倾斜,尽可能为新兴产业创造一个健康平稳的发展环境,责任限额无疑成为一个很好地突破口。1935年在CITEJA(航空法专家国际技术委员会)会议上,Ambrosini提出,“营运人的责任必须尽最大可能地加以限制,使得航空事业能够受益。”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航空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随着各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承运人对于飞行过程中风险的预测与防范能力趋于成熟,加之航空保险机制地不断完善,企业自身力量的逐渐强大,航空产业俨然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力量的朝阳产业,此时若仍将航空产业作为弱势产业继续看待,显然已经不符。故此,作为保护幼稚产业的一种激励手段,责任限额的存在价值应该予以重新考虑。
目前学界关于责任限额的存废众说纷纭,主流观点为以下两项:保护航空利益说、保护弱者利益说。保护航空利益说对责任限制制度持肯定态度,例如,在1951年的一个巴西的案例中,法官将责任限制原则作如下解释:“责任限制原则是作为一种航空业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for air navigation)而被接受的,以避免全部财富将因赔偿请求而消失殆尽的风险,否则将导致人们对于致力并投资于交通运输服务失去信心,而这一点对于社会而言显然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③从当今航空业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各项技术水平的不断完善,承运人自己真正承担的赔偿额越来越少,因一场空难而造成全部财产损失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此,如果继续将责任限额作为激励机制的话,显然有些偏颇。
保护弱者利益说对责任限额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责任限额是政府为保护弱势产业而做出的政策倾斜的结果,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护承运人利益,这实质上是对旅客权利的侵害,因此应该废除该项制度。
对于上述观点,应当从法律、社会等各方面综合考虑,以决定对航空承运人责任限额制度的基本态度。
首先,从法律的发展来看,责任限制制度不符合法律未来发展趋势。根据上文对责任限额发展的历史逻辑探究可以发现,从《华沙公约》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关于责任限额的规定呈现从无到有又倾向于无的趋势,赔偿数额也不断增加。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走向。航空业发展至今已不再是所谓弱势产业,而旅客在谈判协商权及举证索赔能力方面远远不及承运人。法律的发展必然以实质公平为目标,这就要求逐步实现承运人责任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平衡航空承运人与旅客二者之间利益的同时,不能单纯将法律的天平倾向于承运人,从而忽略旅客的利益。从这一点来看,责任限额的存在有悖于当今法律的需求,应当予以废除。
其次,社会价值的变化促使制度进行必要的变迁。华沙体系诞生初期,国际社会的重心主要放在如何提升自身综合国力之上,而航空产业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因素,因此,为保护航空产业的发展,责任限额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纳。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出现,以及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走向开始发生转变。以牺牲旅客的权益为代价而推动整体航空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已经无法被公众所接受,责任限额的存在故此受到诟病。
再次,航空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责任限制制度相冲突。航空公司与旅客间签订的是运输合同,承运人理应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按照约定的时间将旅客送至目的地。航空公司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考虑利益相关方即旅客的期望,致力于改善公共关系,寻求更好地发展契机。随着目前航空公司自身实力的增强,航空保险机制的完善,各类航空企业百花齐放,航空公司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空难所带来的风险,而不需要在责任限额的庇护下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最后,旅客的人权越来越受到尊重。人权,简言之,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随着联合国国际大会对人权的强烈呼吁,各国对于人权的重视也开始提升。国际公约中关于承运人责任限额的设定,实质上是对旅客权利的侵害,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衡量,但是当生命被标上价位后却体现了尊严。责任限额的设定,对于将亲人视为无价的旅客家属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诉讼的尽快了结。
基于上述因素的变化,笔者认为,废除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并非那么令人不可接受,反而具有实在而正当的理由。
3 我国关于航空承运人责任限额制度的变革思路
我国关于承运人责任限额在国内与国际运输方面实行双轨制。根据2006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施行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每名旅客人身损害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根据《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为100000特别提款权(经复审提升至113100特别提款权)。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关于责任限额的赔付比例约为1:3。赔偿差距如此悬殊,相当于用国内航空产业的收益来补贴收入颇丰的国际旅客,这对于选择国内航班的旅客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农夫补贴国王的典型表现。此外,国内外关于责任限额的双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违背了国际法中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④
放眼其他各国关于责任限额的具体规定,美国、日本采取的是无限额规定,均放弃关于责任限额的适用;欧盟、韩国统一了国内外关于责任限额的规定,具体规定参照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澳大利亚国内运输赔偿责任限额为725000澳元,国际运输责任限额为260000特别提款权;印度航空法规定在旅客死亡、永久残疾且年龄大于12岁时,责任限额为375000卢比,暂时性残疾期间每月750卢比为限或以总额150000卢比为限,以较低者为准;巴西则规定在每名旅客出现死亡或伤害时,赔偿3500份国债。
通过比较以上各国对于责任限额的规定,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多倾向于选择无责任限额,发展中国家通常会根据自身国情,对于国内与国际运输赔偿责任限额做出针对性规定,但一般国内责任限额要高于国际运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沿用的40万元显然已经滞后,并且这一数额是9年前设定的,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人均消费水平及通货膨胀率等多项因素的变化,40万元已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责任限额的革新势在必行。
尽管我们赞成废除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但是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废除。虽然我国已经跻身于民航大国,但是本质上仍为发展中国家,民航业的发展仍属于过渡时期,直接沿用美国、日本的无责任限额规定显然不太现实,但是不代表以后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责任限额的废除仍是大势所趋。故此,我国关于责任限额的变革可以在改革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设置过渡性规则,最终实现无责任限额目标。
笔者认为,过渡性制度可以参照欧盟、韩国的规定,将国内赔偿责任限额与国际相统一,既可以避免双轨制带来的不公,又能够节约司法成本,与国际社会更好地接轨。同时,将责任限额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在国家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责任限额也随之提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避免出现经济单方面增长,而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滞后的尴尬局面。
在将来我国航空业真正实现规模性盈利时,则可以完全抛弃责任限额,并配套适用承运人推定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将举证责任课加在承运人身上,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性公平。
注释:
①王立志.国际航空法的统一化与我国的利益:历史逻辑与理性回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48.
②10th Session of CITEJA 1935,Doc.290,p.138.
③Apel.R rio.De Janerio 28.1.1947,1 R.B.D.A.(1951)No.1,217 at 223.
④王立志.国际航空法的统一化与我国的利益:历史逻辑与理性回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231.
[1]唐明毅,陈宇.国际航空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王瀚.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王立志.国际航空法的统一化与我国的利益——历史逻辑与理性回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4]王立志,杨惠,聂晶晶.航空旅客权益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5]乔治·汤普金斯.从美国法院实践看国际航空运输责任规则的适用与发展:从1929年《华沙公约》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6]范勤.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的承运人制度研究:从《华沙公约》到《蒙特利尔公约》[D].成都:四川大学,2006.
[7]王茵.我国航空承运人责任限额制度的检讨与研究[J].南方论刊,2007(4).
[8]刘伟民.论中国航空运输责任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3(1).
[9]孙柏年.侵权法归责原则解析[J].法制与经济:热点解析,2014(8).
[10]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策法规司.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精讲[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