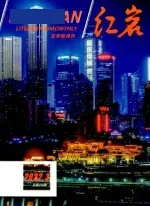诗人与散文
2015-08-15吴佳骏
吴佳骏
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散文界,以诗人身份写散文的人,委实占了半壁江山。且单就创作实绩和作品品质而论,出自诗人之手的散文作品,似乎比那些纯粹以写散文为生的人写出的作品,更具艺术含量和精神格调。客观地讲,一个诗人转写散文,往往会写得很出色。反之,若一个散文家转写诗歌,就会捉襟见肘,力有不逮。
君不见,当下不知有多少握着诗歌利刃的人,在散文领域如鱼得水,纵横驰骋,大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适和惬意,真是羡煞众多苦苦跋涉在通往散文之途上的“老帅少将”。以至于,他们后来在散文上所斩获的殊荣,早已掩盖了他们的“诗人身份”(有的干脆不再写诗,而专事于散文写作)。尤其是当他们像一头头公牛闯入疲软的散文疆域后,以独具特色的文本所引发的各种话题和思潮,更是备受文坛关注。诟病者有之,赞誉者有之。然而,唯有诗人自己,却躲在热闹与喧嚣的背后,冷眼旁观,不置可否,继续以一颗“诗人的头颅”,写着那些“离经叛道”式的散文。至于他们为何要由诗而文,原因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也许,最为合理的解释,恰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散文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实际上已经——承担起某些曾经由诗来扮演的角色。”
那么,诗人写散文,何以就能取得成功呢?
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在诗人写的散文中,除了思维方式、视觉、结构等不同于他人作品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语言修养”好。由于经历过长期的诗歌写作训练,致使他们的文字极富韵律感和节奏感。词句准确、简洁、凝练;且不乏灵动和弹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审美建构”和“叙事诗学”。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曾专门撰文谈到过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经验的散文家,语言容易变得啰嗦和夸张,这足见“语言修养”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
由此衡量与判断,本期刊发的三篇散文,均出自诗人之手。于坚的散文个性鲜明,充满智性和洞察力。他一直在践行他的散文理想,即“散文化的自由书写”。《足球记》洋洋洒洒近万言,婉转腾挪,异彩纷呈,看似谈足球,实则却是在谈历史与存在,记忆与遗忘,人心与灵魂。
何小竹的《从茶峒到苗王城》,从“田野调查”式入手,辅以今昔对比的视觉,追踪溯源,考察、洞悉一个民族的“迁徙史”和“命运史”。有凭吊与伤怀之叹,更有自豪与赞赏之喟。梳理民族历史的过程,也是作者寻找血脉和精神故乡的过程。
汗漫的《一卷星辰》,以冷静、思辨的文字,去触摸、探寻郁达夫、萧红、卞之琳、周梦蝶等前辈作家及其作品,有体温,有情怀,有观点,有剖析;最主要的,是有爱和悲悯。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是汉语文学卷轴上一颗灿烂的星辰。走进他们,便是接近了光。
在哲学家、诗人乔治•桑塔亚纳看来,与诗歌相比,散文是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而且更有责任感。这是否也说明,要写出好散文,跟写出好诗一样困难。故王国维才说,“散文易学而难工”。但诗人们的散文,无疑给立志于散文创作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