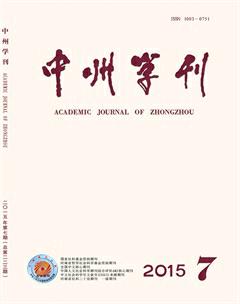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2015-07-28张培高
张培高 杨 莉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张培高杨莉
杨莉,女,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成都610500)。
摘要: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关键词:周敦颐;《通书》;《中庸》;诚;辟佛
周敦颐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通书》等。①虽然从书名上看,《太极图说》与《易通》(即《通书》)都是解《易》之书,但从诠释方法上说,两者则有较大的不同。《太极图说》基本是就《易》而发挥,而《通书》除了发挥《易》的思想外,还发挥了《中庸》《论语》《孟子》的思想,尤其是引《中庸》的思想来解《易》,同时也以《易》来解《中庸》,这是一种《庸》《易》互训的诠释方法。可以说《通书》是一部以《周易》与《中庸》为基础的综合创新之作,既可以看成是解《易》之作,又可以看成是解《中庸》之作。《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学术体系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所扮演的角色仍有所不同,大致来说,周子主要以《周易》作为建构本体宇宙论②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主要以《中庸》作为建构心性论和工夫论的依据。
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要复兴儒学回应佛教的挑战,首先要为儒家的价值观寻找本体宇宙论的依据,因为本体宇宙论是肯定世界真实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基础,而世界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是儒家价值观产生、存在的前提。周敦颐为儒家价值观寻找本体宇宙论的思路也是如此。他首先分析了世界万物的生成。他在《太极图说》中写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③要弄清这段话的意思必须首先弄清“无极而太极”的含义。而其含义,自朱陆争论以来,至今未解决。
从南宋初年流行的版本来看,首句有三种表述:“无极而太极”是“延平本”的表述,“无极而生太极”是杨方所得的“九江故家传本”的表述,“自无极而为太极”是宋史馆所修《国史》中《周敦颐传》的表述。后两种表述比较接近,那这两种版本是否可靠呢?朱汉民先生认为:“从文献学来看,九江本是周敦颐家的‘故家传本’,刊载《太极图说》的《国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典籍,这两个版本所表述的思想比较一致,所以,它们的表述是绝不能轻易否定的。”④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于:第一,朱子明确说以杨方的九江故家传本校延平本,不同的地方有19处,且这几处是“互有得失”的。朱子不满意之处在于该本的首句而已,其因在于他把“无极”理解为“无形”,而该本的表述与朱子的理解不同罢了。第二,从“太极图”的来源上看,虽然朱子肯定此图为周子自作,但他并不否定周子之学与陈抟有某种关系(“窃疑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⑤)。既然有关系,那么周子创立此图时就可能受到道家的影响。若受到道家的影响,把“无极”解释为老庄的“虚无”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无极”一词出自老庄,且周子原文明说“太极本无极”。所以,笔者认为在《太极图说》中,“无极”与“太极”是不同的。由此,笔者认为周子所建立的世界万物的生成模式是: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人)。但在周子的体系中,“无极”不仅仅是“本原”还是“本体”。所以,周子的“无极”是一个本体论与生成论统一的概念。
本体宇宙论一旦创立,回应佛教的挑战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若只讲生成论是不足以回应的。华严四祖澄观(738—839)就曾对儒家的生成论进行批评。“太极”及“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世界的本原,同时也是儒家价值规范产生的前提,而澄观从佛教的“空观”出发否定了这种生成论,认为世界万物皆是“真心”所变现。如此,世界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就被否定了,儒家伦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虽然肯定“妙有”,但更主张“性空”,认为只有“真如”才是绝对不变的本体,“妙有”只是虚幻的、暂时的存在。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为宇宙建立了一个本体,且该本体也具有绝对性、永恒性和超越性。与佛教不同,周子是要肯定世界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为儒家的价值观作论证,因此他一方面认为“无极”经过层层演化,最终生成了万物和人类,另一方面又认为“无极”是“人极”的建立依据。他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⑥虽说人与物皆是禀阴阳而生,然而人却是万物之灵,有形与知,并禀有五常之性。正是因为有“知”,故能与外物相感。人与物接触后,便有了善恶之分。朱子曰:“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又以类分,而五性之殊,散为万事。”⑦圣人有见于此,于是创立了以“中正仁义”为内容的道德规范和主静的修养方法,这一规范和修养方法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违背则凶,遵守则吉。我们可以看到,周子建构本体宇宙论的落脚点在“人极”,由“无极”到“人极”,天人由此而合一。但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规范只是“无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不是本体本身或其属性,它仅是人类的道德原则,这也就是说“在人道的理想之外就还存在一个与价值无涉的自然世界,这对于儒家价值理想的绝对性与神圣性是一种损害”⑧。如此一来,儒家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性仍然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论证。
周敦颐意识到此缺陷,并加以纠正。首先他把“太极”作为最高本体,去除了“无极”这一概念。因为若以“无”为本,便不能说“道德”是“无”本身或其属性。“道德”若是其本身或其属性,“无”便不再是“无”,而是“有”了。他看到了这个难题,在《通书》中,对“无极而太极”进行了扬弃。他说:“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⑨又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⑩这两段是对《太极图说》的解说,但抛弃了“无极”的概念,代之以“太极”。从“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来看,可知“太极”与“无极”一样既是本原,又是本体,但从内容上来说,则根本不同,“无极”是“无”,而“太极”是“有”。由此出发,他从本体宇宙论的高度论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11)“诚”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中庸》。《中庸》通过“诚”把天人贯通起来,正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2)。但与之相比,《通书》仍然有所不同,周子把它与“太极”合讲,并且把“诚”作为最高本体的属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虽然这里提及的是“乾元”,但又说“一阴一阳”,这就是说“太极”是“诚”之根源。在性质上,这种产生于本体(“太极”)的“诚”是“至善”的。“善”之依据何在?因为太极本身是至善的,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之者”即是“诚”。
“诚”不仅源自“乾元”,同时也是“乾元”的属性,更关键的还在于它是人类道德规范和行为的本原。他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13)“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百行”泛指一切行为。这些道德原则和行为若没有以“诚”作为依据,结果便是“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反之,是另一个结果“诚则无事矣”。
总之,周子一方面认为“诚”源自“乾元”,另一方面又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如此一来周子就以“诚”为中心沟通了天人,天人由此合一,正如刘宗周所说:“濂溪为后世儒者鼻祖,《通书》一编,将《中庸》道理又翻新谱,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诚,言圣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却句句指圣人身上家当。继善成性,即是元亨利贞,本非天人之别。”(14)
二、“诚者,圣人之本”与“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诚”源自于“太极”,是“太极”的属性,而人也是源自于太极的,那“诚”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或者说既然太极是“纯粹至善”的,源自于太极的“人”也应该是至善的,既然如此,为何在现实生活中人却有恶的行为,换句话说“恶”是如何形成的?在“诚”与人性的关系上,周子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性命之源,而“道”是纯粹至善的,那么源自“道”的人性也是至善的。这种本然的人性,周子以“诚”来表示,正所谓“诚者,圣人之本”(15),“圣,诚而已矣”(16)。在此,虽然他只论述了“圣人”,但圣人之性实际上就是人之性,圣人与贤人、常人之性的区别不是先天的不同,而是后天的不同。他说:“诚,无为……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17)这也就是说,“圣”之所以是“圣”在于“性焉、安焉”,贤人之所以是“贤”在于“复焉、执焉”。所谓“性焉、安焉”是说圣人能存“善”,因而能够做到“诚”。所谓“复焉、执焉”则是指贤人不能存“善”,故而需要“复性”。在此,周子虽然只讲了圣贤,但实际上常人的性也是善的,从他主张的“圣人可学”就可明了。
既然人性皆善,那恶之因是什么?周子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探讨。
第一,他认为虽然人与万物皆是源于“道”的,但人与万物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万物之灵,是有知的,有知才会有不同的想法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行为。周子说:“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18)又说:“诚,无为;几,善恶。”(19)这里的“几”和“感”与《周易》的“几”与“感”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在《周易》中,“几”主要是指客观事物的细微之象,“感”指阴阳交感。而在周子看来,所谓“几”是指“知”之微,即所谓的“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20)。“感”是指人与外物的交感,即人对外物的认识,也就是说“感”即是知。既然人是善的,那人之“知”(“几”)为什么会有善有恶呢?其原因在于人有情欲。周子说:“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21)朱子也是如此解释的:“几者,动之微,善恶之所由分也。盖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见,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此阴阳之象也。”(22)这就是说人之意念萌动之际,在天理显现的同时掺杂着人欲的成分,故而有善恶。
第二,周子除了以“诚”论“性”外,还以“刚柔”等气的特性论性。他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23)刚柔与善恶相配,形成了刚善、刚恶、柔善、柔恶等几种主要的人性类型。其中“刚善”与“柔善”是好的,而“刚恶”与“柔恶”是不好的。人要做的就是去恶从善,或去恶复善,与此同时,使刚柔相辅相成。人一旦达到了刚柔并济的状态,那就可以说达到“中”了。在此,他以“刚柔”论性与他的太极一元论是一致的。刚柔即是阴阳二气。人皆禀气而生,所以人与人之间由于刚柔有偏有正而导致有刚善、刚恶、柔善、柔恶的差别是必然的。圣人的本性是“中”,自然能够做到刚柔适中,而常人则均有偏失,故人需要改变这种偏失以达到“中”。人性有刚柔不齐的思想受到后来理学家的重视。
综上所述,周子认为“恶”之形成有两种原因:一是受到情欲的影响,二是刚柔失于偏。这两种说法之间有何种联系,周子没有明确指出。(24)此外,他对人性的论述还蕴含了后来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他一方面认为“诚”是“太极”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本性,纯粹至善的;另一方面又以刚柔等气的特性来论性。用张载、二程、朱子等人的观点来说,前者属于“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后者属于“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这两方面是不同的,但这两者的关系周子没有明确指出。
三、“主静”与“立诚”
人有了恶之后,怎么办呢?针对不同原因而造成的恶,周子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首先,针对“几”“欲动情胜”,他提出了“主静”“立诚”“知几”等修养方法。
第一,“主静”。主静是周子重要的修养方法。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25)儒家原来只讲寡欲,“无欲”本是道家的说法。周子借用道家的说法,把儒家的“寡欲”发展为“无欲”。他说:“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26)“盖寡焉以至于无”是说内心排除一切感性欲望(私欲)。如此,则能“诚立”“明通”。所谓“诚立”就是指人经过寡欲至无欲的修养之后,恢复了“诚”,从而成圣成贤。所谓“明通”就是《通书》中所说的“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27)。因为“无欲”,故而能做到“明通公溥”,若达到如此境界,与“圣人”就很接近了。这里的“明通”是指通晓易理,洞察人事之意,如此就能够克服私欲,达到“至公”的境界。当然,“至公”并不仅仅是人修养后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天道的特点。周子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天地至公而已矣。”(28)就是说,周子从修养的境界上论证了天人的合一。
第二,“立诚”。在周子的体系中,“诚”既指客观实在,又指最高本体的属性与最高的道德境界,同时还是成圣的方法。作为方法主要有二:其一,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29)。其二,诚心,“端本,诚心而矣。则必善”,“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30)
第三,“知几”。“几,善恶”,这就要求在意念萌动之际抑恶扬善,为此必须“思”。他说:“《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知几其神乎’!”(31)“无思”与“几”一样,也出于《周易》,“无思”是指易道之自然无为。而在《通书》中,“无思”则是指“诚”,就是指“寂然不动”,即没有“不善之动”。前者主要是指客观的天道,而后者主要指人的道德境界。这就是说《通书》把《周易》的“几”“无思”都作了内在主观化的解释。“无思”是本,但因为有“几”的作用,“寂然不动”“无思”的状态就会被干扰,因而“诚”就会变成不“诚”。圣人也有“几”,但圣人不会因此而失去“诚”,乃在于能“知几”,正所谓“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32)。因而,常人要复“诚”必须以圣人为榜样,在意念萌动之际、恶念未著之时,见几通微,抑恶扬善。
其次,针对刚柔失偏而导致的恶,周子提出了“至中”的修养方法。他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33)对此之恶,周子认为圣人通过教育使人达到刚柔并济,进而扬善去恶。“至其中”的“中”是指达到刚柔并济的状态,达到了此状态也就能做到中正仁义了。
最后,他提出了“立志”的修养方法。这种方法对上述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恶都适用。周子认为人有了不善之行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何谓“过”,甚至是不以“过”为“过”。只有“知过”和“知耻”,才有成贤成圣的可能。他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34)在“可教”的基础上,周子认为率先要做的是必须告诉人们自己的追求,于是他设定了一个价值追求的目标,即“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35)。圣人与天道为一体,自然能够做到静虚动直、明通公溥。贤、士都不及圣人,必须经过后天的修养。贤人以圣人为法,通过努力修养,进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普通士人则以贤人为效法对象,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进而达到贤人的境界,然后又通过努力最终达到圣人境界。虽然“圣、贤、士”三者具体的追求目标有所不同,达到的具体境界也有所差异,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成为圣人,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道德价值追求,这就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比追求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东西——“道德”。若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就能够达到“无不足”的境界。周子说:“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36)“心泰则无不足”的境界就是一种超越功名利禄,进而安然处之、怡然自得的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宋明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的境界。实际上,这种境界也就是“诚”的境界。总之,“立志”的修养方法对上述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恶都是适用的。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上文所说的“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就有“内圣外王”之意,“学颜子之所学”是内圣,“志伊尹之所志”是外王。由此可知,周子虽然讲“知几”“无欲”“立诚”等内在修养,但这不是其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外王,正所谓“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37)。由此也可知,虽然周子与佛老之人有密切来往,甚至“无欲”和“主静”的修养方法还受了佛道的影响,但周子的追求与佛道有着根本的不同:一者是济世安邦,一者是归向山林。因此,周子虽无直接辟佛之语,但其实其书是为辟佛老而作,正如高攀龙所说:“元公之书,字字与佛反,即谓之字字辟佛可也。”(38)
纵观上述可知,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其中“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的修养工夫从表面看来与《中庸》的关系并不大,但实际上则不然。因为无论是“主静”“知几”还是“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周子之学(包含对《中庸》的诠释)与二程相比有其不足之处。第一,他对人之“性”的论述还有不清楚之处,如“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就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和歧义。第二,他提出了“主静”“知几”的修养方法,但“未详细说明主静的问题,更没有讨论静坐、静修的问题”(39),也未详细说明意念萌动之际具体应该如何涵养的问题。这些内容在后来的理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
①关于周子的著作自南宋以来多有争议。潘兴嗣所撰的《濂溪先生墓志铭》说:周濂溪“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文十卷,今藏于家”。据此,朱子认为周子的著作有三种:《太极图说》《易说》和《易通》,其中《易说》已佚,《易通》即《通书》。陆九韶、陆九渊看到《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便怀疑《太极图说》不是周子的作品。今人侯外庐等学者则认为《易说》即是《太极图说》或称《太极图·易说》,《易通》即是《通书》,除此外没有另外一部称为《易说》的书。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②参见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③⑥(18)(25)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中华书局,2009年,第1—5、6、6、6页。以下仅注篇名及页码。④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⑤朱熹:《通书注·附录》,《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以下仅注页码。⑦朱熹:《太极图说解》,《朱子全书》第13册,第74页。⑧肖永明:《北宋理学与新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⑨《周敦颐集》卷二《通书·动静第十六》,第28页。⑩《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三》,第32页。(11)(15)《通书·诚上第一》,第14、13页。(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13)(16)《通书·诚下第二》,第15页。(14)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482页。(17)(19)《通书·诚几德第三》,第16—17、16页。(20)《通书·圣第四》,第17页。(21)《通书·刑第三十六》,第41页。(22)朱熹:《通书注》,《朱子全书》第13册,第100页。(23)(33)《通书·师第七》,第20页。(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三松堂全集》卷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页。(26)《周敦颐集》卷三《养心亭说》,第52页。(27)《通书·圣学第二十》,第31页。(28)《通书·公第三十七》,第41页。(29)《通书·《〈乾〉〈损〉〈益〉动第三十一》,第38页。(30)《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第39页。(31)《通书·思第九》,第23页。(32)《通书·圣第四》,第17—18页。(33)《通书·幸第八》,第21页。(34)《通书·志学第十》,第23页。(35)《通书·颜子第二十三》,第33页。(36)《通书·陋第三十四》,第40页。(37)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第523页。(38)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责任编辑:涵含
【历史研究】
*基金项目:西南石油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发展基金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宋《中庸》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5BZX061);西南石油大学校级科技基金资助项目“文化研究科研团队”(2012XJRT001)。
收稿日期:2015-01-14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7-0107-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B244.2
作者简介:张培高,男,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宗教所博士后,哲学博士(成都61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