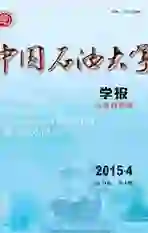论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2015-07-27董金鑫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规定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这与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虽然该制度在中国还比较陌生,但在少数的国际私法立法实践中涉及是否以及如何设置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探讨。涉外民商事审判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实践对直接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需求不足是目前阻碍立法的两大原因。为了中国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以及设立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长远看有确立之必要。未来在设计这一制度时,应特别考虑其适用的领域范围以及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关系,并对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作适当权衡。
[关键词] 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中图分类号]D9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4-0059-06
传统上,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处理需要当事人和法官从多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出选择。然而,由于各国纷纷加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如制定反垄断法、实行进出口管制以及外汇管制,且此种维护公共利益的管制性强行法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应该在系统考察规范自身的性质、目的以及适用结果之后作出决定,由此造成国际强制规范直接适用理论的兴起。所谓国际强制规范,又称为超越一切的制定法(overriding statutes)、超越一切的强制规范(overriding mandatory rules)、警察法(lois de police)、直接适用的法(règles dapplication immédiate)、干预法(eingriffsnormen),是指为维护一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重大公共利益,无须多边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于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实体强制性规范。[1]107
就来源国的不同来看,国际强制规范可分为法院地强制规范、准据法所属国强制规范和第三国强制规范。通常认为,当国际强制规范属于准据法所属国时,只要不违背公共秩序,可视为准据法的一部分;当国际强制规范属于法院地国时,如法院认为有必要同样可以确立其适用资格。[2]上述国家之外的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存在较大争议。
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4条确立了中国国际强制规范的直接适用,其范围由201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加以规定。但该制度仅限于中国的国际强制规范,对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却付之阙如,此种内外有别的做法值得探究。放眼世界,不仅作为当代合同领域统一国际私法代表的1980年欧共体《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合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第7条第1款①和2008年《罗马条例I》第9条第3款②在欧盟层面逐步统一了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而且在2000年以来正式确立国际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立陶宛、俄罗斯等18国国际私法立法中,仅有韩国、摩尔多瓦、马其顿和中国未对第三国强制规范作出规定。考虑到该制度在中国还比较陌生,既往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多,本文首先回顾中国的立法实践,进而分析阻碍立法背后的原因,最后对该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下的设置提出建议。
一、关于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中国立法实践
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长久以来不构成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重要议题,更未在法律的正式文本中得以确立。不过少数立法实践涉及如何设置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探讨。
(一)《国际货物买卖法律适用公约》修订案
为修订1955年《国际货物买卖法律适用公约》(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员参加1985年海牙外交会议审议公约的修订案。在会议上,阿根廷、美国等国在第74号工作报告中拟定了国际强制规范适用条款:公约不妨碍法院地法当中不顾冲突规范而必须适用于国际销售合同的条款的适用。如果另一国与案件有充分密切联系,可以给予该国与前款特征相同的条款以效力。
1. 中方对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提案以及回应
各国代表就法院地强制规范争议不大,而关于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则产生了严重分歧。代表中方发言的王振甫先生认为,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条款旨在维护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方不赞同该立法提议。他解释到,如果合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当事人签订的,而公约意图适用某一发达国家的法律,则可以接受上述条款。然而本次会议讨论的是由发展中国家参与且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合同的法律适用。因为营业地对当事人以及合同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利益,公约应该关注当事人营业地所属国的强制规范。中方同意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公约不应影响当事人营业地所属国强制规范适用的意见。他还认为,此类规范特别表现为各国都存在的公法性规范,如货币管制、进出口管理、环境控制等。合同当事人应该尊重并关注双方营业地所属国的强制规范,无视这些规范将会导致判决或裁决没有意义。[3]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8月
第31卷第4期董金鑫:论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与会的其他代表纷纷对中方的提案发表看法。丹麦代表菲利普先生首先回应,认为中方观点大大限制了草案规定的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他甚至认为,中方使用的术语比其意图更加狭隘。瑞士代表沃尔肯先生不赞同中方关于设置第三国强制规范的目的主要是为保护工业化国家利益的看法,该规则的适用不会先验地偏向于任何特定的法律体系,而是有助于促进国际纠纷公正解决的发展。法国代表贝罗多先生则认为,可以在原稿的基础上增加“尤其买方或卖方拥有营业地国家的法律”的语句以反映中方的意见。③最终,大会对该款进行了修改,但仍没有获得半数与会国的同意,④未能反映在1986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当中。
2. 对中方提案的评价
(1)对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的认可
参与《国际货物买卖法律适用公约》的修订是中国官方最早接触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问题。中方代表的发言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但仍有可取之处。它并非一概排斥第三国强制规范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外的直接适用,而是就第三国的范围有所担忧。那些如货币管制、进出口管理、环境控制的现代公法规范当然适用于私人跨国间的商业活动,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相互承认此种规范对涉外合同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维护规范所属国、当事人的利益,还是从规范实际能对合同以及判决执行的影响来看,都应特别考虑当事人营业地国的强制规范,而非更为宽泛的密切联系国。
(2)施加当事人营业地限制的原因
当时中方关注较多的是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即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此种基于营业地联系认定销售合同的国际性的做法一度备受推崇。1986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作为法律适用公约,注意协调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关系,也将当事人营业地作为确立适用范围的标准。如果第三国强制规范和公约适用范围采取同样的联系要求,一方面,中国一旦加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准据法之外的中国国际强制规范在其他缔约国法院就有很大的适用机会;另一方面,对中国法院而言,将第三国限于当事人营业地国不仅相对简易、方便,而且可避免考虑那些过分的域外立法,尤其是美国制定的贸易禁运令。此种行政禁令适用的标准并非传统属地或属人的范畴,而是基于货物或技术的来源、母公司的国籍等联系,要求域外适用。⑤至于采用效果原则的反垄断等竞争法,虽然在现代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确立,此时也会被中方视为霸权主义存在的表现。
(3)属人和属地因素的重合
属人性连结因素的采用不代表中方排斥履行地之类存在属地性联系的国际强制规范的适用。对当时的中国,采用当事人营业地确立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实现进出口地在中国的本国国际强制规范的适用。一方面,对双方当事人营业地不在中国而履行涉及中国的案件,如运输过境中国的外贸纠纷,当事人一般不会在中国提起诉讼或仲裁,即使在中国提起,也很少涉及中方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不多,几乎不存在涉及中方当事人的经贸诉讼不在中国实际履行或预备履行⑥的情况,故可以说属人和属地因素存在高度的重合。
(二)《法律适用法》草案
自参与1986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制定后,该制度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层面一直长期沉寂。虽然《法律适用法》确立了中国国际强制规范的适用,但只是在立法的最后阶段才被正式提出。而就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仅在2010年1月在北京拟定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立法草案稿(简称《北京稿》)中有所反映,[1]116其第5条第2款规定,根据本法确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时,可以适用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一国法律中的强制规范。⑦
《北京稿》将国际强制规范性质、目的和适用后果这类考量因素统一规定在第3款当中,即无论法院地强制规范还是第三国强制规范都应进行如上分析。此种做法构成国际强制规范适用制度较明确的双边化,赋予了法院地强制规范和第三国强制规范在法律适用上的同等地位,不仅有助于防止法院地强制规范滥用的发生,也有利于达到跨国判决结果的一致。
然而,出于贸然引入会过于增加法官理解以及外国法查证困难的担忧,这一规定最终没有体现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正式提交的《法律适用法建议稿》当中,其第7条“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仅仅指向中国的强制性规定,即本法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以后的立法审议对此也没有关注,留下遗憾。与学者的期待相左,[4]《〈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仍没有涉及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造成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尚未在中国确立的局面。
二、阻碍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确立的原因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阻碍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立法的原因
除了存在较大的理论争议外,从事涉外民商事审判的法官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和目前实践对第三国强制规范直接适用的需求不足也是阻碍中国建立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重要原因。
1. 法官重视程度不够
中国法官的整体业务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不仅表现为对国际私法的认知能力较差、认识理解不足,而且在观念上对新鲜知识不够重视。以《法律适用法》第4条为例,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认真学习,⑧但司法实践中已出现多起明显误用、滥用中国国际强制规范的案例。
在杨某诉钟某等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⑨,广东海事法院将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视为《法律适用法》第4条下的强制性规定,而该强制性规定只能是实体法规则;在上海伽姆普实业有限公司与Moraglis S. A.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中⑩,为适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上海高院援引了《法律适用法》第4条,然国际统一实体公约的适用是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非出于冲突法的考虑;在甲公司与金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争议在于当事人能否证明借贷的事实,属于法院地法支配的程序事项,但法院还是机械地以“我国法律对境内公民向境外主体借款有强制性规定”为由援引第4条,这虽然有立法不清晰的原因,但也是法官对国际私法理论不够重视的结果。再考虑查明外国法存在的问题,即使设置了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司法适用的结果也必然五花八门。
2. 实践需求不足
首先,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管仍比较多,尚不构成十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对外经济交往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在这一过程中,遵守作为东道国法的中国国际强制规范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受制于整体的法制环境和法律服务能力,中国法院很少作为中立的裁判地,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的机会不多。
其次,在实践中极少会发生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的案件。这不仅是因为适用依据的不存在而导致法院不主动加以关注,也是由于当事人根本没有提出主张。将“厦友公司诉现代会社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作为中国审判遭遇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的实例[5]并不十分地恰当。该案的上诉人厦友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为规避韩国的法律订立讼争合同,从而达到向其海外分支提供原材料的目的。一审判决将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认定为成立,没有探讨合同是否规避韩国法。由于案件适用中国法,故似乎法院无视了上述请求。然上诉人并非希望法院适用作为第三国法的韩国的管制规范,从而否定已经有效成立的涉案合同的效力,而意在表明当事人根本不具有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真实意图,即合同因存在意思表示瑕疵不成立。
除此之外,实践需求的不足也与国际政策立场有关。中国正处在韬光养晦的发展阶段,希望同世界各国发展普遍的友好关系,以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坚定奉行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际纠纷,极少通过单边对外实施经济制裁的方式推进本国的外交政策,故而对外国此类措施的域外效力鲜有关注。与之对应的是,第三国强制规范往往与国家合同相关,被认为涉及一国的统治权行为(act jure imperii),中国目前仍坚持国家及其财产的绝对豁免,推崇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纠纷,难以在司法层面探讨第三国强制规范的适用。
(二)未来的发展方向
综合现在的发展阶段、涉外民商事审判的现实情况以及当前的外交理念,似乎中国是否确立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都无伤大雅。况且虽然针对第三国强制规范进行立法日趋成为一种潮流,但就东亚国际私法的格局而言,晚近对国际私法进行全面修订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澳门、台湾地区都没有予以规定。
然而,各国相互承认并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能够促进国家间公法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国际经济治理。[6]随着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并参与全球治理活动,它必将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终究会面临第三国强制规范的直接适用问题。此类规范的适用,不仅有助于实现国际司法礼让,促进判决的一致,进而维护中国国民在对外交往中的利益,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良好的司法环境和法律服务构成自由贸易区建设规划的前提。随着上海等自由贸易区的纷纷建立,是否适用第三国强制规范更关乎中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国际上的声誉。在适用制度缺失时,目前司法实践只能借助中国的公共利益、合同发生履行不能的情形等替代性方法实现第三国强制规范所在的法律体系的指引或将此类规范作为事实予以考虑,[7]无法有效实现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的意图。故对该问题的研究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尽早着手进行中国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设计。
三、中国的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设计方案
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设计的难点在于如何解释规范背后的实质意图,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不能完全通过单一的条文予以解决。毕竟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更多提供的是判断的方法,而非能作出明确解答的系统规则。单从规范的内容看,《罗马公约》和《罗马条例I》的规定都可为中国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提供参考。本文不试图推翻现有的立法例,而只就中国在制度设计时所涉及的一些框架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存在的领域范围
关于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设计,首先要决定制度作用的领域是否限于合同。就现有的立法例,瑞士等多数国家将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作为法律选择的一般条款而适用于所有的民商事领域。土耳其明确将该制度限制在合同范畴,德国甚至将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限于合同。
就中国而言,首先,立法者没有限制《法律适用法》第4条下的强制性规定的领域范围。不过,《〈法律适用法〉解释(一)》将之限缩解释为“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解释和判断冲突法层面的强制性规定时试图与中国现行实体法的规定协调一致。《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相关司法解释要求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必须来自法律、行政法规,相应排除了部门规章及以下位阶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资格。尽管此种限制在合同以外的其他领域是否适当值得探讨,[8]但表明国际强制规范主要存在于合同领域,尤其表现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公法性强制规范。为查漏补缺的需要,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可以如《法律适用法》第4条那样不作明确的范围限制,从而构成法律适用领域的一般条款。
(二)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关系
就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关系,是否不加区分而规定相同的适用条件值得探究。除了个别的国际文件,立法多分别规定。就此种情形,又多数在同一条分款加以规定,且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在前。《罗马公约》将第三国强制规范置于法院地强制规范之前的做法只是特例,已经为《罗马条例I》所放弃。
本质上,第三国强制规范和法院地强制规范的适用标准相似。首先,对二者在适用方式和适用裁量用语差异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都需要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并综合考虑诸多因素之后才确定是否适用;其次,二者都要与案件存在密切联系,[9]且能够作用于私法关系,其区别只是第三国强制规范往往不满足法院地对本国国际强制规范的判断标准;最后,规范的性质和目的以及适用与不适用的后果应该构成所有国际强制规范适用考虑的因素。在法院地强制规范和第三国强制规范发生真实冲突时,应优先维护法院地强制规范所保护的利益。除此之外,过分强调二者的不同难以达到国际私法追求的法律交换目的。
但考虑该问题的复杂性,且不破坏《法律适用法》第4条对中国国际强制规范适用的规定,单独确立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也是较稳妥的方式。另外,《北京稿》将是否适用所要考量的条款作为共通的因素,实现了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部分要件的统一,此种做法也值得考虑。
(三)具体内容的适当权衡
就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条文的设计,应就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作适当权衡。如果对第三国强制规范一概不予认可,实为新的法院地主义,不仅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与案件的公正审理,还会导致挑选法院现象的发生;然此类规范的适用如不加合理地限制,同样会损害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预期、提高缔约成本,最终阻碍国际商事交易的顺利开展。故不仅需要制度条文设计时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还要求作出裁量的法官具有较高的冲突法素养、丰富的比较法知识以及宽广的国际视野。为保证法律适用的公平,在此限制过程中需要特别考虑联系的要求、规范的性质以及适用的后果。
联系要求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设计领域范围以及如何处理与法院地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关系。从现有的立法实践看,如果仅于合同领域,《罗马条例I》对履行地的规定至少在逻辑上可行;但一旦将该制度推向所有的民商事领域,采用密切联系的《罗马公约》更具吸引力。另外,尽管密切联系存在模糊,需要通过司法实践加以类型化,但在条文设计中似乎难以过多解释。特殊情况下存在解释困难的履行地联系虽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毕竟构成合同领域最重要的连结因素,与中国修订《国际货物买卖法律适用公约》的提议不存在根本冲突。故可在采用密切联系的同时特别声明关注履行地国法的要求。
就规范的性质以及适用的后果,可以仿效《罗马公约》或《罗马条例I》那样较为笼统的规定,将自由裁量的权力交由法官行使。但为了实现裁判结果的一致,更宜考虑借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加以细化,即对规范的性质、目的作正当性与合理性分析;而就适用或不适用所发生的后果,在这一过程中应明确考虑对有关国家以及当事人所产生的影响,以真正做到当事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包括国际礼让在内的国际利益的平衡。
四、结语
根据上文的分析,并参酌《北京稿》第5条第2款、《罗马公约》第7条第1款以及《罗马条例I》第9条第3款的规定,拟定独立、全面的中国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条文如下:
可以给予与案情有密切联系的第三国的强制规范以效力(在合同领域特别表现为履行地国法的要求),只要此类规范根据该国法律必须适用。
在决定是否给予此类强制规范以效力时,应考虑到它们的性质、目的是否正当、合理,以及适用或不适用对有关国家以及当事人所产生的后果。
注释:
① 当根据本公约适用一国法律时,可以给予与案情有密切联系的另一国法律中强制规范以效力,只要此类规范根据该国法律必须予以适用而无论合同准据法为何。在决定是否给予此类强制规范以效力时,应考虑性质和目的以及适用或不适用的后果。
② 可以赋予那些合同债务将要或已经履行的履行地国法中超越一切的强制规范以效力,只要此类强制规范能够导致合同履行不合法。在决定是否给予此类规范以效力时,应考虑性质和目的以及适用或不适用的后果。
③ 如果另一国与案件有充分密切联系,可以给予该国与前款特征相同的条款以效力,尤其当事人营业地国的法律。
④ 投票结果如下: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佛得角、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塞俄比亚、民主德国、匈牙利、伊拉克、韩国、马耳他、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土耳其、苏联及英国22国反对,阿根廷、加拿大、芬兰、法国、联邦德国、几内亚、洪都拉斯、伊朗、爱尔兰、以色列、卢森堡、墨西哥、荷兰、西班牙、瑞士、泰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及南斯拉夫20国赞成,印度、日本、莫桑比克、也门未投票。
⑤ 1979年《美国出口管理法》规定,总统有权禁止或减少处于美国管辖或由美国管辖的任何人进行的任何货物、技术或其他信息的出口。
⑥ 如采用CFR交易条件的外贸合同,在国内港口起运或在第三地如中国香港转运。
⑦ 第1款规定中国国际强制规范的适用,“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第3款规定前两款适用应考虑的因素,即“适用强制性规则时,应该考虑强制性规则的性质、目的以及后果”。
⑧ 见《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知》。
⑨ (2011)广海法初字第373号判决书。
⑩ (2012)沪高民二(商)终字第4号判决书。
公约在中国的适用依据有《民法通则》第142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4条。
(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1262号判决书。
(1999)经终字第97号判决书。
见《土耳其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程序法》第31条。
见198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第34条。
《〈法律适用法〉解释(一)》针对《法律适用法》的总则部分,如果希望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尽早出台,纳入针对具体领域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二)》是稳妥的做法,可以考虑将之限于合同领域。
如《代理法律适用公约》第16条、《合同与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公约》草案第7条。
《土耳其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程序法》将第6条和31条分开,是因为法院地强制规范的适用构成法律选择制度,故在总则规定;第三国强制规范仅限于合同,故规定在合同部分。
参见2012年《捷克国际私法》第25条、《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条。
参见2005年《罗马条例I》草案第8条第3款、《罗马尼亚民法典》第2566条第2款。
[参考文献]
[1] 肖永平,龙威狄.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J].中国社会科学, 2012(10).
[2] 董金鑫.国际体育仲裁院普通程序案件的实体法律适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4(7):33.
[3] Antonio Boggiano.The Contribution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Latin America[J].Recueil des Cours, 1992:148149.
[4] 卜璐.国际私法中强制规范的界定——兼评《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J].现代法学, 2013(3):150.
[5] Yong Gan.Mandatory Ru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Yb. Priv. Int. L., 2013:319.
[6] 王立武.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J].政法论丛, 2012(1):14.
[7] 肖永平,董金鑫.第三国强制规范在中国产生效力的实体法路径[J].现代法学, 2013(5):142.
[8] 肖永平,张弛.论中国《法律适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2):117.
[9] GralfPeter Calliess.Rome Regulations: Commentary on the European Rule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M].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1:206.
[责任编辑:陈可阔]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pplicable Institution of Thirdcountry
Mandatory Rules in China
DONG Jinxin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Law of the PRC on Application of Laws to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s does not define the applicable institution of thirdcountry mandatory rules,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custom. Although this institution is still relatively unknown in China, there are a few legislative practic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volving whether and how to establish i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reasons of impeding the legislation currently: One is that judges engaged in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s fail to take it seriously enough; the other is that practices are in insufficient demand of immediate application of thirdcountry mandatory rules. To meet the need of Chinas wid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setting up freetrade zon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pplicable institution of thirdcountry mandatory in the long run. When designing the institution,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cope of its application as well as its relation with the applicable institution of mandatory rules of the forum. Whats more, whether and how to apply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ppropriately.
Key words: thirdcountry mandatory rules; applicable institution; Law of the PRC on Application of Laws to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