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中他者的建构
2015-07-24龙雪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宁530004
⊙龙雪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宁530004]
《最蓝的眼睛》中他者的建构
⊙龙雪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宁530004]
《最蓝的眼睛》是享誉世界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故事讲述一个年仅十一岁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游走在学校和社区的边缘,处在社会的底层,渴望获得最蓝的眼睛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处在他者地位的佩科拉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呼唤。本文拟细读文本,以佩科拉为研读对象,解读故事中黑人小女孩的他者的建构。
《最蓝的眼睛》黑人小女孩他者的建构
一、引言
《最蓝的眼睛》是享誉世界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故事发生在作者的家乡——俄亥俄州一个名叫洛兰的小镇。故事通过一个九岁的黑人小女孩克劳迪娅的讲述展开。佩科拉·布里德洛夫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黑人小女孩。因为黑皮肤,佩科拉在学校里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和欺负;在家里被父母忽视;在社区里则不被大家接受:她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长相丑陋、没有蓝色的眼睛。于是佩科拉日夜祈祷能够拥有一双最蓝眼睛:因为只有拥有了蓝眼睛,她才能像美国所有金发碧眼的孩子一样美丽,一样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接受,才能改变她处于弱者的地位。在对蓝眼睛的期盼中,佩科拉被亲生父亲糟蹋,并且怀上了父亲的孩子。孩子的早产和夭亡使得佩科拉发疯了,从此进入了混沌的世界。小说通过克劳迪娅的讲述和作者全知视角的运用,清晰地建构了女主人公佩科拉的他者,并发出他者的呼唤。
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曾提到“同者与他者”(the same and the other)的关系,他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柏拉图提及的“同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他者”是相对于“自我”以外的概念,是指自我以外的人与事物。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他者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深厚的渊源,在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也被广泛地使用。他者暗示了边缘、低级、被压迫、被排挤、被剥削的状况。
他者的概念,首先被女权主义者运用到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即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进而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父权社会的话语之下,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受男性主宰。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因为她们的身体缺少某些性质。”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女人是一个“构造不完整的男人”。其他作家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因此造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就无所适从。进而,女人是依附于男性的他者。而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主要探讨妇女的生存状况,后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上卷深入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种种神话,下卷则主要说明当代妇女从少到老的实际生活经历,研究她们的共同身心状况与生存处境。她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人类的文化整体产生了所谓的“女性”。波伏娃认为,在不少男性作家,如蒙泰朗、劳伦斯、司汤达等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而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男人是社会的引导者,而女性只是依附于男性的被引导者。这实际上表明了女性他者的地位,女性只需要依附于男性、服从男性的权威即可。这事实上是构建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女性是变成他者的,而并非是他者。
小说《最蓝的眼睛》,故事中年仅十一岁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出生于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父亲是一个脾气糟糕的酒鬼,母亲则向往白人家庭,因在白人家庭中帮佣而深感自豪,因喜欢白人家的小女孩而忽视对佩科拉的照顾。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佩科拉,人人避免用眼睛看到佩科拉,男孩子则以捉弄佩科拉为乐。社区里,糖果店的白人老板对佩科拉视而不见,人人对她指指点点。游走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边缘,佩科拉只能是一个弱者,处于他者的地位和生存现状。
这样的生存现状使佩科拉意识到,原因就是自己长得丑,没有最蓝的眼睛。因为学校上课用的课本告诉她,蓝眼睛才是最美的。于是,没有父爱母爱的家庭里艰难度日的佩科拉为了改变这样的生存现状,只得日夜祈求上帝,赐予她一双最蓝的眼睛。因为只有拥有了最蓝的眼睛,佩科拉才会变得漂亮,人们才会喜欢她,而不是歧视和忽视她。这是佩科拉内心深处最歇斯底里的他者的呼唤和呐喊:一双最蓝的眼睛。
二、种族他者的建构
所谓种族他者,指非白人民族,包括非洲、亚洲的马来人和中国人以及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人等。这些他者的表现,就是话语权的不对等性,以及人体外貌特征在视觉效果上的差异等等。对应当时的时代特征,“白人优越论”,除了白人的其他种族,无论是在知识水平上还是外貌长相上,都无法与白人相比拟,这使得黑人无形中更处于社会的边缘。相对于黑人女性,则更是处在社会的边缘,甚至是底层。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建构了一个长期受到遮蔽的他者,时刻受到来自种族的遮蔽和压迫。

在故事的开端,作者用三段一样的话来描写白人居住的漂亮的房子的模型:“这就是那所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非常漂亮”,“这就是那家人……他们生活得很幸福”,那所房子已然成为了白人社区的一个标志,只有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人才会生活得幸福。而与这个理想家庭居住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佩科拉黑暗且不和谐的库房。而这样的不和谐,是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生存的空间的显著对比。克劳迪娅去找佩科拉时看到了布里德洛夫太太帮佣的那家人的房子则完全符合了理想家庭的标准:“离公园入口处不远的地方就是有长满鲜花的手推车的大白房子。”进到白人的房子,“我们走进厨房,是一间很大的屋子。白色的瓷器和木器,以及擦得锃亮的壁橱和铜器把布里德洛夫太太的皮肤映照得像塔夫绸那样的光亮”,这就是白人的家庭:干净,漂亮,宽敞。和黑人肮脏,黑暗,狭窄的社区相比,更凸显了黑人生存环境的狭窄和黑暗,黑人的家庭没有理想家庭模式中那种绿白相间的大房子,没有长满鲜花,更谈不上漂亮。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生存环境的强烈对比,凸显黑人生存环境的贫瘠。
在黑人社区里,白人对佩科拉视而不见,黑人则是对她不接受,让走在黑人社区里的佩科拉深感要想摆脱现状只有获得蓝眼睛。
糖果店主让黑皮肤的佩科拉有了不可言喻的羞耻感。“他迫使自己将目光朝她转去。蓝眼睛,但红而无神”,“在时空的某一固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他的眼神。他并没有看见她”,“一个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小店老板……怎么会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短短的一段话里,作者用了“目光”“蓝眼睛”“看见”等几个和眼睛有关的词语,更突出了这样的蓝眼睛看待自己的眼神,于佩科拉而言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羞耻感。社区里,人人对佩科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是有意地回避她。在蓝眼睛的注视下,佩科拉感受到的只有羞耻感,不断上升羞耻感。
作者建构了一个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他者:黑皮肤,没有蓝眼睛,这是佩科拉改变现状。游走在社会的底层,佩科拉坚信唯一的方法就是获得一双美丽的蓝眼睛。

学校里建构的他者是识字课本上教育孩子们蓝眼睛为美。因为没有蓝眼睛,老师们忽视佩科拉,尽量避免看到她,黑皮肤的男孩子们则尽其所能地欺负佩科拉,这些行为让佩科拉深深地觉得只有蓝眼睛才是解决学校里的歧视的关键。
因为丑,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都鄙视她。她是班上唯一单独使用双人课桌的人,“所有的老师都这样对待她。他们总是避免看她,只有当全班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叫她”。学校里老师们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佩科拉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佩科拉是黑人,长得丑,没有白人孩子的金发碧眼。而学校里黑人男孩子对佩科拉的捉弄和辱骂,使得佩科拉的心里更认定自己是丑陋的,自己更需要的一双蓝眼睛。学校里建构的他者凸显了种族的歧视。“有一段时间,佩科拉意识到如果她的眼睛——目睹那些画面和场景的眼睛——不同的话,就是说,她有双美丽的眼睛的话,她本人也会不同。”而这所谓的不同,就是拥有一双蓝眼睛。学校里同是黑皮肤的男孩子的欺负行为因为一双蓝眼睛而停止。学校里的歧视使得佩科拉在学校里的任何地方都感到不自在,没有归宿感。面对这样的歧视和周围人对蓝眼睛的喜爱,这样的束缚,佩科拉更认定,只有拥有一双蓝眼睛才能改变这一切。
本该是平等、有爱的学校,却人为地建构了他者。不平等和歧视迫使佩科拉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他者的地位,而这只能借助于一双最蓝的眼睛。

在佩科拉的家里,父亲乔利酗酒,懒惰,脾气暴躁;母亲布里德洛夫太太也是脾气暴躁,一方面自认为是位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乔利的罪孽。“他越堕落,越无信义,越无法无天,她以及她的使命越发崇高。”后来,布里德洛夫太太在白人家庭里做帮佣,忽视家庭,对白人家庭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宠爱有加,对佩科拉则不闻不问,甚至是打骂。哥哥山姆或是出走或是加入父母的战斗中。佩科拉则不得不忍受父母的战争而在痛楚中生存。雷蒙斯曾说过,家庭是因爱而爱的,可是“布里德洛夫”一家,名字是繁育爱,可是却缺乏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佩科拉一直以为父母不爱自己,是因为自己长得丑,自己没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所以佩科拉日夜向上帝期盼的是拥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而在对蓝眼睛的期盼中,佩科拉却两次遭到了父亲的践踏,并怀上了父亲的孩子。
“繁育爱”的家庭里并没有爱,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父母都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也缺乏足够的责任。所以,当乔利在对佩科拉施行兽性的行为时候,丝毫没有一丝愧疚和罪恶感。而读者在不少的黑人文学作品中,均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女孩子在家庭里不安全,她们要提防来自父亲、叔叔,甚至是哥哥的危害。家庭本该是人生最温暖的港湾,可是黑人家庭里女性是不安全的。这无疑让黑人女性在家庭中也处于他者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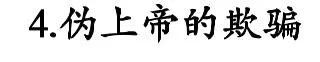
怀了父亲孩子的佩科拉,不再上学,走在社区的路上,人们总是对她指指点点,说她败坏道德。似乎造成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佩科拉的不道德,事实上,却是因为父亲的兽性爆发。佩科拉,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承担的却是两个成年人犯下的过错和罪恶。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佩科拉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被遮蔽,他者的地位和处境已经将佩科拉重重地压在了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底层。面对生活的困境而无法自救的情况下,佩科拉只能求助于上帝让自己变美,而通向上帝的路就是社区里的“皂头牧师”。
炎热的下午,佩科拉求助于皂头牧师:“我想让眼睛变蓝。”听到佩科拉的这个请求,皂头牧师犹豫了,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听到的最荒诞同时也是最合理的请求。一个丑陋的小女孩请求变美”。毫无疑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如果,拥有一双最蓝的眼睛可以使自己变美,变美仅仅是改变自己的他者的地位的话,那么就算是外貌变美了,他者的地位在实质上仍然无法改变。皂头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赐予佩科拉一双最蓝的眼睛。在皂头牧师的指引下,佩科拉接过牧师递过来的有毒的肉给老妇人的老狗吃,并看着狗在自己的面前死去。根据皂头牧师的说法,如果狗的举止反常,那么佩科拉的愿望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实现。事实上,狗确实被毒死了,佩科拉却仅仅是在幻想中得到最蓝的眼睛而已。换个说法,佩科拉也被这个说法和想法给毒害了。在故事的叙述者和佩科拉的对话中,佩科拉语无伦次地强调自己拥有了最蓝的眼睛。从这里,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佩科拉已经走向了混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他者。作者借助万能的上帝建构了一个他者,因为号称万能的上帝也不能帮助佩科拉实现自己的愿望,改变佩科拉他者的地位,改变他者的处境。
种族的他者,使得身为黑人女性的佩科拉不具备白人的金发碧眼,在外貌上无法和白人比拟;怀孕后辍学的佩科拉永远无法在学识上有所长进,处于知识的他者的地位。
三、文化他者的建构
白人文化盛行的时代,灌输给黑人的是白人才是美的标准。白人文化的不断输入,使得黑人文化不断地被抛弃。而黑人女性相对于黑人男性而言,更是他者,因为生而平等的权利并未赋予黑人女性。
佩科拉到底长相如何,故事中并未详细描述,“当你注视他们时,你会纳闷他们为什么这么丑陋。你再仔细观察也找不出丑陋的根源”,由此可见,他们并非真的丑陋,“之后你会意识到丑陋来自信念,他们对自身的信念。似乎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给他们每个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而他们不加疑问便接受下来”。作者的描述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经历多年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终于演变成了波澜壮阔的黑人权力运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身体。但是,针对白人社会传统的认为黑人丑陋的观点,一些黑人简单且得意地提出了“黑人是美的”口号。对此,莫里森有她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身体美是一种白人的价值观念,即使按照这一价值观念把“黑人丑”变成“黑人美”,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奴役的后果。而佩科拉,则将这样的信念作为自己的面具天天戴着,并遭受着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就是在这样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学校的歧视、社区里的不接受,所有的不幸都聚焦在佩科拉没有一双蓝眼睛,于是就造成了佩科拉精神的扭曲、异化,在日夜对获得蓝眼睛的期盼中——佩科拉疯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也被扭曲和异化了。文化建构的他者,使得黑人盲目的以“黑人是美的”变成自己的信念,并深深印刻在自己的文化里。而文化建构的他者,让女性处在文化的边缘,女性只有美才能赢得别人的认可。
在这片黑人社区里,有着和佩科拉一样观念的黑人,他们同样也生活在他者的处境,被白人审美标准的不断异化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黑人文化和传统,他们自己给自己建构了一个文化他者。布里德洛夫太太像白人学习——看电影,梳白人一样的发型。“唯一让我快乐的时光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一有机会我就去那儿”,“白人男人对他们的女人真好,他们都住在整洁的大房子里,穿着讲究,澡盆和马桶在同一地方。这些片子让我快乐,但是也让我难以回家,难以面对乔利”。故事中这段斜体字是布里德洛夫太太的描述,字里行间反映的是她对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向往,喜欢并且享受白人妇女的打扮,以及对黑人的生活环境的憎恶。而她也在看电影中不断地被白人化,不断地腐蚀自己,就像牙齿被腐蚀一般地腐蚀自己。当山姆和佩科拉还很年幼的时候她又出门工作了。她所帮佣的这个家庭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模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她感觉自己也像一个白人一样地生活了。“像孩子的粉红睡衣,一摞摞的绣花枕套,带蓝色矢车菊的床单等。她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理想的佣人,而这个角色也完全满足了她的需要。”从此,她将全身心地为白人尽善尽美地工作,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文化他者的地位。
学校里识字课本上告诉小孩子蓝眼睛才是美的,从教育上给孩子们建构一个文化的他者。事实上,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其背后发出的声音告诉人们,蓝眼睛并不一定是最美的,最美的是心灵美,是坚毅的性格和顽强的勇气。从佩科拉的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他者,恰恰缺乏就是一种坚毅的性格和顽强的勇气。
四、结语
莫里森密切关注黑人的生存和文化,通过一个九岁的黑人小女孩叙述和作者全知视角的运用,将故事中以佩科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受到白人的美的标准的文化歧视、种族隔离和歪曲下他者的地位和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白人文化价值和审美标准的不断灌输之下,黑人女性向往白人的审美,逐渐内化了他者,精神空间的扭曲、变形、异化,也造成了佩科拉的悲剧。佩科拉的悲剧源于她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将他们置于文化空间的边缘和底层,别人为自己建构了一个他者的同时,自己也给自己建构了一个他者。
也正如托尼·莫里森对自己创作最中肯的评价是:我的作品源于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不管整个故事的基调是多么压抑,读者总能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黑人民族的希望,看到她作品中丰富的黑人文化,为黑人女性他者的建构提出思考。
[1]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 York:Plume(Penguin Group),1990.
[2][美]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海口:南海出版社,2005.
[3]郭宇飞.白人文化霸权下的黑人自我否定——从《最蓝的眼睛》透视出的看法[J].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11(5).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5]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2011(1).
[6]祝远德.他者的呼唤——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作者:龙雪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