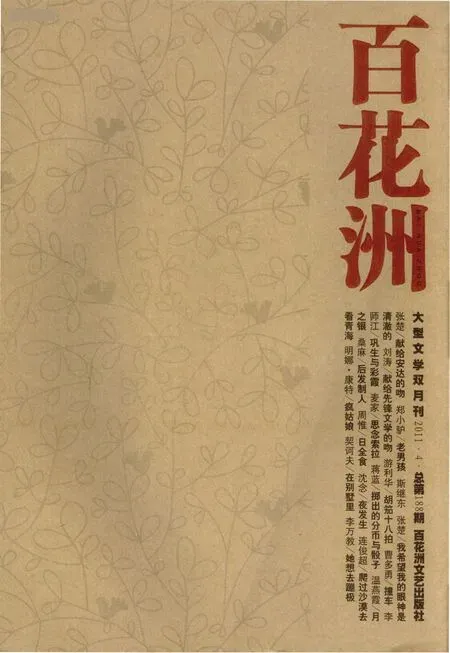命运分岔的三台海子
2015-07-13杨方
杨 方
命运分岔的三台海子
杨 方
出城,一个人投荒而去,马不停蹄地西行八百里,就到了三台海子。
这是天山山脉隆起的边缘,有零星分散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在山下居住。海子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湖泊,在海拔2073米的地方,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一片又大又蓝的水域,面积足有460平方公里。从事地质考察的人说,这个湖泊属封闭型断陷湖,是地壳下沉形成的洼地,由四周的高山雪水经历百万年慢慢汇聚而成。它像是时间的湖泊,在时间的虚无里一切都是乌有,呈现出墓地般的沉静。但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圆,从地图上看略呈椭圆,如一滴不小心掉在彩色纸张上的水珠,浓缩的蓝在你眼前魔幻般地荡漾,然后扩散到你的眼珠子里,随着瞳孔的无限放大,你以为自己已经淹死在窒息的蓝色之中。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真实的湖一下子在你面前铺开,地平线完全被蓝色所淹没,你会以为自己旅行到了天上。凛冽的风吹走了你熟悉的一切,包括前方的道路,你将要去往的城市和你居住的国家。你的眼睛里到处都是天空一样的蓝,你无端端的,就会感到呼吸艰难,仿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氧气。
作为一个路过此地的人,你不可能对一座湖知道得太多。三台海子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它在地图上的叫法是赛里木湖,这应该是曾经征服此地的蒙古人的语言,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清代在湖的东岸曾经设立鄂勒著依图博木军台,军台即三台,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北道。从伊宁出发,经霍城、清水沟、芦草沟、果子沟到达此地,往南去往一个蒙古人聚居的高原城市,往东经四台、五台去往另一个城市,那是个人口混杂的大城市,有汉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锡伯族人和无处不在的回回,却几乎见不到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的踪迹,他们的马匹不允许进入有红绿灯和清扫工的街道,他们只能留在草原上,留在过去的生活方式里保持着不变。
要描述这座高山湖多少有点困难,它太像一个幻影了,太阳,月亮,星星,云朵以及危峰耸立的雪峰,从不同角度,不同高度照耀着湖面,天庭的光泽与水光相辉映,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面积巨大的神话,当你看见它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失去模糊的界限,一点一点融入蓝色而低垂的天穹。
而你身在其中却不着边际,你仿佛被什么东西卡在那儿了,进不得退不得,最后只能长叹一声,丢鞭,弃马,做长时间停留下来的打算。
第一天,你发现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像草一样被种植。你在湖边的时候你是蓝,你离开湖走进草地你就是绿,草叶与草叶之间发出霍霍的摩擦声,它们朝你的脖子里嘶嘶地吹吐着凉气。你坐着,躺着,或站起来不停地移动,无论到哪儿,都逃脱不了它们的纠缠和排挤。你用三分钟躲开的轮台草,它只用了一秒钟就赶上了你的脚步。被七零八落打断筋骨的瑞香狼毒,你一住手,断肢残体就落地生根,长成新的一丛,用尖锐的视线逼迫你道歉。你感受到植物野性十足的体力,甚至嗅到它们密谋挟持你的危险气息。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想方设法让你变成一株植物。真的,在这里太阳长长的爪子,因为少了城市灰尘和雾霾的阻隔,可以直接触碰到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不可避免地和周围的草一起进行着光合作用。强烈的紫外线不能使你变得更黑,只能使你变绿。
接下来你会更加惊讶地发现,一座山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植物分布带。你的脚边,湖的舌头一下一下舔着岸边圆滑的石头,像舔着甜蜜的水果糖。水边的菖蒲是湖的胡子,过了夏季会结出俄罗斯熏肠一样的果实。另外一种植物马莲草,叶子是草地的绿,花朵是湖水的蓝,它有机地结合了地理版块自然分割的颜色。其间一群羊在头羊的带领下,引导了你视线的缓缓移动和上升,它们先是从湖边经过,影子掉进虚幻的蓝色湖水里。当它们离开湖岸的时候,就像是一群从湖里走出来的水生动物。你看着它们带着做梦一样的表情,穿过山脚的阔叶丛,山腰的针叶灌丛和革叶灌丛,沿着地形分布的规律,走向陡峭的高山带,那里,低矮、寒生的蕨类和地衣,远不及山下常绿的丛生杂草美味多汁。牧羊的哈萨克人使劲吹响了口哨,但口哨似乎失去了平日的魔法,再不能把一群羊乖乖地召唤回来。它们像一团出窍的灵魂,轻飘飘地越过夏季雪线,出现在高寒的草甸地带。羊群在那里略微停顿了一下,整理好身上的裙裳和被风吹乱的队形,然后继续向着虚幻的冰雪带飘移。
你没法知道这些淡泊的,月光一样的羊群到底要走到哪里去。你和哈萨克人一起伤感地坐在弓起的山脊上,看着它们越走越远,越走越缥缈,最后它们终于走到了天上,成为一团蓬松的云朵悬浮在你们的头上。你怀疑这群羊原本就是天上的,它们原本就是离群的事物,喜欢飘零在自身之外。下雨的时候雨打湿了它们,体重的增加使它们无法继续漂浮在空气中,只能顺着雨水落进湖里,湖水把它们像仙女一样洗得更白更干净,然后一群羊在头羊的带领下从水里走上岸,头也不回地旅行在肋骨起伏的山体上,又一次回到了天空中。
哈萨克人否定了你的想法,他的每一只羊左耳朵上都有烙印,是用烧红的火钳烫出来的,形状是部落姓氏的符号。如果仔细辨认,不难发现天空有一部分的云朵上隐约显示着这样的符号。另外一部分没有符号的云,肯定不是他的羊,从尾巴上看应该是山那边蒙古人的羊,他们喜欢养新西兰大尾巴绵羊,那些羊从地球另一边过来,边走边拉屎,像彗星尾巴上一路掉落的闪光。哈萨克人说等他的羊群有一天从天上返回,他一定要剪掉它们轻飘飘的羊毛。一群羊的思想太高,超出世俗太多,终究是一件让人大伤脑筋的事情。
第二天,你感到整个身体里只剩下这蓝色而庞大的肺叶在呼吸,你甚至可以看见自己的胸部和湖面一样广阔地起伏,舒展,宛若运动健将。你担心如果它突然静止,像心电图的波纹消失在深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座湖泊的死亡?
一座湖在你的眼皮底下有时闪耀,有时又蓝得发暗。它在夜晚吞没了时间,在早晨吞没了太阳,在黄昏吞没了宇宙。那一刻庞大的世界在你面前呈现出末日般的沉静,到处都是虚无和无中生有,常年积雪的高山,在最后的金色余光中显现出平时看不见的环形倾向,而峰顶的积雪倒映在湖中的白增加了世界的虚幻。你看见爱情,梦想,远方和460平方公里的海子,都是最孤寂的,而你比它们更孤寂。你的眼里没有忧伤,也不追念,只有一只鹞子在暗下来的湖面低低地飞旋,它是你自身孵化的鸟,有三双眼睛,五只翅膀。天黑下来的时候鹞子突然翻了个身,仿佛被冰滑了一跤,仿佛湖面是一块巨大的从不融化的冰,又蓝又脆,无法呼吸。它还没有被打破的蓝色孤独,和你一样找不到流出去的豁口。
你突然想到,人和湖都是神所创造,是天地所生,一座湖出现在这里,肯定不是为着自己的缘故,你来到这里,也不是为着自己的缘故。在这个星球上,人都是活一阵子,然后死掉。湖也是活一阵子,然后死掉,只不过湖比人活得更久也比人死得更久。你无法知道冬天一座结冰的湖,是属于活着还是死去,那时它是一颗硕大的蓝宝石戴在神的手指上,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用切割羊肉的刀子一块一块切割下它们,冰峰一样驮在骆驼的背上运回毡房,烧奶茶,煮羊肉,做抓饭。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吞下神的赏赐是为了延续生命,强壮地活下去,这些蓝宝石的蓝在他们的肠胃里被消化被吸收,最后成为他们眼珠子里的蓝,血管里的蓝,呼吸里的蓝,语言里的蓝。
从今往后也将成为你灵魂里的蓝。
第三天,一个盲眼的阿肯沿着你的路线来到三台海子。他看不见蓝,一如他看不见光,但是光和蓝会通过弹唱的十根手指进入他的内心,成为他弹唱的一部分。
第四天,你在湖边散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她从湖岸的那一头向你迎面走来,步子和手臂步调一致得有点令人想发笑。就是说她迈左腿的时候摆动的是左臂,迈右腿的时候同样摆动着右臂。这样她走动的姿势就显得十分奇怪,臀部有些夸张地扭动,还有她胸部的乳房,饱胀得简直要把衣服撑破。擦肩而过的时候,你飞快地在脑子里计算了一下,如果用你自己的身高作参照物,她足足高出你五个头还不止。你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女人,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女人,她的高大和健硕简直令你感到惊惧,还有她身体散发出的奶香,令你感到饥饿。
下午你在湖的另一边散步的时候又遇见了这个女人,相遇的时候她礼貌地停下来侧过庞大的身躯让你先过。你迟疑了一下,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弧线优美的“请”的手势,同时还不忘记礼貌地微笑。在如此荒蛮的地方你依然保持着绅士优雅的风度,这十分难能可贵。女人被你的举止弄得不知所措,看来她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甚至从不曾见过这种奇怪的肢体语言,以她的见识,实在无法理解其中明确的含义。你看见她脸上露出惊慌的表情,就像遇见了一个陌生的鬼。凭良心说,她长得不算差,只是两只眼睛间的距离相隔远了点,看上去像禀性多疑的食草动物。在你们相对而立的时间里,她的嘴里像嚼口香糖似的一直嚼个不停,起初你以为是她掩饰内心不安的表现,也难怪,一天的时间里,在这么大的水域的边界,你们两次相遇,就像两颗运行在茫茫银河中的星星,两次偏离自己的轨道撞在了一起。后来你听见她的喉咙里发出咕嘟一声响,她竟然把咀嚼的东西咽进了胃里。接下来,她又把什么东西从胃里吐到嘴里,继续刚才的咀嚼和吞咽。这时候你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你认出她原来是哈萨克人家里的奶牛,每天早晚两次被主人挤奶,其余的时间,不是在满心忧伤地找自己的小牛犊,就是在找那只和她交配过的公牛。
你帮她把松开的头巾重新系好,她的头顶上鼓着两个硬硬的包,世界曾给予一只牛短暂的爱情,但却不允许她长出幻想的犄角。
同样,世界也不允许你长出翅膀。
“你还要走多远?”她突然开口问你。
你低头想了一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说,说不好。你在努力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但找不到。气压,气流,时间的推移都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你弯腰摘下一朵恰恰草的花递给她,她接过去含在嘴里,沿着湖岸慢慢地走了。
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单调的日子一个接一个。你发现你找不到你的思路了,如同一个人深入梦境,醒来时无法记起曾经到过什么地方。你怀疑你的思想恐怕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到你的脑子里来了。
第十天,雷电在傍晚时分咬住了山峰,接着在马群中炸开。那些叉形的闪电是天神甩出的响鞭,吓坏了低头吃草的马,它们不知道大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明白为什么受到惩罚,只是受惊地在山坡上四散逃奔。蒙古人被自己的马从马背上摔了一下来,那个蒙古人是一个浑身鼓胀着蛮力的中年人,长着一副铜嗓子,他发出的声音像五十个人发出的一样大。但他无法把自己的马喊停下来。他狼狈地钻进哈萨克人的毡房躲避闪电,一边大碗喝奶茶一边响亮地放屁。可怜的哈萨克人仿佛遭遇了更可怕的闪电在他们头上炸开,一个一个捂着鼻子跑出毡房,然后从湖底浮上来般长长吸一口气。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洁癖的民族,从来不在毡房里放屁。蒙古人对他们的大不敬让他们很生气,在雷电停下来之后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寻找马匹,那些马都是老马,会在三天后自己走回来。他们要做的是拆掉毡房,找一处洁净而干燥的地方,重新搭建一个新的住宿地。
蒙古人并不为自己粗鲁的行为感到羞耻,也根本没有打算道歉,在哈萨克人忙着在天黑前搭好毡房的劳动中,他一直嘲笑不止。他跟你说起一些过去的事情,曾经一个路过此地的汉人送给哈萨克人一些蔬菜,以报答哈萨克人收留过夜的好意。然而哈萨克人吃惯肉食和奶酪的肠胃消化不了这些纤维和维生素,一家人轮流地跑到毡房外放屁。汉人的礼物最终惹怒了哈萨克人,半夜他被赶出毡房,摸黑爬过一座山,投奔到蒙古人的毡房里。
第十一天,午夜的时候传来敲门声,你肯定来者不是夜间看牲口的哈萨克人,也不会是蒙古人,他们在夜间从不靠近湖,他们也不让牲口靠近湖。湖中的水怪在月光下抓走过他们的骆驼和女人。你的住所正是当年勘探队留在湖边的空房子,透过左边的墙缝可以看见月光旅行在肋骨似的水波上,透过房顶的漏洞则可以看见天空中湖的虚幻的倒影。湖的多种可能性从各个方面包围着你,有时候让你以为自己处在一个虚无缥缈,空无一物的地方。
敲门声响了好一会,断断续续。后来你发现敲门声其实来自窗户,于是你推开窗,一只夜鸟从窗外闯入。不是一只猫头鹰,也不是一只老鹰或灰头雁,是一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鸟,有点像乌鸦,但比乌鸦大十倍,也比乌鸦黑十倍。你猜测这是一只旅行的鸟,和你一样带着旅途的风尘,头上的发型被风吹得很乱,腋下磨破了皮,为了好受一点,它得微张着翅膀。等它一开口发出声音,你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它的口音完全不是本地的,卷舌,鼻音很重,语速也很快,有点像是从斯拉夫语系地区来的,不过,也有可能是波斯语系地区。你猜测它的国家:斯洛文尼亚?俄罗斯?不,那实在太远,一只鸟孤身旅行充满危险,弄不好会中途毙命。最有可能的是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只要飞过边境,就能很快到达这里。
夜鸟不理会你猜疑的目光,它竖起耳朵,颇认真地听了漫长的三分钟,仿佛银河的光被它听见。然后它松一口气,咕哝了一句,缩起脖子准备睡觉。夜鸟的黑让你看不透,你想打破这种诡异的气氛,于是说起一连找了十一天的驿站,“那就好像一个抛尸荒野的人,连一点遗址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你怀疑驿站被风刮到天上去了,或者被湖水淹没沉落在了湖底。可是你想不出那些驿站上的人都去了哪里。如果他们死了,他们肯定在这儿,如果他们没有死,他们也应该在这儿。总之,驿站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剩下,不可能消失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夜鸟沉吟了一会,比划着说这个它也不明白。它跟你一样是来证实一个问题的,它听说赛里木湖的湖底与巴尔喀什湖是相通的,有一条暗流像秘密的通道,某年一艘赛里木湖考察的船只,在湖心被吸入水底,后来这艘船出现在巴尔喀什湖的湖面上。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是不是说巴尔喀什湖和赛里木湖就是两个连体的湖,这就像人类的连体双胞胎一样,它们在地球上两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各不相干,又心脉相连意念相通。这个湖里的水浅了,那个湖的水也必然浅下去。这个湖的蓝和那个湖的蓝几乎是混合过一样的均匀。或者,它们根本就是同一个湖,这个湖是那个湖的水光的折射,那个湖是这个湖蓝色的幻影。如果一个湖从地面上因种种原因消失,那么另一个湖也会因同样的种种原因而消失。
“驿站可能沉落湖底,沿暗流到了巴尔喀什湖,最后在那个地方出现。”你沿着夜鸟的思路推理,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可是,如果说两个湖是同一个湖,你实在无法判定你现在是身处真实的湖还是幻影的湖。你更无法判定的是,你自己是真实的你还是幻影的你。
夜鸟告诉你在中亚的腹地,离巴尔喀什湖不远的一座城市,有蒙古人留下的宫殿。蒙古人曾经征服过那里。而赛里木湖边也一直有蒙古人活动的踪迹。巴尔喀什湖边的蒙古人,是不是就是赛里木湖这边迁徙过去的同一个部落。也有可能是这个部落零碎分散的一支。从自然分布和气候上看,高气压总是在蒙古高原上形成,它们像强大的蒙古人一样,从那里就开始了四面八方的侵略和扩散。蒙古人的影像有可能被投射到各个地方,最远的在多瑙河沿岸。有一部分,甚至有可能经过光线的折射去往了另一个星球。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要不无法解释那么庞大的蒙古军队和部落,曾经覆盖了亚洲乃至欧洲的大部分面积,最后却只剩下了地图上一个面积不大的国家,一个逐渐被外族人分化的省份,外加一个地势向西倾斜的荒凉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夜鸟很担心自己这次冒险出来会找不到回去的路,因为它不是一只候鸟,从来不飞到别的地方去,只在自己的领空里飞。它既没有候鸟辨别路途的能力,也没有长途飞行的体力,它的体型偏胖,不适合长距离飞行,但它想弄明白一些问题。
对此你表示同情,因为你也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有时候一个人和一只鸟所想的基本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人的思维不见得比鸟更深奥。
天亮的时候,夜鸟用你的剃须刀修整了一下羽毛,看上去精神了很多。然后跺跺脚,一使劲从昨晚闯入的窗子飞走了。
第十二天,你摸到快结霜的天气里,秋天还有十二天,黑走马还有十一天,黑松林还有七天,落日还有五分钟,炊烟还有半分钟,五岁的哈萨克小姑娘,还有最后一秒就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她仿佛是热情所生,浑身散发着小动物臭烘烘的气味,一个下午都忙着在山坡上打地鼠。那些灰色的地鼠皮毛闪亮,不断从各个洞口冒出来,摆出妩媚的姿态,俨然一群擅长勾魂术的小妖。后来它们开始模仿哈萨克小姑娘擤鼻涕,擤完鼻涕手指在脚背上一擦,露出两颗啮齿嘿嘿地嘲笑。小姑娘恼怒得脸色发红,刚打下去一个,另外很多个就从她的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冒出来。这些狡猾的家伙打通了地球的思路,它们在复杂黑暗的窟窿里像是一些有思想的家伙,负有重载似的稳重,但它们一露出地面就失去了想象力,除了模仿,搔首弄姿和嘲笑,剩下的就是一个出卖自己的大肚皮。哈萨克小姑娘最后被七十岁的哈萨克老女人拽回了毡房。小姑娘叫她妈妈,那其实是她的外祖母,她是按还子的习俗送回来的。对哈萨克民族这个古老的习俗你已经不感到陌生。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父母以报答生养之恩,最后再把自己还给神以感谢上天的赐予。在这里生命就是如此简单和明了。
第十三天,是一个突然变冷的日子,世界绿的部分不再绿,瑞香狼毒也好,轮台草也好,一下子软弱下来,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它们开始迅速萎缩,世界开始变成一个遍野干枝的荒凉世界。浅蓝的湖也变成了深邃的蓝,没有一丝杂质。这时候云的影子落到湖面是站不住脚的,哧溜一下就滑跑了。山峰变成寒冷的金属堆积的山,也几乎不能再停留湖面。一群鸟急速地飞过,看上去是借助了吹刮的风力才消失得那么快。这应该是你见过的最为不真实的一次飞翔。这时候所有的牲畜都不再进食,甚至不再反刍,闪耀着光泽的粗盐粒这时候也不能引起它们的胃口。牛,羊,骆驼,马都呆呆的聚集在湖边,默不出声地进行着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你夹杂其中,忘记了周遭,不再思考任何问题。在这里所有的思考都是徒劳的,思考只会让你更加混乱更加糊涂。
新疆时间五点半,牲畜开始有序撤离,湖边顿时空空荡荡,你怀疑地伸出手,但摸不到一丝灰尘。你确信这里已经是世界尽头,连接着一个冷酷仙境一样的地方。随着西伯利亚寒流大面积地经过,三台海子很快就要下一场罕见的大雪,在这之前,哈萨克人将去往山脉那边的冬窝子,蒙古人则去往高原上的博尔塔拉。在这之后,海子封冻,大雪封山,这里所有的生存和生命将告一段落,包括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