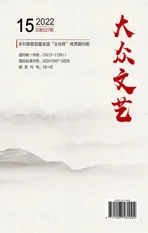信仰的形象·陶瓷佛教造像之语义
——元、明、清陶瓷佛教造像
2015-07-12欧阳昱伶四川美术学院400000
欧阳昱伶 (四川美术学院 400000)
信仰的形象·陶瓷佛教造像之语义
——元、明、清陶瓷佛教造像
欧阳昱伶 (四川美术学院 400000)
元、明、清陶瓷佛教造像,从技艺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创造潜能活跃起来,使新风格得以产生。制瓷工艺与难度之间挑战性的选择无疑使造像更加理想化和更加意义化。
佛教造像;元明清;陶瓷技艺;朝代范式
元、明、清陶瓷佛教造像通过技艺上升使质地和色泽、姿容和状貌、形式和风格都置于发展的创造之下,技艺发达使它们易于变化;它们多样,它们丰富,它们不断地改变气质形象。它们并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滋养生发,它呈现依次发生的永恒,是一次次从容的、自如的事件,一次次经典:在前一个经典造像背后,还有下一个经典孕育着,而在每一个经典之下,都有一个集体灵魂的信仰世界。在所有的技艺力量之下,在每一个法相之下,虔诚都更加真实。
元代影青菩萨坐像与青白釉水月观音像不只能在仪态娴静优美,璎珞帔、花冠镯缀的华丽又缤纷活泼的视觉印象中突出其属神法像的身份;更在能够享受宗教的快乐和融汇理想的联合中获得意义:自由、静观和无虑的精神客体和虔诚的实践主体在这里聚合:答案依然是启发注意力、精神的进化、灵性的成长以及灵性的升进得以到达的喜乐——无执着——静观的自然。
结跏趺坐于犼兽上的元代龙泉窑骑兽观音像,喻示着普渡无量众生。其不同于青白釉观音像的仪态、塑造、釉饰以及赭红胎色,都不过是适应信徒们的不同需求而显现的不同形象罢了。
除德化窑外,明代传世、出土的陶瓷佛造像还有洪武青釉带座佛像、青花布袋僧像、哥釉达摩坐像、青釉布袋僧像、米色釉阿弥陀佛像、密宗千手观音像和白胎五智如来像龛以及明三彩佛像等,它们在树立信仰所能到达的、技艺所能实现的——资源与传统、技艺与特色的这种多样标志着佛教作为能动的宗教的发展,明代佛像自身呈现的多样性已经告诉我们各种倾向和差异的表现是什么。此外,这各种倾向不是相等的,它们具有不同价值。
明代何氏佛像的范式给瓷塑佛像的建构诠释更高级的意义,在观想中存在的意义。其核心概念是与神连接,从中产生一种可靠的意义,这个意义形象——不论达摩亦或观音都无限细致、复杂、细腻、厚重,它们是清晰的、神性的、精神的和被宣传的。何氏佛像的超凡脱俗对抚慰被掩饰和封闭起来的内心,是一种有疗效的精神法。神韵光环滋养着人们的精神实践,宗教化的实践和朴素的诉求实践。它无限地编织佛像的神圣的多,把它放在了艺术的目标上,造出神话概念的一种增补性的再现,以及以意义为指向的艺术。色泽上,白釉不再向我们呈现已经存在过的白色,而只是德化所是的“如脂似玉”,它是灵性的光耀,它因此而达到神话,并因此而始终区别于它白,并成就了充分发展的白色与胎、形、神合一之间存在极致的程度。其突破由佛像造像的历史化所提供的既有样式,宣布这些神话的人物都作为更卓越的存在而存在,同时,这里更有对“空静”和“无思虑”的伟大注释,其不可简约的神圣性稀释着现实世界的尘嚣。何氏佛像作为实践信仰的观想物,对应于开解现实世界的诱惑给心灵设置的障碍,其观、想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何氏佛像作用于心灵的可见的力。
明代三彩佛像所呈现的既不是唐三彩饱满的视觉强度,也不是辽三彩直至精神的形式变种。它在实现自身的情况下达到差异的创造,同时又包含前朝因素——这就是它付出的最大努力。在对信仰和价值的理解中,它以世俗化,人格化,现实化使形象集中,是其在人们沉浸其中的全部感官体验中呈现的身影。它试图表明,用世俗化的形象来肯定信仰不只是亲和现实的修习,而且使现实的修习同时包含神的授权和加持。在此,世俗化的选择不仅仅是像教的策略,它呈现给感官的,感官在形、色中发现的,是信仰与世俗生活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中的结果。
清代博及渔人款观音立像依然携带着明德化窑白瓷佛像的唯美基因,但在法像中存异的不是仪态,也不是仪态塑造,不是风格,而是气质。
在景德镇的瓷佛造像中,景德镇已经取得的瓷艺成就是这些神祇异彩纷呈的时代支持,而翻新瓷佛造像又激发了技艺人的创造潜能。古老的瓷艺继续在支撑信仰使命下扩展表现(从形姿设计到工艺手法),翻新模式(包括生成为某一风格提供范本性模式),混合技艺(集多种装饰于一体,以及借鉴藏传佛教金铜佛像的样式);几乎所有景德镇的制瓷工艺——雕塑的、色釉的和绘饰的,协力了瓷佛造像的行动。它把向新品的变革、实验的热忱、扩展工艺力量的有意识努力这些主动,导入造像价值的创造之中。
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通过捕捉藏传佛教造像的玄奥神秘而显示自身,粉彩描金——那些奇幻瑰丽的极端浓缩旨在在严格约束的佛像造像量度上把藏传佛教艺术串联起来,并用一种独一无二的“身之工巧”宣布它在皇家气派的造像中的极致观念。在这里,技艺挑战性的复杂触及到了属世的永恒性质。御制造像,实际上意味着担负有极致使命的传达,它主张工艺与精湛绝对接近,难度与价值的意义绝对接近,塑型敷彩与审美的理想性绝对接近。
素三彩十八罗汉群像。塑型既非通用也非奇特,既非神化也非草根,既非程式化也非符号;敷彩既非再现也非偶得,既非附加也非对缺乏的补充,既非简单的整合也非简单的次要性;表现既非模式化也非特殊化,既非模仿也非臆造,既非同一也非差异,既非标准也非随意;工艺既非奢侈也非平庸,既非廉价也非昂贵,既非普遍也非改造,既非重复也非偶然。罗汉群像——在创造(形式的形成)中将组构和主题统一起来的有效工作自动填补形、意接缝。在清代瓷艺的领域里,这种开拓更加可靠、更加深入。
在清宫旧藏的两套陶塑罗汉群像中,石湾“十八尊者”的各种准草根用语:渔樵耕容、粗服敝履,自在中包含了高士们寄托于归田园居的真正自由的精神诉求,构成了罗汉群像返璞归真的基调。塑手建构性的直觉创造了集泥艺、釉韵、灵心为一体的淡泊自如。悠然的、平静的和“质性自然”的草根应身是这些神圣住世的一种介入,市民趣味与罗汉造像的关联存在其随机缘显现的人格身之中:我不在,在那里我是我灵的衣服;我不是我是什么,在那里我并非非我在。
人类的前进除了物质文明更有求真意志。因为在对世界(内部的或外部的)的认识中——也因为在人生无明的“苦”之中一定要有解脱之道,像教便提供了一种开悟境界的直接方式,这些陶瓷佛教造像的共同特征就是传递佛像所表达的的主张,所承载的智慧。作为弘法的直观符号,造像促使人们在宗教情操上观想教义,使解读增值,清晰的表达意图反映了造像本身揭示的佛法智慧,其意义和内容都在触及终极范畴的价值取向内进行。
[1]孙迪.《琼瑶琨琚——中国古代佛教陶瓷塑像赏读》.收藏界,2006(77).
[2]孙勐.《北京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收藏家,2012(06).
[3]吴明娣.《中国古代陶瓷佛教造像述略》.佛教研究,2002(1).
[4]田军.《故宫藏石湾窑瓷塑罗汉群像》.文物,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