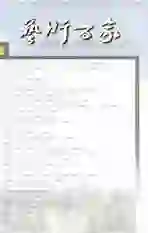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现代性建构
2015-07-07于忠民
于忠民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Modern Construction of Realist Film Aesthetics: Reading Shen Yizhens Study of Realist Film Aesthetics
YU Zhong-min
(School of Media and Fil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现实主义备受冷落的当下,针对国内电影艺术质量和功能的退化,沈义贞先生在著作《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国电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即是一个对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再认识问题”[1](p. 2)的命题。作者对现实主义的这种理论自信,一方面主要根植于对现实主义电影实践悠久历史的考察、对现实主义策应当下的现实有效性论证,以及对现实主义未来发展的宏观展望之中,另一方面则源自于对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现代性建构的认识之上。
一
现实主义电影实践的历史论是作者建构其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现代性体系的重要基础或逻辑起点。作者不是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既定的理论模式和预设的结论之上,而是采取“以史为鉴”的实证方法,从中外电影实践的历史史实中求其所“是”,即主要的特征、规律等,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电影史观。在《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研究》中,我们看到,论者首先对中外电影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宏阔的检视,并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剔除偶然性的遮蔽寻见出世界电影历史的主流脉络和发展趋势。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路径我们获得了如下的认识:在中外电影艺术的发展史上,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电影艺术实践,以及围绕着它展开的理论话语影响最为久远、成就最为显著,正如作者所言:“无论就创作实践抑或理论研究而言,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参与或观照,我们也就失去了谈论这些作品的依据,其价值性也就大打折扣”[1](p.45)。也正因此,我们可以把世界电影的“主流”历史看作是一部关于现实主义发生、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者那里,现实主义并非是一个保守、封闭的美学体系,本书中,作者就以“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对中外电影史上各种眼花缭乱的电影文化现象、思潮和流派进行了统摄,从不同影片类型之间的区隔中寻见其被其他主义或表象所遮蔽的现实主义的普遍性与恒常性。作者此番的历史性审读,不仅为我们“重写”了一部现实主义的世界电影史,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现实主义的现代转型。
过去,我们在讨论好莱坞类型片的时候,往往只将其定位于产业化生产的类型化文化商品而与现实主义美学撇清干系,但作者却看到了现实主义电影与类型电影的共通之处,诸如,好莱坞是“类型其表,现实其里”,即其类型片的外衣下包裹的依然是现实主义内核;“法国所谓的‘第三种道路”并未脱离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在电影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其本身就是以现实主义命名的;因循于本国文化传统的英国电影可以说是“并未张扬的现实主义”;注重理性思辨的德国主流电影则是“哲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
作为解决中国当下电影病灶的理论探索,作者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审读才是其“历史论”的真正旨归。沈义贞用几组关键词把中国百年的电影历史,依照其历时性的表征分割成四个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回家”与“离家”(1905-1931);第二阶段,“大时代与小人物”(1931-1949);第三阶段,“英雄与集体”(1949-1966);第四阶段,“探索与发现”(1976-1988)。尽管其各个历史时期的叙事主题不尽相同,但是,作者认为“在既往的一百多年的中国内地电影实践中,现实主义一直是内地电影的主流,或内地电影的主导品格” [1](p.132),因为,中国电影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保持同步,时代风云的变幻,社会风貌的迁移,都在中国电影的镜像中得到了如实的反映;百年中国内地电影之旅不仅承载了中国内地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交锋和观念演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担负了传播、探索、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使命等等”[1](p.131)。也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电影史就是一部百年来影像化的民族心灵史,包括华语电影中“台湾的寂寞中坚守”和“香港穿行于类型电影”的操演亦是如此。
中国电影所取得的辉煌和经历的挫折都与我们是否真正地坚持现实主义美学有关。历史上无论是左翼电影的成就和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都证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特别是“文革期间”,电影艺术之所以呈现出意识形态功能畸形化,认识功能狭隘化和审美功能程式化的症结,反证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实践中只有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才是保证其文化的继承与建设的关键。
在此必须提醒的是,作者借助其历史论重提现实主义曾经的辉煌,其目的不单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它过去大有作为的肯定,而是通过“历史论”为现实主义话语资源寻求其“进入当下”的路径与语境,其言外之意就是,即使在当下,现实主义也同样具有其历史上一样的主流地位。
二
“现实主义当下有效论”是作者建构其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现代性体系的核心观点。所谓“有效论”即我们不应停留于对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一般概述,而是要在给出现实主义“必须”再度出场的理由的同时,还要为现实主义摆脱当下的困境出谋划策。
要坚持现实主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得弄清“现实主义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否则就会因概念不清无理可据,从而再次陷入以倡现实主义之名,却行其它主义之实的混乱之中。那么,现实主义的本体性到底是什么呢?论者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话语系统的考察指出,其本体性就在于它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日渐积淀的规定性,即,它的真实性、典型性和作为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性。“真实性”是其原则,“典型化”是其方法,“意识形态性”则是其应有的功能。现实主义正是依靠这些本体性的显现来实现它自身的审美价值。
为什么要坚持现实主义?论者的论述也没有拘泥于电影本身,而是将电影摆放到一个更为宏阔的语境中予以论证。
首先,现实主义的复兴在当今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政治需求。作者强调,现实主义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它仍然承载着对中国当下社会矛盾的深刻呈现、民众愿望的真切表达、社会心理的准确反映、个体焦虑的独特揭示、边缘底层的人文关注等等重要使命。
其次,当下中国文化场域的生态失衡也急需现实主义的再度出场予以制衡。“电影艺术已退回到了娱乐杂耍的游戏层次” [1](p. 14),当前电影中“正能量”的“缺席”亦如其“十七年间”狭隘地“在场”一样,都会给我们的民族文明带来灾难。所以,作者提醒我们,“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娱乐永远绝非时代的主导精神!一个耽于逸乐的社会一旦遭遇历史的重大挑战必将崩溃,而以娱乐作为电影唯一的、终极的目的,亦必将使电影倒退回早年的杂耍。”[1](p.354)因此,用现实主义美学的内容丰富性、主题深刻性和审美诗性来反制当下流行文化中粗俗、浅薄、阴冷、灰暗等病症,是我们呼唤现实主义再度出场的又一合理申述。
再次,现实主义的出场某种程度上亦是我们抵制全球化浪潮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策略。在当前的中国电影实践中,我们所能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发扬中国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以其对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弘扬,以及对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和人们主体精神的深刻把握,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具有东方诗学韵味意境和人文内涵的,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化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影视作品。
三
面向未来的“发展论”是作者建构其现实主义电影现代性美学体系完整性的必然选择。所以,作者在探索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复兴的时候,并没有停留在对既成的经典理论的复述层面上,而是在遵循现实主义本体的“真实性”、表现方法的“典型性”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原则下,根据社会经济文化语境的新形势、新变化,最大范围地容纳、吸收新的文本资源与学术前沿的新的发现加以补充,不断赋予现实主义新的内涵。那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延续和发扬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怎样才能为大众广泛接受?”[1](p.4)
首先,重新衡定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通过对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的把握,指导具体的创作实践。毫无疑问,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现实主义电影与类型电影同为艺术品,其在美学特征方面亦有若干重合之处,论者正是在这一认识背景上,通过对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特征的反复提炼,以及与类型电影的反复比较,提出现实主义电影有别于一般现实主义文本以及类型电影的三个核心的美学特征,即,“现实流动性的跟踪”、“现实审美性的依归”与“主体的独创性和内显性”,这就不仅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依据,而且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实践指明了路径。
其次,突显了“现实主义电影的观赏性”问题。与类型电影相比,现实主义电影常常曲高和寡,流于小众化,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在强调艺术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一个观赏性的问题。而要提高观赏性,也有诸多方法。论者给出的具体策略就有,摆脱传统文学形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文学性,“转向影像,转向类型”,最大限度地发挥“跨国想象”等等。
再次,提倡“现实主义大片。”作者指出,“所谓‘现实主义大片不仅是指采用大制作、大宣传、高投资、高科技、超强的明星阵容等高概念运作的电影,而更多的是指其具有一种大思想、大气魄、大境界与大视野,能够全方位、全景式的展现时代的精神风貌与社会生活画卷,不仅能够最为广阔地反映现实表象,而且必须传达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从而往往具有一种史诗品格。”[1](p. 314)(责任编辑:贾明哲)
参考文献:
[1]沈义贞.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