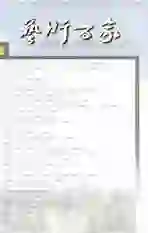“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军影像改写
2015-07-07吴海云
吴海云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电影对于抗日战争中日本士兵的塑造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并由此构建出两种日军影像的“定型化”:“丑角”式的与“禽兽”式的。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塑造的日军形象呈现出全新的特征。今天的中国导演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下,尝试以新的角度与方式重申和叙述中日之间在“二战”期间的冲突与暴力,希冀在世界舞台上对那段历史的阐释发出自己的声音,却在对“国际身份”的渴望与追求中忽视了“中国身份”的本位思考,自动归入了国际化/西方式的思维与叙事框架。
关键词:电影艺术;定型化;国产电影;日军形象;改写;艺术作品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Rewriting of Japanese Army Imag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s an Emerging Superpower"
WU Hai-yun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Simia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10061)
电影,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流行艺术形式,其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许许多多的电影作品中加以保存。而日军的形象在不同时期国产电影中呈现出的各自特征,折射出中国意识形态的不断变更。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产电影中对于抗日战争中日军的影像塑造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并由此构建出两种关于日军形象的“定型化”(stereotyping)。“十七年电影”中有不少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包括《平原游击队》(1955年)、《铁道游击队》(1956年)、《地雷战》(1962年)、《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小兵张嘎》(1963年)、《地道战》(1965年)等。这一时期影片中的日军,多以“小分队”的形态出现,很少有血肉丰满的个人;即使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体”从群像中脱颖而出(比如《地道战》中的山田、《平原游击队》中的岗村),但一旦将数部作品相对照,就会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特点,带有明显的公式化、类型化描述方式。
“十七年电影”中日军的定型化形象是:身材矮小,獐头鼠目,目光凶恶,智商低下,常常腰间别着一只鸡,嘴里喊着“花姑娘”——总之,是具备喜剧元素的邪恶角色。面对这样的敌人,中国老百姓往往经过几场埋伏、几次冲锋,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十七年电影”之所以这样塑造日军,是该时期电影作为革命经典叙事的基本逻辑使然。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产电影中的日军形象出现了重大变化。同样是“抗日”的主题,电影讲述的重点却与过去大不相同:惨烈的正面战争取代了轻巧的游击战役,日军对中国人的疯狂屠杀取代了中华儿女与日本鬼子的斗智斗勇。抗日题材的“十七年电影”,结局无一例外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即使那只是一个历史限定中的局部的胜利;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抗日影片中,中国人被日军欺凌、侮辱、屠杀成为情节主线,比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红高粱》(1987年)、《屠城血证》(1987年)、《南京大屠杀》(1996年)。
影片中的日军,均表现出骇人的残忍、血腥和变态,而不再具备任何“可笑”的特点。
二
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所构建的日军形象,开始表现出与之前的两种定型化形象都不尽相同的新特征。最为明显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演员上,片中的日军不再由中国演员、而是由日本演员、甚至日本的著名影星出演;与此同时,日军角色的形象也发生了从“鬼”到“人”的转变。
领风潮之先的影片是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在这部电影中,尤其是影片的前半段,姜文对于“日军”的人性化改写确凿无疑。该片的黑白色调与片名中的“鬼子”二字,似乎是对“十七年电影”的一种致敬和回潮;然而影片一开场,观众就发现,导演的真正意图在于对前文本的颠覆。
另一部因“颠覆性”而引起巨大争议的电影《南京!南京!》中,日军群像也具备这样的“人性”特点:面对南京城内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但在暴力场外,他们是一群相亲相爱的年轻人,一起跳高、跳舞、唱民歌、踢足球,彼此间进行着“我好想吃炖山药”、“你妈妈做得确实很好吃”之类同乡间的温馨对话。
事实上,《鬼子来了》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国民性”的电影:一方面,它对于中国老百姓轻信、懦弱、窝里斗的国民性进行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军事残暴的战争行为进行了“国民性”归因。
将日军在“二战”中表现的残忍与血腥,完全归因于日本的“武士道”或“民族性”,这种描述范式也出现在陆川导演的作品《南京!南京!》中。这部影片中的第二主角、日本军官伊田,在沦陷的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却不时地显现出一些“人文”情怀:他开枪打死被折磨至疯的慰安妇,给出的理由是:“她真漂亮……她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在范伟所饰演的拉贝秘书被枪决前,他临别赠言道:“人总会死的……这是个很美的地方。”在影片的叙事逻辑里,支撑此人残暴行为的,是一种“日本式”的文化与哲学。
而最具代表性的诠释,是《南京!南京!》接近尾声时出现的一场“占领庆典”:在悲壮雄浑的军鼓声中,日本军士用一种奇特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完成对牺牲日军亡灵的祭奠,表现出武士道精神浸染下的群体性狂热。
三
当然,影片《南京!南京!》对于日军形象最具新意的刻画,在于对其“现代性”的强调。在这部电影中的侵华日军,无疑是一支“现代”的军队:他们大规模地使用枪支、而不是军刀;主角角川的自杀,用的也是用枪打向太阳穴的方法,而不是传统武士道式的剖腹。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小步,却是中国电影对日军形象构建策略中的一大步。
一个具备人性和美德的现代人,也可以同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机器;关于20世纪战争凸现出的这一特点,学者列维纳斯、阿伦特、鲍曼、德里达等都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在此无需赘述。而陆川只是单纯地将这种“人性/兽性”的双面性成列出来,而对于“双面”之间的关联却没有做出任何让人可以接受的解释,这让影片在基本的义理和逻辑上呈现出一段刺眼的空白。
在日军个体的“现代性”塑造上,陆川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是这位对于作为群体的日军现代风貌的书写,却被之后的中国导演继承和发扬。在张艺谋导演作品《金陵十三钗》中,张艺谋、张伟平为了为了在银幕上展现“暴力奇观”,重金邀请世界顶级特效设计威廉姆斯团队打造片中的战争场面。于是,影片中中日两军交战的场面,呈现出《拯救大兵雷恩》《兵临城下》一般的紧张节奏与震撼效果;日军的重型装甲与新式武器,显示它是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钢铁虎狼之师。
四
2008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抗日神剧”。而在大银幕上,出现了一部名叫《厨子戏子痞子》的国产电影,导演是以黑色幽默著称的管虎。
作为一部“抗日”影片,该片完全没有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表现中日的矛盾,而是向观众呈现了一台混合式的疯癫喜剧。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编导对于结局的处理,地下党人以飞扬的柳絮作为解毒工具,此举不但拯救了中国平民,也让日本军人获得了解药,再加上歌曲《送别》的旋律,影片在结尾处竟然呈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日本士兵从侵略者成为可怜的被拯救者,这种叙事可以被勉强解读为一种“大国心态”,即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可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俯视日本,甚至去演义、去戏说、去改写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往。
事实是,今天描写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电影,都在试图重审和重述中日之间那段冲突与暴力的历史往事,并力求站在一个局外人式的“客观”角度,以一种“国际化”的视角,对日军进行一种可以被“世界”接受的阐释。
而笔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这些导演在塑造日军时所采纳新的书写策略,与其说是“国际化”的,不如说是西方式的。比如,《鬼子来了》中对于日本国民性的定位,与其说是基于中国的本位理解和经验,不如说是受到了本尼迪克的《菊与刀》及其他类似西方文本的影响;陆川在《南京!南京!》所塑造的角川这样一个“现代主体”,其“现代性”完全体现在他说英语、信奉基督教等“西方性”上;《一九四二》和《金陵十三钗》,都将日军的侵略行为描绘为西方商业大片中常见的战争“奇观”;而《厨子戏子痞子》更是在叙事范式上借鉴了大量好莱坞的西部片和侦探片,通过讲述一个虚构的抗日盛举,完成了对《罗拉快跑》等西方后方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模仿和致敬。
五
同样是抗日题材的电影,如果说“十七年电影”弘扬的是革命情绪和乐观精神,80年代的创作体现出民族悲情与复兴渴望,那么今天中国的国产电影,则显示出一种对国际身份的渴望与追求。
那是中国伴随着经济崛起后产生的文化愿景,即在世界舞台上对历史的阐释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他们在对“国际身份”的渴望与追求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西方主流话语的阐释框架,无论是对日本的国民性归因、对于“现代性”的强调、还是好莱坞式的影像构建,其奉行的表现方式、叙事框架还是价值体系都是西方式的,让这些回顾中日历史的当代国产电影,缺少中国本位的文化元素与经验思考。(责任编辑:贾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