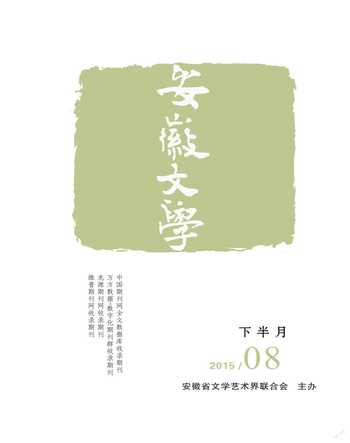戴望舒诗歌意象与其译诗诗歌意象相似性探析
2015-07-05沈菲
沈菲
摘 要:戴望舒作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综观其文学道路,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译诗工作一直相伴相随没有分开,且他本人的诗作与他的译诗之间具有一种明显的文本间的相互阐释关系。本文从意象分析入手,运用互文性理论对戴望舒诗作及其译诗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戴望舒的诗歌作品。
关键词:戴望舒 意象 互文性
作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综观他的文学道路,诗歌创作与译诗工作一直齐头并进、相伴相随。也因此,戴望舒的译诗常带有他本人诗歌的风格特色,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话,会发现彼此间具有相互阐释关系。本文拟用互文性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戴望舒诗歌及其译诗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1]”诗歌因其体裁的特殊性,在互文性关系的表现上更为隐秘,意象作为诗歌的基本元素,往往凝结着诗人特殊的情感或是独特的认识,从诗歌意象入手分析互文性关系,更容易把握戴译诗与戴诗间的特殊联系。
不同的诗人因其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表达方式的不同,而使得诗歌带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不过,有意思的是,某些情绪和精神体验却有着潜在的相通之处,也许在作品中它们由不同的意象来表达,但深入本质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意象能够互相阐释内涵,这也是本文讨论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首先来看戴望舒诗歌中的自我精神寄托类意象,这类意象有一种侧重个人生活情境中的情感,如他作品中的“游子”、“流浪人”、“少女”、“弃妇”等形象,属于完全私人化的意象。另一种则是诗人个人人生经历与感受的表现,带有他本身的影子,比如他的“夜行者”意象和“单恋者”意象。“夜行者……夜的最熟稔的朋友,他染了它一切最古怪的脾气……夜行者是最古怪的人,他走在黑夜里,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我觉得我是在单恋着,但是我不知道是恋着谁……我常是暗黑的街头的踯躅者……人们称我为‘夜行人……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而且又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有研究者认为上述二者属于 “孤独者”类意象,因为它们都偏重于反映诗人徘徊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挣扎纠结的复杂心态,但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戴望舒对其诗人身份自觉性的把握和认知。来看一组戴望舒所译波特莱尔诗歌中的意象,方便我们进行比较分析以加深理解。“信天翁”意象:“这些青天的王者”,“把它们一放到船板上”,就“羞耻而笨拙”, “诗人恰似天云之间的王君,它出入风波间又笑傲弓弩手;一旦堕落在尘世,笑骂尽由人,它巨人般的翼翅妨碍它行走”(《信天翁》);“大天使”意象:“你用轻盈的脚和澄澈的凝视/践踏批评你苦涩的尘世蠢物,黑玉眼的雕像,铜额的大天使”(《赠你这几行诗》)。
这两组意象初感差异性很大,戴的意象阴郁而寂寞,波的意象却自信而张扬。《夜行者》全诗以旁观者角度来切入,夜行者敏锐感受到自己与世人的隔膜,他的形象由世人之眼刻画而出——古怪,安静,行走在黑夜里,只有黑夜与他相伴;而“单恋者”则秉持着坚韧与向往,在尘世间努力追寻着自己内心的希望,只不过这一切在世人看来仍是不可理解的,他依旧是一个古怪的“夜行人”。波特莱尔笔下的“信天翁”和“大天使”作为诗人形象的化身(原诗中已点明),同样着力展现着诗人在尘世生活中窘迫的状态和情境,不过内蕴的情感则是洒脱和无畏的。剥离掉诗人的情绪,再来看这两组意象,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敏感忧郁的“夜行者”、“单恋者”,還是乐观开朗的“信天翁”、“大天使”,他们在骨子里都有一种深刻而难以抑制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并非来源于情感上的寂寞,而是由一种纯粹的精神孤独所激发,它来源于不被世人所理解的诗人们的那份独醒的忧伤与悲愤。诗人眼中的世界与世人眼中的世界完全迥异,他们所鄙弃的,世人竞相追逐,他们所珍视的,世人却任意抛弃,也因此他们成为世人眼中的异类,在尘世间的处境困苦而艰难。“象征主义者的诗歌意象常常是晦涩含混的。这是一种故意的模糊,以便使读者的眼睛能远离现实,集中在本体理念上”[2],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诗人的精神追求与内在情感在意象设置中的重要性。
再来看戴望舒诗作与其译诗中的家园类意象:“五月的园子静无鸟喧,篱门的锁也锈了,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深闭的园子》);“小病的人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于是遂有了家乡小园的神往”(《小病》)。在这两首诗中,无论是对无人小园的畅想还是对家乡小园的神往都传递出戴望舒的漂泊之感,波特莱尔也有着类似的感受:“我没有忘记,离城市不多远近,/我们的白色家屋,虽小却恬静”(《我没有忘记》)。这类家园实质是诗人们在现实漂泊生活中所期待的理想居住地,安然恬静,能够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享有彻底的安宁,家乡本就是诗人们的情感依托之地,也因此这类意象常常带有乡土田园的影子。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那能够带来短暂性安慰的家乡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开始逐渐瓦解,西方诗人所面对的是不断被工业文明侵蚀的大自然,中国诗人面对的则是传统家园的逐步遗失。至此,诗人们的精神家园在现实已无法寻觅,他们只有再度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精神的静谧。“乐园”和“天”于是成为诗人们完全精神意义上的心灵归属地,戴望舒在诗中发问:“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到乐园里去的?/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乐园鸟》),“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像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孩子笑着和哭着一样”(《对于天的怀乡病》),诗篇中所映射出的是诗人的孤独与彷徨。同样的,波特莱尔也渴望“飞向明朗的天空”,因为那“微青色的天边”是“使人梦想永恒的无边昊苍”,阿尔倍谛也有着同样的精神诉求“我邀你,影子,到青空去”,到“青空底真实去”,到“青空底真实之高峰去”,诗人们以此寻得灵魂归属与精神寄托,渴望回返乐园与青天的意念成为他们超越尘世的终极主题。
参考文献
[1]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
[2] 柳扬.花非花——象征主义诗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3] 梁仁.戴望舒诗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4] 王泽龙.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1(3).